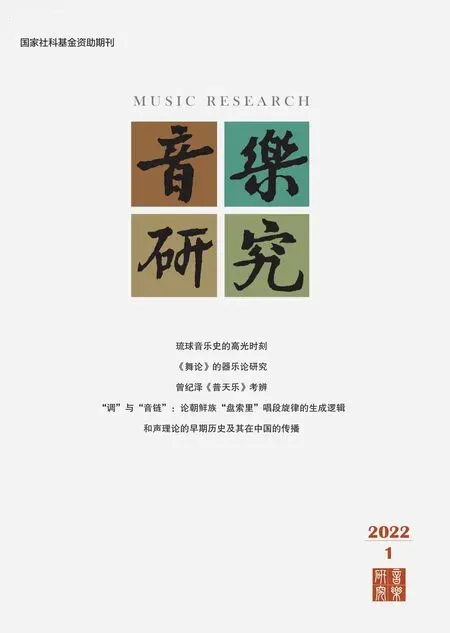和聲理論的早期歷史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兼論斯波索賓團隊《和聲學教程》對和聲理論傳統的繼承(上)
文◎任達敏
和聲的英文為harmony,該術語起源于希臘語harmonia,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含義,其漢語譯義也會有所不同。①國內出版的許多音樂史或音樂理論譯著將出現在希臘、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理論中的harmony 千篇一律地譯成“和聲”,顯然是不恰當的。古希臘人用這個術語代表音階,即聲音的有序進行,該術語的含義是“音階”。在希臘作家的概念中,harmony 指的是一個八度音階中的音程組合,音階不是被理解為一個序列,而是一種結構,是基于簡單的“和諧的”數字比率的“音程”——八度(2:1),五度(3:2)和四度(4:3),這些音程構成了音階的框架(e’—b—a—e),因而harmony 的另一個含義是“音程”。
從中世紀開始,harmony 一詞逐漸擁有了“和弦”的含義,它最初指兩個音同時發聲,現代概念稱之為“和聲音程”。到文藝復興時期,它指的是孤立的三個音同時發聲。從18 世紀后半葉開始,該術語也指同時發聲的音響(和聲音程或和弦)之間的進行,現代和聲概念稱之為和聲“續進”(progression)。②Sadie, Stanley, ed.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armony”.狹 義 地 講,harmony 和triad 為同義詞,其含義又等于“三和弦”。③Riemann, Hugo. Dictionary of Music. trans. J.S.Shedlock, London: Augener & Co., 1896, p.325.作為一個作曲技術理論術語,“和聲”指不同樂音的調性組合實踐,這種意義上的“和聲”是本文研究的中心。
一、和聲理論的內涵及其早期歷史概述
要論述和聲,最佳起點是從今天我們通常所說的“功能和聲”或“調性和聲”開始。“功能和聲”(functional harmony)是德國理論家胡戈·里曼(Hugo Riemann,1849—1919),以法國杰出作曲家和理論家讓-菲利普·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的和聲理論為基礎,而加以完善的“一種調性和聲(tonal harmony)理論。按照里曼理論看,所有和弦都可以被分析為具有主、屬和下屬這三個功能之一,這種類型的分析分別用T、D、S 代表”。④Randel, Don Michael, ed. The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Fourth Edi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Functional Harmony”.可以說,功能和聲的運行方式是出自這樣一個前提:每個和弦都在這種運行或續進中具有某種特定的作用。
“功能和聲”又被稱作“調性和聲”。人民音樂出版社2010 年出版的《調性和聲及20 世紀音樂概述》(斯蒂凡·庫斯特卡與多蘿茜·佩恩合著,杜曉十譯)的書名,包含了“調性和聲”(tonal harmony)這一術語。我們瀏覽一下該書的內容,發現它和我們熟悉的以功能理論為特色的伊·斯波索賓團隊《和聲學教程》⑤伊·斯波索賓團隊由四人組成,另外三位是伊·杜波夫斯基、斯·葉甫謝耶夫和符·索科洛夫,他們均為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師。本文論及的是1991 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增訂重譯本”,陳敏譯,劉學嚴校。國內音樂界普遍將這個教程簡稱為“斯波索賓和聲學”,下文簡稱為“斯氏團隊《教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漢譯本(以及更早的漢譯本)中,第32 章“離調、半音體系”和第33 章“半音模進、離調”中出現了同一個術語“半音”,其原文是хроматическая。半音是錯誤譯法,應譯為“變音”。半音是音程,變音是調外音,即帶有變音記號的音。這種把“變音”譯成或理解成“半音”的錯誤(最常見的錯誤就是把“變音和聲”說成“半音和聲”)在國內出版的和聲教科書和論文中普遍存在,應該予以糾正。的內容大同小異,兩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和弦記號與部分術語的用法有所不同,比較突出的是,前者使用了羅馬數字和弦標記,后者使用了TDS 加羅馬數字的組合和弦標記。布萊恩·海爾(Brian Hyer)給出了調性的簡潔定義:“該術語是西方音樂思維里重要的概念范疇之一,它通常指的是旋律與和聲朝著一個參照性音級(或主音)運動的趨勢。然而,最廣義地講,它指的是音高現象的系統排列和它們之間的關系。”⑥托馬斯·克里斯坦森主編,任達敏譯《劍橋西方音樂理論發展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Theory),上海音樂出版社2011 年版,第686 頁。(以下簡稱《劍橋史》)“調性和聲”這一概念的關注點是:音樂有調中心,使用大調、小調音階和三度結構的和弦。庫斯特卡在《調性和聲及20 世紀音樂概述》(第Ⅷ頁)中指出:“因為每一個和弦都或多或少地在一個調中充當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這種特征導致有時也將調性和聲稱作功能和聲。”這個定義說明,功能和聲與調性和聲涵蓋的是同一和聲范疇,兩者的用語不同,體現了理論側重點的不同。調性和聲通常涵蓋的是西方“共性實踐”時期(common practice,約1600—約1910 年)音樂作品的和聲組織。
斯氏團隊《教程》是繼承里曼功能和聲理論的典型代表,也是集西方前輩理論家成果之大成的教科書。但該書存在著一些概念定義不夠清晰或理論邏輯不夠嚴謹的問題,某些重要的傳統和聲概念或用法沒有被繼承下來,與更早出版的其他西方教科書相比,其內容有很多缺失。鑒于該教科書在中國具有較大影響力,筆者將它作為一個分析樣本,看一看它的功能和聲理論到底是由哪些概念或要素構建的。從這部教科書可以解析出9 個概念或要素:(1)和弦及其原位和轉位概念;(2)和弦之間的關系用和弦的根音關系來識別;(3)屬七和弦定向關系;(4)正和弦與副和弦的劃分;(5)TDS 功能以及功能組劃分;(6)和聲終止式概念;(7)和弦的非樂譜記號標記;(8)調關系遠近的等級劃分;(9)大、小調和聲調性作為基礎。
上述9 個要素或概念,均不是由蘇聯或俄羅斯理論家原創。當代任何一部功能和聲或調性和聲教科書的理論體系,都是16—19 世紀多位理論家成果的綜合體現。前8 個概念或要素的創立,要歸功于多位早期歐洲理論家,特別是拉莫和里曼。而大、小調的形成,則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脫離調式音樂的轉變過程,到18 世紀才在音樂理論中確立。值得注意的是,調性和聲使用的小調主要是包含“導音”⑦把自然小調第七級音也叫作導音的錯誤概念,充斥于許多中國教師編寫的基礎樂理及和聲教科書中。只有主音下方的小二度音才能被稱作導音,自然小調第七級音叫作Subtonic,即“下主音”。Subtonic 是英語,源于中世紀調式理論中的希臘術語subtonium,它最初代表的是正調式收束音下方的大二度。的和聲小調或旋律小調,自然小調使用得極少。以下是對上述9 個要素或概念之起源的追溯。
(一)和弦及其原位和轉位概念
1.和弦概念的萌芽
近代和聲理論是從16 世紀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是建立在三個音或四個音同時發聲的和弦概念之上的,和弦是首要的并且是和聲的基本單位。要理清和聲理論的歷史,首先需要弄清楚和弦概念是如何確立的。最早對和弦產生萌芽認識的是威尼斯音樂理論家焦塞佛·扎利諾(Gioseffo Zarlino,1517—1590),他在其《和聲的原則》(Le istitutioni harmoniche,1558)第三部分第31 章中指出,和弦的多樣性是由低音聲部上方三度或十度決定的。扎利諾的和弦基本性質是由低音上方三度的性質所決定這一權威闡述,引起了許多音樂家對這種特性的關注。不過,扎利諾的論述和現代“三和弦”的概念并不一致。“三和弦”的概念是在他死后才出現的。(《劍橋史》,第713 頁)
從16 世紀末開始,許多理論家開始認識到建立在音程上的和弦的重要性。大約17 世紀初,德國理論家O.S.哈尼施(Otto Siegfried Harnisch,約1568—1623)和約翰內斯·利皮烏斯(Johannes Lippius;1585—1612)都認為,數字低音符號代表的63 和64和弦,從本質上看,是基本53 和弦(原位三和弦)的重新排列,但他們還沒有明確提出和弦轉位概念。利皮烏斯在其著作《爭論》(Disputationes,1609—1610)和《新音樂概要》(Synopsis musicae novae,1612)中,最早提出“和諧三和弦”(trias harmonica)的概念,他創造了術語“三和弦”(triadis),從此產生了現代意義的和弦概念,也為后來的和弦轉位概念奠定了基礎。此外,利皮烏斯還最早提出,調式之間的根本差別是由建立在收束音之上的三和弦性質所決定,正是根據這一理論,今天我們把各種調式用它的主和弦的性質來區分,分為大調類調式和小調類調式兩大類。⑧關于調式分類的詳盡論述可參見任達敏編著《基本樂理》(人民音樂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0—141 頁。
2.拉莫確立了和弦及其原位與轉位概念
拉莫在其1722 年的著作《論和聲》(Traité de l’harmonie)中,開始創立他的和聲體系,在他后來的四十多年里又出版了其他六部著作,其中比較重要的著作包括1726 年的《音樂理論的新體系》 (Nouveau système de musique théorique)和1737 年的《和 聲 的 起 源》(Génération harmonique)。他的和聲體系的要點在這一系列著作中逐漸得到發展。拉莫明確了和聲理論最重要的幾個基礎概念:所有和弦的源頭是協和音程,根音位置的三和弦(完滿和弦),給三和弦增加一個音符所構成的不協和七和弦,所有和弦都可以轉位,和弦的根音(son fondamental)是三和弦和七和弦的生成體。
在《論和聲》第一卷,拉莫以思辨性方式提供了從測弦器(monochord)的一根弦的分割,來推導出所有和弦的詳細過程,而且他還借用了扎利諾的“首六數之比”(senario)⑨扎利諾的首六數之比理論,是他在其《和聲的原則》(1558)中提出的,參見注⑥,第241—242 頁。概念,他認為首六數之比提供了構成任何和弦所需要的成分:純五度、大三度和小三度。“首六數之比”的意思是從1—6 這六個數字中任意兩個數字之間的比率,比如1:3、4:5、5:6 等。拉莫認為,每個和弦都產生于測弦器的弦,因而測弦器就是和弦的基本“原則”。
但是,拉莫的弦長比無法為小完滿和弦的生成提供支持。于是他通過采用大三和弦弦長比的倒影⑩大三和弦弦長比的倒影也相當于“沉音列”(undertone series)概念。而為他的小和弦的生成找到了理論依據。他提供的弦長比是10:12:15(La—Do—Mi),即大三和弦4:5:6結構的倒置,大和弦的生成基礎是根音,而小和弦的生成基礎是五度音。
拉莫通過“八度等同”(octave identity)概念而確立了和弦轉位的認識基礎。例如,弦長比4:5:6 是原位大三和弦(do、mi、sol),如果把4 提高一個八度,會獲得5:6:8,即一個轉位的六和弦;如果把5:6:8 的5 提升一個八度,會獲得6:8:10,即一個轉位的四六和弦。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莫提出轉位概念之前,數字低音時代的大部分鍵盤演奏家和理論家都認為,不同的數字低音符號(例如和弦、和弦、和弦)所代表的和弦是不同的和弦,即使這些和弦是由相同音符組成。這個時期的某些理論家已經有了一些萌芽的轉位意識,但是缺少明確的理論支撐。拉莫和弦轉位理論的確立具有重大意義,他把過去認知中的一個調內的無數種不同和弦簡化為七個不同根音上的和弦,而且他提出了通過和弦根音來觀察和弦之間的續進關系,因而能夠從本質上發現和弦的指向性進行規律。
(二)和弦之間的關系用和弦的根音關系來識別
拉莫在分析和弦時,運用了“基礎低音”(fundamental bass)概念,所有和弦進行均用根音(或隱含的根音)進行來表示。他在其和聲分析中,通常會額外增加一行譜表來標記基礎低音。他的理論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1)從一個和弦到另一和弦的運動應該理解為這些和弦的根音進行,這叫作“基礎低音”的連續。(2)基礎低音的運動具有指向性,這種運動導致產生調性感,而且最終因基礎低音運動與終止式的方向性之間的同一性或相似性,而產生調性的連貫性。(《劍橋史》,第718 頁)他認為和弦根音的下五度(或上四度)續進是最完滿的。
(三)屬七和弦定向關系
拉莫在《論和聲》中明確了以“屬—主和弦”為代表的定向關系。拉莫的“屬—主和弦”就是大小七性質的屬七和弦。他指出,“‘屬—主和弦’之所以被如此命名,是因為在所有的結尾它會立即進行到主和弦”(《論和聲》,第220 頁),“屬—主和弦”最完滿的目標就是續進到主和弦。他指出,“屬—主和弦”的三音(導音)和七音之間形成的三全音程,是推動該和弦進行到主和弦的動力。拉莫還特別強調了導音的作用,認為“屬—主和弦”中的導音對主音的傾向是調性確立的要素,“導音之所以被如此命名,是因為無論它在哪個聲部中出現,它只會進行到主音。我們可以說,它使我們感覺到我們所在的調。”
拉莫認為,和弦續進主要靠的是純五度關系的基礎低音運動,其次還有三度關系和七度(或二度)關系的基礎低音運動。拉莫提升了不協和音程——特別是七和弦的不協和音程的作用,認為不協和音程的存在是促使一個和弦以定向方式進行到另一和弦的因素。在“屬—主和弦”中,是其中的不協和音程推動了該和弦解決到下五度的三和弦中的協和音程。“拉莫常用類似牛頓學說的語言來描述這些和弦的關系:主和弦對屬和下屬和弦產生重力吸引,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把這三種和弦約束在一起”。(《劍橋史》,第694 頁)
(四)正和弦與副和弦的劃分
從其1737 年出版的《和聲的起源》開始,因為受到牛頓引力理論的啟發,拉莫提出一個調的調性組織是由上五度和下五度——屬音和下屬音包圍著的主音而構成。主功能由一個三和弦代表;屬功能的功能就是下行五度到主和弦而且含有一個七度;下屬功能的功能就是上行五度到主和弦,而且它是一個含有附加六度音的和弦。
在這部著作中,拉莫最早確立了第一、第五和第四級音上的和弦為“正和弦”(essential)。他還認為,調性產生于主和弦與它的下屬和弦、屬和弦之間的引力。而第二、第三和第六級音上的和弦都是“副和弦”(incidental)。這種正副和弦的劃分具有極大的作曲內涵,可以極大地簡化和聲的寫作(《劍橋史》,第754 頁)。
(五)TDS 功能以及功能組劃分
TDS 這三種功能的概念與術語的確立應歸功于拉莫,“他的出版于1722 年至1761 年間的著作的大部分理論化內容,是把長期存在的概念重新整理并且合并成一個單一和聲性和方向性的觀點。”(《劍橋史》,第712 頁)在拉莫的和聲論著問世之前,已經存在著主音(tonic)和屬音(dominant)的概念,他在其《音樂理論的新體系》(1726)中首次采用法文sourdominante(英文是subdominant),來代表第四級音上的和弦,即下屬和弦,而且把第五級音上的和弦叫作屬和弦,放棄了早先的“屬主和弦”這一名稱。雖然拉莫沒有明確使用“功能”(function)這一術語,但是他確立了TDS 這三個基本和弦功能。
完整的功能和聲理論是胡戈·里曼在拉莫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里曼在其《簡明和聲學或和弦的調性功能理論》(1893)中首次采用“功能”(function)這一術語,來描述屬和弦和下屬和弦與參照性的主和弦之間的關系。他的功能和聲理論的基礎就是他所說的“Klang”(共鳴體,或和弦)的雙重解釋。他認為泛音列是和弦生成的自然基礎,但自然泛音列只能產生大三和弦,無法產生小三和弦。為了給小三和弦的生成找到依據,他引入了沉音列(undertone series),即泛音列的倒影。因此里曼的和弦生成理論具有二元論的特征,而他的這個認識來自拉莫。
里曼指出:“(1)只有兩種和弦:上生和弦(overclangs)與下生和弦(underclangs);所有不協和弦都被理解、解釋并標記為上生和弦與下生和弦的變體。(2)只有三種調性功能,即主功能、屬功能、和下屬功能。在這些功能的轉換中包含了轉調的本質。”?Riemann, Hugo. Harmony Simplified or the Theory of the Tonal Functions of Chords. London: Augener Ltd. p.9.這里所說的上生和弦,指的是由原生音向上純五度和大三度所產生的大三和弦;下生和弦,指的是由原生音向下純五度和大三度所產生的小三和弦。大三和弦的原生音是根音,小三和弦的原生音是五音,不是根音,小和弦是大和弦的對稱的轉位或倒影。
里曼認為,主(T)、屬(D)和下屬(S)和弦,是調性體系中的三個支柱,是三個功能原型,所有其他和弦都是這三個正和弦的派生和弦。里曼認為,代表特定調性功能的和弦不止一個,主、屬和下屬功能各有三個基本和弦的變體:變形(Variante)、平行(Parallele)和導音轉換(Leittonwechsel)。“變形”使具有相同根音的大、小三和弦相互關聯,如C 大三和弦和C 小三和弦;平行使相隔小三度的大、小三和弦相互關聯,如C 大三和弦和A 小三和弦;導音轉換使相隔大三度的大、小三和弦相互關聯,如C大三和弦和E 小三和弦。
里曼的副和弦生成原理是:大正和弦(T、S、D)的五度音用六度音替代,產生“大”平行和弦(Tp、Sp、Dp);大正和弦(T、S、D)的根音用其導音替代,產生“大”導音轉換和弦(S<、T<、D<);小正和弦(oT、oS、oD)的原生音下方五度音用六度音替代,產生“小”平行和弦(oTp、oSp、oDp);小正和弦(oT、oS、oD)的原生音用其導音?按照里曼的理論,小三和弦是由原生音向下生成的,原生音的導音是其上方小二度音,即“上方導音”。替代,產生“小”導音轉換和弦(S>、T>、D>)。
(六)和聲終止式概念
在調性音樂中,終止式是區分不同程度的終結性質(finality)的重要手法或模式。在調性音樂產生之前,14 世紀的教會音樂寫作中就已經形成多種模式化的教會調式終止式,譜例1 列出的是以對位方式構成的不同類型的三聲部終止式:(a)是弗里吉亞終止式;(b)和(c)是雙導音終止式;(d)包含平行五度的終止式;(e)是蘭迪尼終止式(Landini cadence)。

譜例1 14 世紀常見的三聲部終止式
弗里吉亞終止式在調性音樂作品中得到了保留,并且有些變化。用小調來看,它結束于大屬和弦,聽覺上是半終止。其典型聲部進行是最低聲部從六級音下行到屬音,即小二度下行,同時高音聲部從四級音大二度上行到屬音,典型的和聲續進是iv6—V。這個續進的高音和低音聲部可以上下顛倒,典型的和聲續進是iv—V。弗里吉亞終止在巴洛克時期的作品中使用得非常普遍,而且仍然是當今傳統和聲學的教學內容之一。
到15 世紀,在法國作曲家若斯坎(Josquin,1450—1521)和 迪 費(Du Fay,1698—1739)的作品中,常能見到如譜例2所示的和聲配置,這種配置預示了完滿終止的出現。這種終止式是以三聲部對位方式構成的,中聲部是基礎旋律聲部(tenor,即主旋律聲部),通常級進下行,基礎旋律對位聲部(contratenor,一般為基礎旋律聲部的下方聲部,這里是最低聲部)有跳進。

譜例2 15 世紀基礎旋律對位聲部有跳進的終止式?譜例1 和譜例2 引自Sadie, Stanley, ed.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80. “Cadence”.
另一在17 世紀初的音樂實踐中確立的和聲終止手法叫作“辟卡迪三度”(Tierce de Picardie),其特點是將小調作品結束的小主三和弦的三度音升高半音,以便用大三和弦獲得更強烈的“結束感”。該術語是18 世紀法國偉大啟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音樂詞典》(Dictionnaire de Musique,1767)中引進的。?該術語的英文為Picardy Third。盧梭沒有說明這個術語的起源。這種終止手法在巴洛克時期作品中使用得非常頻繁,幾乎成為小調作品終止的標準用法。但是,自古典主義時期開始,作曲家使用得相對較少。
在18 世紀初,出現了以和聲續進為基礎的不同終止式的區分。拉莫為終止式概念的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其《論和聲》中論述了完滿終止(perfect cadence)、不完滿終止(imperfect cadence)、不規則終止(irregular cadence)和中斷終止。?“中斷終止”又叫作“詐偽終止”(deceptive cadence)或“阻礙終止”。拉莫的分類方式是:從原位屬七和弦解決到原位主和弦是完滿終止;如果完滿終止的兩個和弦有轉位就是不完滿終止;從附加六度的下屬和弦解決到主和弦,或者從主和弦進行到屬和弦就是不規則終止(《論和聲》,第73 頁)。拉莫的完滿終止在后來的理論家的著作中被叫作正格完滿終止。拉莫的中斷終止就是改變完滿終止中的某個音的進行,“在大調中低音上行一個全音,在小調中低音上行一個半音”(《論和聲》,第289 頁)。拉莫的終止式概念大部分被后來的理論家繼承下來。
(七)和弦的非樂譜記號標記
為便于和聲教學以及音樂作品的和聲分析,歷代和聲理論家都設法采用各種非樂譜符號來標記和弦及其性質。無論采用何種記號,都是以簡單明了為原則。和聲教科書使用的非樂譜和弦記號多種多樣,主要有五種:數字低音記號、羅馬數字記號、字母記號、TSD 功能記號,以及這四種記號的任意組合記號。所有這些記號都是在19 世紀末之前被理論家創造的。
1.數字低音記號
數字低音(英文figured bass;意大利文basso continuo;德文Generalbass)大約是16 世紀末在意大利興起的一種簡化的和聲寫作方式,是最早用非樂譜記號記錄和弦的方法,很快就在歐洲得到了普及。在和弦性質方面,數字低音只能體現不多的知識。大約1600—1750 年是它的興盛時代,后稱數字低音時代。數字低音是由書寫在低音譜表上的低音音符和該低音聲部上方或下方的數字組成,當時的數字低音譜和現在的鋼琴譜具有同等意義。最早使用數字低音的似乎是賈科波·佩里(Jacopo Peri)、尤利奧·卡奇尼(Giulio Caccini)、洛多維科·維亞達納(Lodovico Viadana)和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大約1600 年,數字低音被他們用于宣敘調和歌曲的伴奏譜中,后來又在合奏曲的鍵盤樂器伴奏譜中得到廣泛應用。?Maitland, J.A. Fuller. ed., 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The Macmillan & Co.,1906.Vol. II. p.37.
2.羅馬數字記號
最早在理論著作中引進羅馬數字標記的是德國理論家福格勒(AbbéGeorg Joseph Vogler,1749—1814),這是他對和聲理論做出的最大貢獻。福格勒在其1776 年出版的《音響科學與作曲藝術》(Tonwissenschaft und Tonsezkunst,1776)中,用羅馬數字Ⅶ標記了導音和弦,在其后來的《和聲理論手冊》(Handbuch zur Harmonielehre,1802)中,他通過用羅馬數字標記所有的音級(Stufen),來指明和弦根音的音級分布,福格勒發明了羅馬數字標記法。
將音級理論加以完善的是德國理論家格特弗里德·韋伯(Gottfried Weber,1779—1839)。他在其1817 年的著作《作曲藝術系統理論自學指南》?該書英譯版的名稱是Theory of Musical Composition(《作曲理論》),譯者是James F. Warner。筆者參考的是1842 年第2 版。(Versuch einer geordneten Theorie der Tonsetzkunst zum Selbstunterricht,1817—1832 年出版過三個版本)中,采用了福格勒的羅馬數字記號,羅馬數字從此變成了標準的和弦記號。韋伯用大寫和小寫改進了福格勒的記號,為的是能夠區分三和弦的性質。他使用羅馬數字為從1—7的音級編號:大寫羅馬數字代表大三和弦;小寫羅馬數字代表小三和弦;度的標記(o)代表減和弦。韋伯以音級含量為基礎,把這些羅馬數字分配給具體和弦,最終結果是三和弦與七和弦合在一起,大調式有14種基本和弦,小調式有10 種基本和弦。
譜例3 是韋伯對莫扎特《魔笛》中一個片段的分析(引自《作曲理論》第一卷,第397 頁)。注意譜例3 下方的羅馬數字標記,韋伯沒有使用轉位標記,但是他用拉丁字母標記了各聲部的音符在和弦中的位置:R 代表根音,T 或t 代表三度音,F 或f 代表五度音,S 或s 代表七度音,此外還用斜線標記了和弦外音。
3.字母記號
韋伯在其《作曲理論》中還創立了字母和弦記號。他用大寫或小寫的拉丁字母來代表和弦的根音,再附加代表和弦性質的記號,比如,以C 為根音的不同性質的和弦標記是:“C”即C 大三和弦;“c”即C 小三和弦;“oc”即C 減三和弦。韋伯沒有提供增三和弦的標記。他還提供了四種七和弦的標記,例如,以G 為根音的不同七和弦標記是:“G7”即大小七和弦;“g7”即小七和弦;“og7”即減小七和弦;“G7/”即大七和弦。
韋伯除了用羅馬數字表明和弦的根音音級外,還用拉丁字母表明一個段落的調性。他用大寫字母代表大調(如譜例3 中的“F:”和“C:”),用小寫字母代表小調。韋伯首創的這種調性和聲分析標記,今天仍被廣泛使用。

譜例3 韋伯對莫扎特《魔笛》一個片段的分析
英國理論家阿爾弗雷德·戴(Alfred Day,1810—1849)因為看到這樣的現實——通奏低音中使用的數字不能區分它們所代表的和弦性質,而且同一和弦的不同低音位置需要用不同的數字來代表,他認為應該簡化這些標記。他在其專著《論和聲》(Treatise on Harmony)中提出建議,用低音下方的A、B、C、D 大寫字母代表同一和弦的不同低音:A 代表原位;B 代表第一轉位;C 代表第二轉位;等等。因此,一個七和弦的不同位置的數字低音可以用他的更為簡單的標記方式替換,譜例4 顯示了兩種記號的對比。

譜例4 兩種記號的對比
4.羅馬數字與字母組合記號
埃比尼澤·普勞特(Ebenezer Prout,1835—1909)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和聲的理論與實踐》(Harmony:Its Theory and Practice,1901 年第16 版)中,采用了將羅馬數字與字母相結合的組合標記法,羅馬數字代表根音音級,小寫字母代表低音位置,例如,Ib 代表主和弦第一轉位,ⅱ7c代表ⅱ7 和弦第二轉位,等等。這種組合標記法現在英國仍然被廣泛使用。?普勞特標記法,在今天的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ABRSM)的音樂理論教程中仍可見到。
有關TSD 功能標記的說明,見本文第三部分“斯波索賓團隊《和聲學教程》對里曼功能理論思想的繼承”。
(八)調關系遠近的等級劃分
最早對不同調性之間的遠近關系做出等級劃分的也是韋伯。在18 世紀,德國理論家有時會運用“親緣關系”(Verwandtschaft)這一術語,來談論調性之間的關系。調性遠近關系的劃分,通常依據的是一個自然音集(或自然音階)與另一自然音集(或自然音階)之間的音高含量的相似度,或者說兩調之間的共同音的多少。韋伯的《作曲理論》對調關系的等級劃分,也是以這種觀點為基礎。韋伯根據調性之間主音的關系而劃分了三個調關系等級。?有關韋伯的調關系網,參見注⑥,第745 頁插圖25.1,以及相關論述。從斯氏團隊《教程》第51 章可以看到,該書對調關系做了四個等級的劃分,雖然這四個調性等級劃分與韋伯的劃分不完全一樣,但毫無疑問是受到韋伯三個調性等級劃分思想的啟發。
(九)大、小調和聲調性作為基礎?本節部分論述內容出自筆者的論文《劍橋西方音樂理論發展史給我們的啟示》,《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3 第3 期。
調性音樂(大小調風格音樂)從巴洛克早期(17 世紀)開始興起,此后一直在西方藝術音樂中占據統治地位,而且影響了西方世界以外的音樂文化。在巴洛克時期之前,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西方音樂一直是以教會調式音樂為中心。調式體系向大小調體系演變的過程是十分復雜的,其動因來自多方面,歸納起來有四點:(1)格拉雷安的十二調式理論的出現;(2)和弦概念的確立;(3)數字低音的出現;(4)調性終止式的出現。
1.格拉雷安的十二調式理論的出現
瑞士人文主義者海因里希·格拉雷安(Heinrich Glarean,1488—1563)在其1547年的著作《十二弦里拉》(Dodecachordon)中,最早提出了十二調式理論。在格拉雷安之前,西方音樂理論中只提到了八種教會調式:四種正調式——多利亞、弗里吉亞、利地亞、米克索利地亞,以及建立在這四種調式收束音下方四度音上的四個下調式(或“副調式”)——下多利亞、下弗里吉亞、下利地亞、下米克索利地亞。格拉雷安將調式種類擴充到十二個,新增加的調式是愛奧利亞(Aeolian)和伊奧尼亞(Ionian),以及各自下方四度音上的下愛奧利亞和下伊奧尼亞。正是他的新增加的這兩個調式,為大小調的確立奠定了基礎。格拉雷安曾經將B 音上的八度種型(octave species)[21]八度種型指的是在一個純八度音程當中連貫音符之間的特定音程順序。參見注⑥,第294 頁。所產生的兩個調式,稱為上愛奧尼亞和上弗里吉亞,但最終因為它的減五度而被廢棄。
2.和弦概念的確立
比格拉雷安晚出生近一個世紀的德國理論家約翰內斯·利皮烏斯,杜撰了術語“三和弦”(triadis)。而在利皮烏斯之前,威尼斯理論家焦塞佛·扎利諾在其著作《和聲的原則》中,已經提到了模糊的和弦概念。利皮烏斯還最早將六個正調式劃分為大調類和小調類兩種調式。
3.數字(通奏)低音的出現
從17 世紀開始,和聲導音的引入,逐漸瓦解了調式音樂并因此而產生了調性音樂,可以說,有無導音是調性音樂與調式音樂的分水嶺。和聲導音之所以能夠侵入調式音樂系統,主要歸功于數字低音實踐的興起。格雷戈里·巴尼特(Gregory Barnett)指出:“對于調性空間概念的最終形成,17世紀通奏低音實踐的三個基本原則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1)大、小三和弦作為基本和聲音響的使用;(2)出現了通用的音階和聲配置法(scale harmonizations),這種方法使通奏低音演奏者能夠在那些數字不充分或沒有數字的地方實現和聲;(3)在任何音高水平上伴奏或配和聲的能力”。(《劍橋史》,第400 頁)
在上述三個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則即音階和聲配置法,這種配置法可以將一個音階中的音級組織成一系列以主音為中心的和弦。17 世紀初有關通奏低音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安東尼奧·布魯斯基(Antonio Bruschi)出版于1711 年的著作《對位法與通奏低音伴奏的規則》(Regole per il contrapunto e per l’accompagnatura del basso continuo),該著作提供的指導方針是:低音的“音級、和所配的和聲是完滿三和弦,音級、、和所配的和聲是六和弦”。(《劍橋史》,第401 頁)
關于音階和聲配置法的價值,巴尼特指出:“這種音階和聲配置法最終產生的意義有如下幾點:第一,我們可以認清建立在音級、和之上的原位正和弦和建立在音級、、和之上的副六和弦之間的區別;第二,我們還可以推斷布魯斯基的tuono(調式)所包含的調性概念,它的種類就是大或小;第三,在大調和小調第五音級上方使用大三度,保障了導音。簡而言之,三和弦的和聲與調性和聲功能均在這些八度和聲配置法中得到發展”。(《劍橋史》,第403 頁)
音階和聲配置法也叫作“八度法則”。較早提出“八度法則”(Règle de l’octave)的是法國吉他演奏家弗朗索瓦·坎皮恩(Fran?ois Campion,1748 年 去 世)。他 在其1716 年的著作《再論伴奏與作曲法》(Addition au Traité de l’accompagnement et de composition)中,在“八度法則”的標題之下,通過數字低音記號,給上行和下行的大音階和旋律小音階配置了標準和聲,他把這種配置法確立為和聲續進的典范。
坎皮恩的著作出版7 年之后,拉莫在其1722 年出版的《論和聲》中也給出了他的“八度法則”范例,但拉莫沒有采用這個術語。拉莫在第四卷第七章“各調八度內和弦續進必須遵循的順序”中,給出了他與坎皮恩略有不同的“八度法則”數字低音。譜例5[22]引自《論和聲》第四卷,例IV-17。在巴洛克時期,沒有任何一位作曲家的數字低音記號是通用的,拉莫著作中的數字低音記號更加不通用。中的羅馬數字和弦標記是筆者補充的。

譜例5 拉莫的“八度法則”
4.調性終止式的出現
理論家普遍認為,實際音樂作品中調性的確立,應該歸功于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1567—1643)。他早期作品的創作,主要體現的是調式思維,而他中、晚期作品的創作,特別是1607 年的歌劇《奧菲歐》(L’Orfeo),則比較明確地體現了調性思維。在《奧菲歐》第二幕“Mira,deh mira Orfeo”第10—12 小節,對位化的寫作方式與和弦化的寫作方式平分秋色,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重屬和弦到屬和弦的解決(V/V—V)、阻礙終止(V7—VI),以及對位化的V—I。
17 世紀晚期出現了多種以通奏低音為基礎的概念,包括各種終止式。意大利作曲家和理論家洛倫佐·彭納(Lorenzo Penna)在其1672 年的著作《音樂的萌芽時期》(Li primi albori musicali)中提出了四類終止。前兩類終止的特點是:“‘第一類終止’,是由下跳五度或上跳四度的低音構成的和聲;‘第二類終止’,是由下跳四度或上跳五度的低音構成的和聲”。(《劍橋史》,第406 頁)他的描述強調的是低音的特性音程進行,如果僅從低音進行來看,這兩種進行無疑為后來拉莫的完滿終止和不規則終止,即后來調性和聲中的正格終止和變格終止的劃分奠定了基礎。
在復音音樂不斷發展的同時,早在16世紀的歐洲世俗大眾音樂中,例如,法國和意大利的坎佐內(canzone)、弗羅托拉(frottole)和維拉內拉(villanelle),就已經開始呈現出與教堂音樂不一致的和聲配置。這類音樂體裁的和聲配置,更強調和弦進行以及完滿的終止進行。當然,當時還不存在“完滿終止”的概念和這種概念的清晰表達。當時的音樂家發現,一個具有完滿終結感的終止式,需要在主和弦之前使用屬和弦和下屬和弦。但是,隨之而產生了一個實踐問題,按照胡戈·里曼的說法:“如果不借助于偽音的輔助——對嚴格自然音調式的偏離,沒有任何一個教會調式會獲得完滿的終止感。”[23]Riemann, Hugo. Catechism of Musical History.London: Augener & Co., 1892. p.140. 該書原德文版1888年出版。上文已經提到,17 世紀出現的通奏低音實踐,已經確立了屬和弦使用大三和弦的規則,為的是確保導音的存在,而屬和弦所包含的導音對主音的傾向性,恰恰是屬和弦進行到主和弦的關鍵要素。
從調式特點看,大調下屬和弦是大三和弦,小調下屬和弦是小三和弦。在格拉雷安引進新調式之前,只有四種教會調式(指正調式),這四種調式要滿足屬和弦和下屬和弦的性質要求,就必須運用偽音(變音)。在譜例6 中,T(t)、S(s)、D 分別代表大小主、大小下屬和大屬和弦。多利亞調式的六級音(B),需要降半音來滿足小和弦的需求;利地亞調式的四級音(B),需要降半音來滿足主音下方純五度的要求;米克索利地亞調式的七級音(F),需要升高半音來滿足導音的要求。弗里吉亞比較特殊,它的七級音(D),需要升高半音來滿足導音的要求,同時還需要二級音(F)也要升高半音(#F)來配合升七級(#D)的使用,但在當時#F 的引進是不可思議的。對于弗里吉亞調式而言,它不存在屬和弦,無法形成正格進行,因此人們只能滿足于將該調式結束的小主和弦變成大和弦(E-#G-B),因而產生了盛行于巴洛克時期的“弗里吉亞終止”。

譜例6 四種教會調式的主和弦以及運用偽音所構成的屬和弦與下屬和弦
從譜例6 的和聲音級構成可以看出,除了弗里吉亞調式受影響不大外,其他三個調式因偽音的引進導致多利亞調式變成d 小調,利地亞變成F 大調,米克索利地亞變成G 大調。格拉雷安之所以引進伊奧尼亞(相當于自然大調)和愛奧利亞(相當于自然小調)這兩種新調式,為的是使音樂理論和實踐保持統一。引進伊奧尼亞調式后,大調類調式就不需要出現任何“偽音”,引進愛奧利亞后,小調類調式只需要出現升七級(#G),這種含有升七級的調式就是和聲小調(見譜例7)。這兩種調式被引進后,最初它們被認為等同于舊的調式,但不久后,這種關系就被顛倒了,舊的調式被認為等同于新調式,而且舊調式逐漸變成了背景,新調式變成主體,舊調式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總之,各種調式因為大屬和弦或小下屬和弦的使用而導致偽音的引進,為避免偽音使用帶來的不便,格拉雷安引進了伊奧尼亞和愛奧利亞調式,從此所有的教會調式(除了弗里吉亞)都喪失了各自原有的特性,最終演變成自然大調或和聲小調。而旋律小調則是和聲小調進一步演變的結果。[24]同注[23],第140—142 頁。雖然調式體系向大小調體系轉變,是在一個漫長的進程和復雜的理論演變中逐步完成的,但是決定性因素無疑是具有解決到主音傾向的和聲導音對調式音樂的入侵。可以說導音的入侵是這種轉變的催化劑。需要重申的是,音樂研究者必須建立起正確的導音概念,否則就無法正確認識調式音樂與調性音樂的區別,同時也無法正確認識傳統調性和聲體系的本質。
調性音樂在20 世紀初的現代嚴肅音樂創作中逐漸開始瓦解,隨之一同瓦解的當然還有調性和聲。取而代之的是放棄了傳統和聲的調性模糊或無調性的各種先鋒派作曲手法。但是,20 世紀以來,仍有許多調性和聲著作出版,但這些著作的理論體系沒有真正的創新,基本上均體現了對17—19 世紀和聲理論概念或要素的重新整合或進一步完善。
二、和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西方和聲理論向中國傳入的過程有點曲折,最初是先從日本傳入,后來再從西方傳入。傳入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大約1900—1949 年,這個階段是一個和聲理論向中國緩慢和零散傳播的時期。傳入中國的媒介是幾位曾經留學海外的中國學者撰寫并發表的相關文章或者自編教材。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音樂理論在內的西方音樂文化之所以能夠跨越語言障礙而傳入中國,最重要的依托是西方音樂在日本的普及。
始于19 世紀60 年代末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開啟了日本全盤西化的現代化改革運動,學習西方音樂文化是日本提倡的文明開化,以及現代化教育的組成部分。到19 世紀末,日本有多部重要的音樂理論著作或譯著問世,例如,內田弘一翻譯的《音樂捷徑》(L.W. Mason 著,1883),神津元翻譯的《樂典》(J.W. Callcott 著,1883),鳥居忱的著作《音樂理論》(1891)和鈴木米次郎翻譯的《新編音樂理論》(Ouseley 著,1892),等等。常用的音樂基本理論術語都出現在這些著作當中。到19 世紀末,日本學者已經基本完成了西方音樂理論常用術語的日譯統一化或標準化的工作,而且大部分術語采用了漢字譯名。我們今天熟知的絕大多數漢語音樂理論術語,都是直接來自這個時期確立的日語漢字譯名,例如,音階、音域、音程、拍子、和弦、導音、旋律、聲部、樂句和轉調等。[25]參見朱京偉《近現代以來我國音樂術語的形成與確立》,《中國音樂學》1998 年第2 期,第103 頁。此外,在大正時期(1912—1926),日本理論家又補充了演唱演奏以及曲式方面的術語,例如二重唱、四重唱、混聲合唱、交響詩、協奏曲、諧謔曲和 變奏曲等。常用音樂術語日譯標準化的確立,不但為西方音樂在日本的普及奠定了基礎,實際上也為西方音樂文化隨后在中國的普及作了鋪墊。
1896 年,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僅幾年的時間,清朝留學生累計有八千余人,其中包含了學習音樂的留學生。毫無疑問,這個時期的留日學生參考的是明治末期出版的這些著作。[26]同注[25],第105—106 頁。日語術語與漢語相通的便利,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西方音樂文化,以及日后將西方音樂文化向中國大眾譯介,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捷徑。
就和聲理論而言,留學日本的曾志忞(1879—1929)1905 年發表在《醒獅》雜志上的《和聲略意》[27]《醒獅》雜志由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該文發表在第1 期的“音樂欄目”,續文發表于第3 期同一欄目。參見唐吳瓊、陳林《從〈樂理大意〉到〈和聲略意〉》,《人民音樂》2018 年第3 期。一文,可能是用中文介紹西方和聲知識的第一篇文章。1914 年出版的高硯耘譯、曾志忞校正的《和聲學》,是我國第一部和聲理論著作。早年留學日本,后又留學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的蕭友梅(1884—1940)編寫的《和聲學綱要》,于1920—1921 年連載于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的《音樂雜志》。幾年后,蕭友梅將他的《和聲學綱要》進行修訂,1927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和聲學》。[28]參見劉冬云《蕭友梅〈和聲學〉研究》,《音樂研究》2015 年第3 期。上述的和聲著述還算不上系統的和聲理論著作,主要是和聲知識的介紹,但這些著述的作者都有留學日本的背景,他們在寫作時所參考的資料一定離不開日文文獻。從20 世紀30 年代開始,國內學者更加重視西方和聲理論著作的直接翻譯引進,到1949 年之前,中國出版的重要譯著包括:賀綠汀翻譯的(英)埃比尼澤·普勞特《和聲學理論與實踐》(英文首版1889,中文版1936);張洪島翻譯的(俄)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和聲學實用教程》(俄文首版1886,中文版1936);[29]這個譯本包含了個別重要術語的翻譯錯誤,例如,第113 頁的“等音轉調”(энгармоническoй модуляции)被誤譯為“四分音轉調”。趙沨翻譯的(美)普雷斯頓·瓦雷·奧瑞姆《和聲的初步》(英文版1916,中文版1948);等等。
第二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前16 年(1949—1965),這是一個和聲理論向中國快速和系統的傳播期,19 世紀末至20 世紀上半葉的西方以及俄羅斯的多部和聲理論教科書,通過翻譯出版而被引入中國。較為重要的譯著包括繆天瑞編譯的(美)該丘斯《和聲學》[30]其英文書名為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ne-Relation(《音關系的理論與應用》)。1962 年出版了中文修訂本。(英文首版1892,1917年修訂,中文版1949);羅忠镕翻譯的(德)保羅·興德米特《傳統和聲學》[31]1997 年該書中文版又以《傳統和聲學簡明教程》的名稱出版。(英文版1942—1943,中文版1951);豐陳寶翻譯的(美)辟斯頓《和聲學》(英文首版1941,中文版1951);朱世民翻譯的斯氏團隊《教程》(中文版1957 年出版,由1947 年俄文版譯出);茅于潤翻譯的(奧)勛伯格《和聲的結構功能》(英文版1954,中文版1958);等等。新中國成立初期,因為政治原因,我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幾乎完全中斷,各行各業全部向蘇聯學習,當時有多部蘇聯和聲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在和聲理論方面,因為20 世紀50 年代到中國講學的蘇聯專家的推薦,斯氏團隊《教程》在中國成為和聲理論教學的骨干教材。1966—1977 年因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擾,沒有正式出版任何蘇聯或西方音樂理論的譯本,這十余年是一個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停滯期。
第三階段是從我國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 年至今天。這個階段是一個和聲理論向中國傳播的更新與完善期。在四十多年的時間里,20 世紀之后西方出版的不同音樂領域的著作被翻譯引進,有多部傳統和聲與現代和聲理論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以前缺少的西方重要和聲論著通過中譯本開始進入中國教師的視野。這個時期出版的重要譯著包括:陳敏譯、劉學嚴校的斯氏團隊《教程》(增訂重譯本1991);劉烈武翻譯的(美)文森特·珀西凱蒂《二十世紀和聲——音樂創作的理論與實踐》(英文首版1961,中文版1990);廖寶生翻譯的(法)泰奧多爾·杜布瓦《和聲學教程——理論與實踐》(法文版1921,中文版1997);杜曉十翻譯的(美)斯蒂凡·庫斯特卡與多蘿茜·佩恩合著《調性和聲——及二十世紀音樂概述》(中文版2010,由2009 英文第六版譯出);等等。這些譯本均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另外一部重要譯著是筆者翻譯的《劍橋西方音樂理論發展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Theory,英文版2002 年,中文版2011 年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屬于工具書,它對包括和聲理論在內的幾乎所有音樂理論學科或領域形成的源頭和發展歷史,進行了全面的梳理,為我們研究和聲理論及其他理論提供了可靠的學術理論與實證文獻的支撐。[32]本文論述的重點是傳統調性和聲,因而這里忽略了許多有關現代和聲或20 世紀和聲的漢譯本。
然而,國內翻譯引進的教科書均為應用性的,西方最重要的幾部具有奠基性、思辨性或應用性的經典和聲論著——扎利諾的《和聲的原則》(1558),拉莫的《論和聲》(1722),韋伯的《作曲藝術系統理論自學指南》(1817—1821 年第1 版),以及里曼的《簡明和聲學或和弦的調性功能理論》(1893),還沒有漢譯本。這幾部著作漢譯本的缺少,極大地影響了國內學者及師生對西方和聲理論演進過程的完整認識。例如,很少有人知道,在和聲理論發展史上,是扎利諾在其《和聲的原則》中,首次提出聲部進行中禁止使用平行五度、平行八度以及對斜關系等。扎利諾給出了兩個方面的理由,首先是從協和音程比率方面考慮,他認為,“具有相同比率的兩個協和音程,不可以上行或下行連接,必須插入其他音程”;此外他也是從聽覺上考慮,認為這些平行音程“盡管顯然不會在聲部之間產生不協和音程,但是卻有一種難以言表的貧乏和令人不快的效果”。[33]Zarlino, Gioseffo. The Art of Counterpoint. trans.Guy A. Marco and Claude V. Palisc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61.
盡管如此,我們基本上可以通過上述和聲譯著,看到西方應用和聲理論的大致面貌。以這些著作的理論為基礎,多位前輩中國教師對于適合中國五聲旋律風格的和聲理論,進行了探索并且編寫和出版了著作,例如,王振亞的《五聲音階及其和聲》(文光出版社1951 年版),黎英海的《漢族調式及其和聲》(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年版),等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