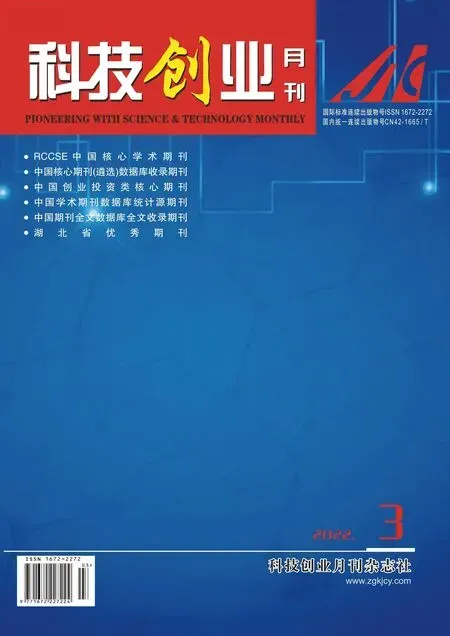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綜述與展望
謝曉潔 常華進
(1.華南協同創新研究院,廣東 東莞 523808;2.湖北文理學院 資源環境與旅游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0 引言
新型研發機構作為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科技企業孵化育成、高端人才集聚和培養等方面的載體,現已成為地方政府推進產業創新,打造創新驅動發展升級版的重要手段。當前,對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運行機制、政府支持、功能、評價與研究趨勢等方面,為推進其初期的建設與發展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但是,隨著總量增加與規模擴大,其內部結構優化、技術服務質量提升、政企協同發展發生結構變遷,需要對新型研發機構的結構層次進一步研究。通過文獻整理,按時空發展邏輯,運用文獻調研方法,歸納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的總體變遷現狀,用內容分析法凝練其研究的變遷過程,以此厘清研究脈絡,挖掘現有研究之不足,以期深化研究,為推進新型研發機構的升級建設提供針對性建議。
1 新型研發機構研究概況
在中國知網中對相關論文進行檢索,檢索篇名為新型研發機構,檢索時間截至2021年3月4日,獲得檢索條目263條,其中CSSCI來源期刊68條。通過詳細分析263篇以新型研發機構命名的文獻,從發表年度、研究主題、發表機構以及研究層次進行歸納總結,凝練出以下研究特征。
1.1 相關文獻數量快速增長,已成研究熱點
針對新型研發機構的研究近年在持續攀升。從文獻的數量來看,2012年4篇,2013年1篇,2014年22篇,2015年9篇,2016年13篇,2017年23篇,2018年39篇,2019年67篇,2020年75篇,2021年94篇(預測值),2015年之后,近5年的增長率分別為44.44%,76.92%,69.56%,71.79%,11.94%,平均年增長52.81%,對新型研發機構的相關研究增長快速(見圖1)。

圖1 發表年度趨勢
1.2 集中在對東部機構進行主題研究
對新型研發機構研究對象的屬地主要集中在東部發達區域,其命名方式開放,但重點突出事業單位性質的討論;研究主題關注內部結構發展,以發揮其科技成果轉化功能。首先,從文獻主題的角度來看,直接相關的研究240篇,區域主題的研究包括廣東省40篇、江蘇省9篇、吉林省7篇、東莞市5篇。發達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東北也開始重視這方面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廣東地區。其次,對機構主題的研究,包括新型研發機構、產業技術研究院、研究院、新型科研機構、高校院所、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發機構、先進技術研究院與科技部、事業單位。機構的名稱比較開放,且關注對單位性質的討論。再次,對功能主題的研究,主要圍繞科技成果轉化、創新驅動發展、協同創新、創新驅動、功能定位、產業轉型升級、成果轉化、科技創新、產業轉型升級、區域創新體系、產學研合作、產業化。對新型研發機構的定位,主要目標是促進成果轉化,推動產業發展。最后,對結構主題研究,包括科技體制改革、對策建議、發展模式、體制機制、研發團隊等,結構模塊的應然性選擇也足夠重視。
1.3 對廣東機構的研究已構成研究體系
廣東多家單位已對新型研發機構進行系列研究,成功豐碩。從發表機構篇數的角度來看,首先是廣東工業大學28篇,其次是廣東省科學技術廳17篇,第三是浙江大學7篇,第四是華南理工大學6篇、第五是南京工業大學5篇,第六是江蘇省生產力促進中心、清華大學、廣東省科技情報研究所、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和北京化工大學各4篇,第七是廣東省科技創新監測研究中心、黑龍江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華中科技大學、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創新科技雜志社和江蘇省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各3篇,其他少于3篇。可以看出,廣東工業大學、廣東省科學技術廳、華南理工大學、廣東省科技情報研究所和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等廣東政府機關、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研究數量較多,已形成系列研究,具有較深的探索。
1.4 為行業發展提供政策性與理論性指導
從新型研發機構的目標出發,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行業提供指導,為政府制定行業產業升級政策提供基礎理論與應用支持。按研究層次的角度分析,首先用于行業指導109篇,其次進行政策研究64篇,第三開展基礎研究44篇,第四進行工程技術研究7篇,第五進行經濟信息研究2篇,最后專業實用技術、職業指導、高級科普、基礎與應用基礎與等各1篇,96%的研究集中于行業指導、政策研究與基礎研究。
2 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的變遷過程
2003年,趙吟佳較早對新型研發機構建設進行討論,她提出從產學研合作、技術結群和產業集群三種資源進行組合,構建適應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研發體系。[1]2012年之后,新型研發機構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主要從功能、政策支持、運行機制、提質增效、評價、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變遷研究。
2.1 功能性研究具有拓展性
關于新型研發機構的作用,研究者主要從促進區域創新發展、人才培養和定位方面開展功能性變遷研究。
在區域創新發展研究方面,研究從省域到三角洲到發達板塊逐漸擴大。如陳雪[2,3]等先通過分析廣東新型科研機構的發展背景、特點與經驗,指出發揮其在創新創業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其有助于推動廣東省成果轉化;之后,劉志峰[4]等認為新型研發機構可以推動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最近,藺全錄[5]提出,新型研發機構有利于助推發達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新型研發機構在區域內的影響范圍在不斷擴大。
在人才培養研究方面,從人才培養的有效性到符合企業需要再到人才創新創業的內涵式蝶變。首先,張玉磊[6]等通過廣東省新型研發機構統計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用數據顯示了新型研發機構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有效性。之后,羅林波[7]等認為新型研發機構通過共同研究、協同創新進行產學研深度融合,為中國高校培養出符合企業需求的人才;羅嘉文[8]也表達了類似觀點。最后,陳雨婷[9]認為新型研發機構是理工科大學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的有效路徑。新型研發機構對人才的培養正從人才的利他型向利他利己型兼顧。
在功能定位研究方面,研究從模型向實踐,由平臺向生態轉變。在理論與實踐研究上,吳衛[10]等從理論模型展開推演,郭百濤[11]更進一步結合案例分析,明確了新型研發機構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厘清了其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而在平臺功能轉變研究方面,袁傳思[12]先通過對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聯盟組建類型和地域分布進行分析,探索新型研發機構在廣東產學研技術創新聯盟中的角色定位及作,之后李智毅[13]等研究者從打造創新生態,形成“平臺+環境”的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體系融合的模式,提出以軍地共建新型研發機構。
2.2 政府支持性研究更具時代針對性
政府支持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的研究,研究者借鑒了國外經驗,并從分類政策支持、綜合配套等措施方面更具時代針對性。
在借鑒國外經驗研究方面,從穩定支持性研究向激勵性支持研究的深化。丁明磊[14]等先在借鑒美國聯邦財政的支持經驗后,提出穩定支持、明確功能定位和出資人制度、拓展革命性和顛覆性技術研發支持渠道與機制及提升項目管理科學化水平的政策建議。之后,賀璇[15]建議強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賦予新型研發機構獨立運行的地位、完善新型研發機構激勵政策體系、引導科研人員向新型研發機構流動以及重點支持與均衡發展。研究者越來越具有市場化意識。
在分類支持研究方面,從分類支持投資主體,到支持區域產業協同,再到制定專項政策,研究對象發生需求性轉變。2015年,談力[16]等在分析不同投資主體形成的類別后,建議政府應根據新型研發機構各自不同的優勢與劣勢進行分類支持。兩年后,趙劍冬[17]等從組建模式、對接產業、區域分布和高校視角進行數據分析,提出重點支持和引導企業、大型央屬科研院所、高校主導建設不同定位的新型研發機構,對接區域產業并加強協同創新。最近兩年,楊詩煒[18]等又從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的視角,建議政府在完善新型研發機構政策部署時分類管理,聯合多個部門,從資金、土地、稅收等方面提供專項政策支持。隨著新型研發機構建設主體的確認,研究逐漸變成關注具體的落實效果與專項服務。
在配套支持研究方面,從綜合性宏觀基礎配套研究向專業化研究轉變。2017年,章熙春[19]等探索從政策、資金、性質、定位、組織結構等方面給出建議。同年,周恩德[20]等通過對湖北新型研發機構培育的理論基礎、政策基礎、經濟及產業基礎、科技創新基礎等的分析,設計機構培育路徑上的配套。 次年,張凡[21]從風險投資角度出發,討論了政府對新型研發機構風險投資的運行模式、評價體系,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任志寬[22]也從創投基金的發展模式出發,提出政府深化管理機制創新、強化培育和監管、積極引進社會資本,提高創投基金的管理能力和運作效率。
2.3 運行機制研究更具整合性
對新型研發機構運行機制的研究,研究者從模式選擇、主體運營、框架結構、促進競爭的角度進行變遷的整合過程研究。
第一,在模式選擇研究方面,從關注內部的定位管理模式,到機構間的協同模式,再到匯集外部資源的開放模式轉變。首先,朱建軍[23]等提出從定位出發,進行研發機構的新內涵和管理模式建設。之后,夏太壽[24]等對新型研發機構與傳統機構進行比較,通過分析協同創新模式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議。接著,周麗[25]基于大學職能擴展論、知識網絡復雜論、開放系統論和協同創新論,對高校新型研發機構運行機制進行了研究。最近,張玉磊[26]等認為開放式創新通過不同時空的創新資源在創新主體間流動,可最大限度釋放創新資源的價值,是高校型新型研發機構成長路徑的必然選擇。可以看出,對運行模式的研究,是一個從內到外的資源整合的發展模式的研究過程。
第二,在主體運營研究方面,從單主體研究向多主體研究轉變。首先,趙劍冬[27]等先對高校主導建設的廣東省級新型研發機構的現狀介紹及案例分析,建議各地高新技術園區應積極引導更多省內高校參加新型研發機構建設。之后,陳雪和原長弘[28-29]等從政府-發起單位雙元構建模式出發,提出創立和發展新型研發機構。最后,米銀俊[30]等從戰略生態位管理視角提出多主體參與的完全開放式創新模式。隨著新型研發機構的結構變遷,參與建設的主體在不斷增加。
第三,在框架設計研究方面,從案例提煉到頂層布局到子集群系統的集合研究的轉變。2017年,黎敏[31]從分析海爾集團開放創新平臺(HOPE)出發,提出設計思路,對總體框架、角色、平臺功能、關鍵資源運行進行設計,以實現科技體系的創新突破。一年后,陳紅喜[32]從理論模型結合經驗的形式進行研究,提出注重組織領導和頂層設計布局、探索混合所有制建設路徑、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項目落地孵化、注重財政專項支持與民間資本并舉、發揮考核評價對各利益相關方的引導作用。 最近,研究者還系統研究了框架下各個模塊的構建關系。如丁紅燕[33]等提出從創新動力機制、管理協調機制、要素配置機制及風險管理機制,四個子機制構建一個有機的、系統的整體,推動新型研發機構的持續創新。因此,對框架設計的研究是一個從個案上升到頂層,再兼顧內在系統的過程。
第四,從促進競爭角度研究方面,從核心能力模塊研究向結構化整合研究轉變。起初,賴志杰[34]等先從競爭力本源出發,認為要在技術能力、管理能力、資源能力、創新能力四個方面形成核心競爭力。而郭麗芳[35]等則從員工責任式創新行為出發,提出增強員工積極性及行為主動性,以提升機構競爭力的建議。同年,李穎[36]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從合作模式、企業需求和政策環境等角度,提出實現新型研發機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之后,周治[37]等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維度,提出要推動科研成果轉移轉化落地、進行科學布局、營造激勵性監管氛圍的對策。最近,周曉梅[38]則從整合機構的人才、技術和管理資源,創新高校與企業、高校與政府的合作機制、創新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機制與投資機制角度,提出發揮高校新型研發機構的創新創業服務效能。
2.4 提質增效研究呈現深刻性
隨著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的越發成熟,研究者從產學研融合、區域主體功能、完善組織、擴大資源角度開展提質增效的研究。
在產學研融合研究方面,從個案研究到機制研究。例如,丁珈[39]從“政產學研”深度融合的視角,以華中科技大學無錫新型研發機構為例,提出通過彌補高校技術成果到產業化之間的斷層,實現科研成果到產業支撐引領的轉變。而任志寬[40]則從產學研合作的運作機制,提出提高產學研合作效率的應對策略。對新型研發機構在提升產學研融合的效率上,研究者已從個體案例進入機制建設的探討,研究越發成熟。
在區域主體功能研究方面,從主體研究的擴展到主體研究的再認識。在單個主體上,龍云鳳[41]從民辦非企新型研發機構的功能定位和管理模式入手,通過系統地剖析“民辦官助”的“三元循環悖論”的作用機制,提出在政府和機構兩個層面的構建方略。在片區主體上,劉玲[42]等通過分析了新疆建設新型研發機構的形勢與建設基礎,提出了提質增效的建設對策。在關聯主體上,王文龍等從培養和發掘校友力,創新工作模式的角度研究新型研發機構建設。[43]在發起主體上,羅嘉文[44]等從高校發揮新型研發機構實效性出發,強調對激勵保障機制、利益協調機制、技術保護機制、協同創新機制、政策落地機制進行完善,提出通過進一步加強政府頂層設計、調動高校積極性、提升自身建設能力,提高新型研發機構發展的合力和動力。[45]通過對主體研究的不斷深化,研究者們再次回到發起主體的作用上,重新認識了發起主體的初始作用。
在完善組織結構研究方面,從完善組織形式的結構性研究到具體政策與措施等因素的實踐研究。首先,陳少毅[46]等針對新型研發機構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瓶頸問題和制約因素,從完善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提出建議。同年,周恩德[47]等運用層次回歸分析法實證研究中國新型研發機構創新績效影響因素,提出增加政府支持與構建內部績效考評體系的建議。次年,譚小琴[48]從“三維創新”提出聯結知識鏈、資本鏈和政策鏈,幫助新型研發機構跨越“死亡谷”。之后,王亞煦[49]等針對市場資源、高端人才、培養體系、體制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搭建市場化創新平臺,引育高端化創新人才,設計多樣化培養體系,完善科學化體制機制的實踐路徑。 可以看出,研究者針對組織形式的研究,根據建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不斷地針對具體版塊,提出實踐性應對措施。
2.5 評價研究中的模型建設更具可測性
對新型研發機構的評價,研究者從體系建設、模型構建、運行監測進行了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的研究。在評價體系上,陳紅喜[50]首先通過剖析南京市“兩落地一融合”工程建設新型研發機構過程,初步構建以產業化為目標的新型研發機構成果轉化擴散績效多維度評價體系。楊博文[51]則從科研投入、創新產出質量、成果轉化、原創價值、實際貢獻、人才集聚和培養六個方面,構建三層次多指標評價體系。之后,在評價傾向上,孟溦[52]等從資源依賴和社會影響力雙重視角,針對其不同階段關鍵績效特征建構關鍵績效指標與評估重點。而在模型建構上,陳雪[53]等先通過對新型研發機構開展競爭力研究,建立了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及測算方法。次年,郭百濤[54]等從研發條件、創新活動、創新效益以及人力資源4個維度設計產業化導向的績效評價模型。之后,任志寬[55]等則從廣東省新型研發機構創新監測平臺的運行情況出發,討論了對新型研發機構系統管理運營評價。可以看出,評價體系的研究過程經歷了“初步的體系建構-突出傾向指標-構建模型-實踐運行評價”的研究過程。
2.6 研究趨勢兼具具體性與實用性
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的未來趨勢,將呈現具體化、生態化、實踐性的特征。2018年,徐頑強[56]等通過對2001—2016年國內新型研發機構相關文獻的研究,認為現在的研究視角停留在宏觀層面,未來的研究將要更加微觀和具體。同年,張玉磊[57,58]等從年份分布、空間分布、主要期刊分析,并從研究知識模塊、研究切入角度和研究趨勢拓展3個方面解剖現有知識斷層,提出未來的研究趨勢。次年,楊詩煒等從新型研發機構作為官產學等多創新主體“耦合”的角度出發,提出構建一個創新生態范式,形成完整的理論框架和實證探索路徑。[59]可以說,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的總體趨勢是往具體化、生態化、實踐化方向發展。
3 新型研發機構研究的展望
隨著新型研發機構的結構變遷,需要對新結構下的模式、政府政策與資金支持、外部協調機制與內部改革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以推進其優化提升。
3.1 促進新結構模式建設的研究
第一,進行創新生態系統比較研究。由于建設主體發生變遷,形成不同類型新型研發機構,構成形式相異的創新生態系統。那么,這些創新生態系統有何不同?在不同的建設主體下,那一種創新生態系統是最有效的生態模式?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區域的創新水平,促進產業升級。哪些是在目前的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保留并加強支持的?哪些是可以在這變遷過程中進行淘汰的?這是結構變遷后,推進新型研發機構發展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二,開展新運行模式的仿真與實踐性研究。隨著新型研發機構的運行結構發生變遷,研究者已對最初的建設框架進行新的設計,但還有許多仍停留在理論層面,未能在現實層面得以實踐。這些新設計的建設框架,有多少能被新用于現實建設中?能否達到其設想的實際應用效果,需要研究者開展新理論應用的實踐研究,進行二次模型提取,使相關框架設計根據不同區域的需要發揮作用。
3.2 推進新結構支持性政策的研究
一是實施支持性政策的比較研究。借鑒國外經驗研究上,研究者開展了穩定性支持研究與激勵性支持研究。隨著理論的實踐,哪一種支持性政策更能推動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還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選用不同的支持性政策?對這些實踐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并提出更好的取代性或結合性模式,是推動新型研發機構應用研究發展的重要課題。
二是推行配套性政策的具體化研究。對新型研發機構的配套性支持研究,現有的研究僅限于對新型研發機構公共職能的支持研究,這種支持性建議比較模糊,對發起建設的地方政府與研究院來說,可操作性不強,難以獲得有效的借鑒。隨著建設的結構變遷與市場化程度的深化,如何按照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變遷,對這些“四不像”的新型研發機構給予合理有效的支持,是地方政府與重點高校舉辦新型研發機構面臨著的實際問題。因此,對于新型研發機構的配套性支持研究,研究者需要從具體設定配套資金支持比例出發,設計可以給出明確的可靠的計算模型。
3.3 增進新結構協同機制的研究
首先,實踐型人才協調機制的效用性研究。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新型研發機構逐步采用市場化運作,但是,外部的協調機制無法改變,造成外部協調緩慢;內部的激勵配套機制未能及時建立,導致內部管理失衡。結果,抑制了員工的勞動積極性與創造力,出現周期性人才培養達不到期望效果,人才流動率過高等問題。因此,在新型研發機構市場化的變遷過程中,內部如何建立高效的協調機制,提高人才培養效果,留住人才,擴大團隊力量,是需要突破的新問題。
其次,展開地方政府-機構協同機制研究。隨著區域功能板塊的擴大,產業結構的容納性發生變化;與此同時,創新主體的數量增加,創新結構同樣發生變化。結果,出現新的結構要素,需要在新的結構體系中進行協調,以揚長避短,形成合力,最大效力地促進區域創新發展。這需要學者根據外部的新條件開展協同機制研究,為地方政府與新型研發機構建立新的協同機制提供新的政策建議,以構建良性的協同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