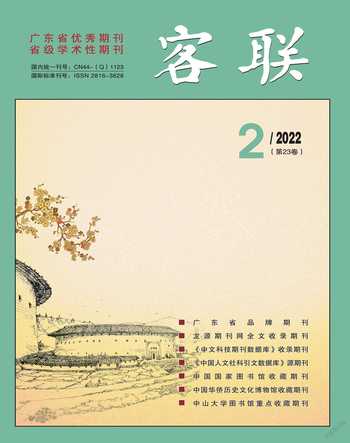《民法典》第369條的解釋論展開
楊凱
摘 要:居住權包括社會性居住權和投資性居住權,其權利定位為用益物權,人役權屬性應當有所削弱。立法上雖未明文規定法定居住權,但法定居住權尚有存在空間。居住權的權利主體應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對居住權設立對象“住宅”,應解釋為房屋。對于投資性居住權,可以通過約定,以直接或間接實現出租、轉讓、繼承的法律效果。
關鍵詞:居住權;用益物權;投資性居住權;居住權權能
一、規范意旨
居住權制度濫觴于羅馬法。在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由于無夫權婚姻和奴隸的解放的事件頻發,每當家長亡故,那些沒有繼承權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便成了問題。因此,丈夫和家主就把一部分家產的使用權、收益權等遺贈給妻或被解放的奴隸,使他們生有所靠、老有所養。[1]故而居住權制度自始就存在著保護弱勢群體的意旨,這一功能也因居住權制度的沿襲而得到保留。居住權作為一種人役權,專為特定人利益而設,故而居住權具有人身專屬性的特征,不得轉讓和繼承,原則上也不得出租。我國民法典第366條雖明確居住權為一種用益物權,但是仍部分保留了其人役權的屬性。
隨著時代的變化和需求的不斷擴大,人們對于“住有所居”的需求也不斷膨脹,但是現有的以房屋買賣和房屋租賃為主的二元房屋供給體系難以滿足多數人的需求。[2]居住權的規定不僅給房屋所有權人提供了一種更為多元的利用方式,也兼顧了居住權人穩定的居住利益,從而有利于實現房屋價值多元化利用、人民住有所居的規范目標。對于此種類型的居住權,不能與古羅馬時期的居住權一概而論,其人役權屬性有所削弱,故而立法上承認,當事人另行約定,使得居住權人可以出租房屋,實現居住權從人役權屬性向用益物權屬性的傾斜。有學者也將此種類型的居住權稱為投資性居住權。[3]
二、居住權的適用領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制定以來,立法上雖沒有承認居住權規范,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大量的居住權糾紛案件。即使當時在立法上沒有明確居住權的規定,但是也有部分地區法院法官富有創造力地部分承認了當事人享有居住權,其裁判理由或基于公序良俗原則、或將居住權解釋為所有權。[4]如今看來,這些判決在邏輯上都或多或少存在弊端,但是不可基于此否定這些判決的作用。這些判決明確了未來居住權規范可能適用的領域。
(一)為保障特定群體居住利益的社會性居住權
1.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居住權
據學者統計,因婚姻家庭關系中產生的居住權糾紛案例總件居于所有居住權糾紛案例中的第二位。[5]在家庭關系中的老人以及離婚后配偶的居住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有學者認為在婚姻家庭中老人、配偶的居住利益可以通過婚姻法、繼承法的相關規定予以保障,而無需通過設置居住權進行保障。[6]然而,婚姻法、繼承法中關于、老人居住利益的規定含糊不清,婚姻家庭關系糾紛解決又過于依靠許多道德與倫理因素,最終處于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老人和配偶的居住利益也難以獲得保障。多數學者認為,為老人、配偶設置居住權,以民事權利的方式確保老人、配偶的居住利益,可以確保老人以及配偶的居住利益。[7]
2.政策性居住保障房中的居住權
由于土地資源的緊缺和人口的迅速增長,房屋的價格也迅速的攀升,房屋購買或租賃的成本也不斷增加。所以各地響應黨中央十九大號召“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宅制度”,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居住保障房,諸如經濟適用房、共有產權房以及廉租房等等。其中對于共有產權房,其到底采何種權利結構,引發學者討論。目前大部分學者認為國家和個人對于共有產權房處于一種按份共有的權利樣態。但是采用按份共有的權利結構可能會引發一系列問題,例如房屋的管理維修義務、共有份額的轉讓等等[4]。進而有學者主張由國家享有空虛所有權,另一方當事人享有居住權,從而一方面確保特定人群享有居住權,實現其居住利益,另一方面也抑制市場上存在的投機行為。此觀點值得贊同。
(二)為實現所有權人財產利用自由的投資性居住權
1.以房養老模式中的居住權
由于現代中國社會典型的“四個老人、二個夫妻、一個孩子”的傳統家庭結構,老人很難一直與其子女一同生活,而其年老又無生活來源,老人養老問題頗為嚴重。以房養老模式的出現,為中國養老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老人可以低于市價的價格將房屋所有權移轉為買方,并約定在所有權移轉后,為老人在房屋上設定居住權。此時老人的居住利益得以保障,還可以獲得足夠滿足生活需要的一筆資金,來解決自己的養老問題。買方也可以一個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得房屋的所有權。[8]當然可能的方式不僅此一種,若老人想把房屋留給自己的兒女,也可不讓渡其所有權,可與從事養老服務的人員約定:老人為其設定居住權,由保姆負擔老人的生活起居也未嘗不可。
2.合資建造房屋或者購買房屋時的居住權
由于房屋的價值過高,個人的購買能力有限,所以實踐中出現了有兩方以上當事人共同出資建造或者購買房屋。此處的當事人不僅指自然人之間共同出資[9],也包括法人之間[10]。出資的形式也不僅限于金錢,也可能是勞務或者具有經濟價值的財產權。雙方當事人可以約定由一方取得所有權,一方取得居住權。此時當事人可以以低于市價的方式各自獲得單獨所有權,另一方也可以以較為低廉的方式享受到穩定地居住利益。
三、對于《民法典》第366條的解釋
民法典第366條是對于居住權涵義的闡述,屬于不完全規范中的說明性規范。其中包含了有關居住權設立、權利定位以及內容的諸多要素,需要經解釋確定其基本內涵,以期明晰居住權的適用。
(一)權利主體:居住權人
居住權人一般為自然人,對于居住權人可否是法人,學者存在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居住權人應當僅限于自然人。[11]理由在于居住權主要是在于為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老人、配偶等弱勢群體而設,而外國立法例上存在的由法人享有居住利益的情形,非為居住權,而為用益權。所以應當將權利主體嚴格定位為自然人。筆者以為,此觀點沒有正確理解我國關于居住權的定位。眾多西歐國家的立法受到羅馬法的影響(法國在有關人役權立法上基本沿襲了羅馬法的規定),立法中關于用益權、使用權、居住權都有著詳細明確的規定。居住權作為使用權的一種,在主體、客體、權能上都受到嚴格的限定,對于居住權以外的情形由用益權進行補足,從而明確居住權與用益權的區分。在我國,居住權被定位為一種用益物權,并未采納羅馬法對于居住權的人役權定位,故而我國實證法上也沒有完整的用益權體系。我國立法者正確意識到居住權的設置并非僅有保障特定群體的居住利益的社會性功能,它還提供給了房屋所有權人更為靈活的投資利用渠道。[2]對于法人參與合資建房,從而享有的投資性居住權,法律沒有理由禁止。所以居住權的主體不一定僅限于自然人,尚包括法人、非法人組織。
需要注意的是居住權人對于特定的房屋享有居住利益,因其家庭生活的需要,最終享有居住利益的不僅為居住權人本人,尚包括其家庭成員、提供家庭服務的人員。但是這些人員并不因享有居住利益就成為居住權人,上述人員的居住利益從屬于居住權人的居住權。居住權人的居住權消滅后,上述人員自無任何權利繼續居住在此房屋。
(二)居住權的設定方式
民法典第366條規定:“居住權人有權根據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民法典第371條規定了“以遺囑的方式設定居住權的”。這兩條規定了居住權的設定方式。我國立法上似乎只承認了以意定方式設立居住權。學說上,也有學者主張,尚需規定法定居住權。[12]理由主要在于雖然法定居住權主要發生在婚姻、繼承、收養法律關系中,但是僅憑現在的婚姻家庭編的制度,無法解決復雜家庭關系中一些弱勢群體的居住問題。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這樣的案例:在“郭偉宏、劉愛珍訴郭國榮等一案”[13]中,郭國榮作為房屋的所有權人拒絕為其兒媳劉愛珍、孫子郭偉宏設立居住權,而劉愛珍、郭偉宏的居住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在不能形成設立居住權的合意而又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加以救濟的情形下,法院通過解釋確定了郭偉宏、劉愛珍的居住權。所以該學者的顧慮不無道理。
但是我國立法上是否真的排除了法定居住權呢?民法典第366條只是肯定了居住權可以依據合同約定產生,我們不能簡單地作反面解釋,進而排除法定居住權出現的可能。事實上,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居住權糾紛,大多都是因為房屋所有權人拒絕為對其具有扶養、照顧義務的親屬設立居住權,大多法院也均依照婚姻家庭法的相關規定,認可了親屬的居住權。故而法定居住權在我國是切實存在的,不能僅因未在法條中明文顯示,即斷然否定法定居住權的存在。
(三)權利客體:住宅
民法典第366條將居住權的設立對象認定為他人的住宅,似有以顯示與后文中“滿足生活居住需要”的協調一致之意。但是我們需要反思的是能夠滿足生活居住需要的就一定為他人的住宅呢?首先,住宅一詞的含義并未明確。就我國現有法律體系而言,住宅一詞并非僅在民法中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39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5條均有住宅一詞出現。其中住宅所指并非是指物理狀態上的住宅或者財產意義上的住宅,而是代表個人隱私、生活安寧的場所,包括但不限于小產權房、不能辦理房屋登記的違章建筑等等。顯然,作為居住權設立對象的住宅,并非此種含義。其次,能夠滿足生活居住需要的不一定為住宅,而應當為房屋。大多數學者也主張,此處的住宅應修改為“房屋”[14],或應當作“房屋”理解。將居住權的客體限定為住宅,會不當限制居住權的客體范圍,諸如酒店、員工公寓等房屋之上能否設立居住權則會陷入爭議。之前的物權法僅存在以土地使用權為核心的不動產用益物權體系,現如今居住權制度豐富了我國的不動產物權體系,更不應將其局限于對于家庭住宅的利用,從而限制了居住權作為用益物權應有的制度功能。故而筆者認為,對此處的住宅應作目的性擴張,進而將其解釋為可以滿足生活居住需要的房屋。
除此之外,尚需注意的是,在我國以國家土地所有權為主、集體土地所有權為輔的土地產權制度框架下,在其上建筑物建成之后,該建筑也僅能用于特定用途。若該土地使用權本身上本身不包含供他人居住的功能,其本身也不能成為居住權的設立客體。[15] 《民法典》第368條規定居住權采登記生效主義,故而不能辦理登記的小產權房以及一些其他建筑也不能成為居住權的設立對象。反之,若是具有利用上、構造上的獨立性,能夠在房產登記簿上登記的,即使為房屋的特定部分,如房屋中的一間房間,也可以成為居住權的設立客體。
(四)居住權的權能:占有、使用
居住權人對于房屋僅能以生活居住為目的進行占有或使用,民法典并未直接承認居住權具有收益的權能。其主要原因在于居住權制度在于滿足居住權人的生活居住需要,而非讓居住權人更有所得。[2]民法典369條規定,居住權不得轉讓、繼承,但可以經特別約定出租居住權人房屋,也有排除居住權收益權能之意。但是對于上文所談及的投資性居住權而言,直接排除其收益權能,似有不當。有學者也在民法典出臺之前提出修改該條的立法建議,但并未被采納。[16]其實由于規定居住權根據合同約定并經登記后有效設立,即已給予居住權人尋求收益的空間。
首先,居住權人可以與所有權人約定,在居住權期間內,可以出租房屋。居住權人與房屋的承租人對于房屋的占有和使用功能,基本是相同的。居住權人與承租人的權利義務關系也可以約定進而向居住權人趨同,例如房屋的修繕、管理也可以經約定由承租人負責。故而,通過合同約定可以類似實現居住權人法律地位的移轉。其次,雖然居住權禁止轉讓和繼承,也可以通過合同的手段加以規避。比如房屋所有權人分別與居住權人、居住權人的繼承人分別訂立居住權合同,房屋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的合同約定居住權期間,與居住權人的繼承人約定的居住權合同約定生效條件:若居住權人在居住期限屆滿前死亡,房屋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的繼承人約定居住權的合同生效,其居住權期限為剩余期限,從而變相地實現居住權的繼承。居住權的轉讓可以采用類似的附條件合同的方式加以規避,從而實現通過合同約定間接實現居住權人的收益權能。其中產生的交易成本,也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的經驗總結,進而形成穩定、高效地交易模式,格式文本,加以緩和。
雖然通過合同約定,可以實現對該條規范的規避,但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其是否構成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進而構成合同無效。正如上文所述,居住權可以分為社會性居住權以及投資性居住權,由于其各自功能目的不同,其制度規范也應作區別設計。對于社會性居住權,固然需要強調其人役權屬性,原則上無償設立,不得轉讓、繼承。對于投資性居住權,則需要強調其用益物權屬性,允許居住權人進行約定有償設立,也可以通過約定從而間接到達可以轉讓、繼承的效果。所以對于社會性居住權,一般房屋所有權人也不會與居住權人達成合意——允許居住權人出租、轉讓,若居住權人擅自轉讓其居住權,則構成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無效。對于投資性居住權,原則上需要所有權人與居住權人達成相應合意,居住權人才能出租,也允許通過約定以變相地實現轉讓、繼承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周析.羅馬法原論(上)[M].上海:商務印書館,1994.375-376.
[2]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領導小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理解與適用(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861.
[3] 申衛星.視野拓展與功能轉換:我國設立居住權必要性的多重視角[J].中國法學,2005(05): 82.
[4] 肖俊.“居住”如何成為一種物權——從羅馬法傳統到當代中國居住權立法[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9(03):102、104.
[5] 曾大鵬.居住權的司法困境、功能嬗變與立法重構[J].法學,2019(12):52.
[6] 陳信勇、藍鄧駿.居住權的源流及其立法的理性思考[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3(03):74.
[7] 錢明星.關于在我國物權法中設置居住權的幾個問題[J].中國法學,2001(05):15.
[8] 肖俊.空虛所有權交易與大陸法系的以房養老模式[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7(01):127.
[9] 參見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9民終764號民事判決書.
[10] 參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2017)鄂民再117號民事判決書.
[11] 孫憲忠、朱廣新主編.民法典評注_物權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20.238.
[12] 單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權規范的檢討和完善[J].當代法學,2019(01):12.
[13] 參見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泉民終字第2914號民事判決書.
[14] 魯曉明.“居住權”之定位與規則設計[J].中國法學,2019(03):237.
[15] 肖俊.居住權的定義與性質研究——從羅馬法到“民法典”的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12):88.
[16] 申衛星.從“居住有其屋”到“住有所居”——我國民法典分則創設居住權制度的立法構想[J].現代法學,2018(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