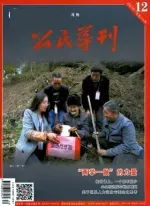吳富禮:森林守望者
周晏如



一個水壺、一條毛巾、一頂帽子、一架望遠鏡……凌晨5點多,整理好簡單的裝備后,吳富禮就騎著摩托來到界石鎮桂花村樵坪山腳下。
再步行10多分鐘,他爬上5層樓高的瞭望塔頂,開啟了一天的工作。
吳富禮是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員,每天的工作任務,就是守護“腳下”那7萬多畝森林的安全。
爬上瞭望塔的吳富禮,被汗水浸濕了衣衫,但他氣都沒喘一下。
“我今年68歲了。”吳富禮笑著說,在這山里守了這么多年,并沒有覺得自己老了,而是正老當益壯。
少小離家老大回
1954年,吳富禮出生在巴南區界石鎮一個普通的家庭。1972年,18歲的吳富禮前往西藏當兵。
之后,20歲的吳富禮到拉薩市城市建設局工作。
“在西藏那10余年,看慣了戈壁,見到綠色的植物,就覺得特別親近。”吳富禮回憶。
1983年,吳富禮申請調回重慶老巴縣,當時老巴縣房管局接收了他,他在那里干起了辦公室事務,打雜、出納……
不用風吹日曬,但吳富禮竟然覺得不習慣,他想親近綠色。
“我想回鄉下去。”吳富禮說得很堅定,因為再好的城市,在他眼里都比不上故鄉的一草一木。
就這樣,1983年冬天,吳富禮從城市回到了農村,從老巴縣房管局調到了界石林站。
“那時候,農村里家家戶戶都要撿柴火燒,什么枯樹枝、雜草、落葉,都有人搶著要,常常還有人私自砍伐樹木倒賣。”吳富禮說,看著曾經挺拔的樹木,一夜之間變成木頭樁子,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林站的工作就是,每周5個工作日,有4天都要到村(社)走訪調查。當時沒有交通工具,出行都是徒步,半個月就能磨破一雙嶄新的解放鞋。”吳富禮說,雖然那段時間非常艱苦,但他從來沒想過要放棄。
2000年后,隨著科學技術發展,農村都用上了煤炭和天然氣,山林里的枯枝再無人問津。但是這樣一來,山上哪怕是有一丁點火苗,都能成燎原之勢,所以接下來的十多年里,防火成了吳富禮最頭疼的問題。
“跟山火斗了這幾十年,別的不說,經驗很管用,不沖在前面就浪費了。”他說。
“千里眼”與“活地圖”
夏季來臨,吳富禮每天都要很早起來巡山。
清晨,天色稍見微熹,就借著這一點光,吳富禮徒步上山。
“因為三伏天是最熱的時候,早上又是氣溫最低的時候,如果有火情,要在9點以前打滅。”吳富禮說。
如果天氣不那么熱,吳富禮就把巡山時間放在下午或者傍晚之前。他說,傍晚也是容易起火的時候。
瞭望塔是一個狹窄的空間。
從塔頂向遠處極目遠眺,群山茂密,但那些人跡罕至的林中深處,每一條步道,吳富禮都能一眼辨別出來。
“東看南泉、樵坪山林區;南看界石、南彭、一品和銅鑼山山脈;西看南泉、橋口壩國家森林公園;北看長生、茶園、燕尾山……”站在塔頂環視,他對山林的每個位置了如指掌。
望著遠處的山林,吳富禮說:“那里有個煤場,三次起火都在那個附近,干旱高溫,煤炭很容易自燃,上次巴南山火也在那個附近。”
吳富禮在林站干了大半輩子,練就了“千里眼”和“活地圖”的絕活。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絕活”,吳富禮才在退休之后又回到了瞭望塔,擔負起森林防火瞭望員的重任。
“今年整個重慶持續高溫天氣,森林防火任務特別重,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望著遠處的山林,吳富禮堅定地說,一旦發現任何異動,他都會立即發出通報,防患于未然。
“雖然現在有了人防技防體系,瞭望塔相對‘原始,但實踐證明,這種‘原始方式依然不可或缺。”界石鎮桂花村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監控塔、無人機雖能做到全方位動態監測林區,但細致程度尚有欠缺,“尤其是火情發生之初,往往只是冒黑煙,監控設備對煙霧的敏感度較低,難以第一時間捕捉。而經驗豐富的瞭望員,往往僅是站在高處,就能憑經驗第一時間作出準確判斷。”
此外,若遇到森林大火,救火過程中及時掌握風向極其重要。但通過監控和地面觀察,很難準確辨別當下風向。這時,瞭望塔就是最佳的風向觀測點。
所以,森林防火瞭望員,依然起著關鍵性作用。
堅守信念的哨塔
春節要防煙花爆竹、清明要防祭祀煙火、春耕要防農戶燃燒雜草、高溫伏旱要防森林火災……護林工作沒有節假日。
從1983年到2012年,29載寒暑,吳富禮都像釘子一般深深扎在林區,他不怕高溫,不怕酷暑,堅持巡山,哪里有火災隱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每逢春節的時候,大家都在團圓,走親訪友,他卻一個人堅持守在林區。
有人說,從事看護森林的工作,需要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
可吳富禮卻云淡風輕地表示,“我習慣了,我要守在這里,心里才會踏實。”
吳富禮今年已經68歲,孩子在成都娶了媳婦、安了家。
他本應該在成都與妻子、孩子共享天倫之樂,但因為心中那份信念,毅然決然回到了界石。
“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工作這幾十年,我每天都要走很多路。”吳富禮說,他每天站在街邊就覺得熱,就喜歡往山里鉆,山里一片綠蔭又涼快。
離開妻兒或多或少都有不舍,但吳富禮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
他一邊吃著飯,一邊不時地拿出望遠鏡看一看。
“我在這里守了這么多年,始終還是舍不得。況且,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守護森林安全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吳富禮說。
“我從小就喜歡養白鴿。”吳富禮抓出籠子里的白鴿,挨個摸了摸。
他說,這些鴿子很乖,有的養了一兩年,最久的已經跟著他12年了,“不管在多遠的地方放飛,他們都知道回來。”
吳富禮就像他養的那些白鴿,無論飛多久,無論飛到了哪里,最后都會回到最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