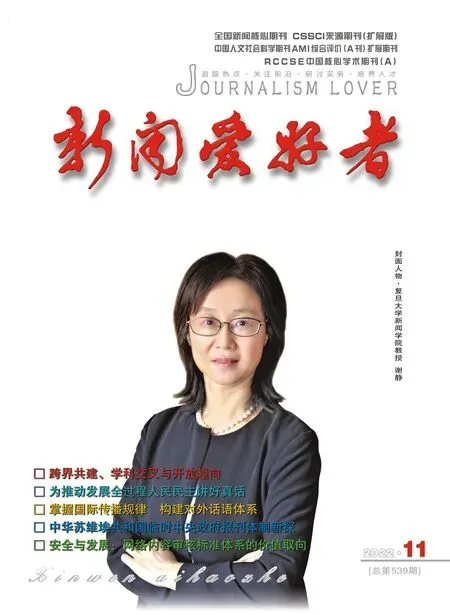媒介與全球治理的三重路徑
張暢
【摘要】當前,全球范圍內對媒介治理的研究還處于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狀態。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并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亟須給出媒介與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現對全球治理的概念進行剖析,提出媒介與全球治理研究的三重路徑:對媒介的全球治理、媒介參與的全球治理和通過媒介實現的全球治理,提升媒介在塑造全球意識、全球價值、全球認同和全球方案方面的主體性和建設性。
【關鍵詞】媒介治理;全球治理;國際傳播;互聯網治理;全球公共領域
“治理”的概念早在2002年就被愛爾蘭學者肖恩和吉拉德引入媒介研究的領域,媒介治理的概念也在2003年進入中國,但目前媒介治理研究尚有待進一步整合。其中存在三個問題:(1)媒介治理概念不清晰。當前學者們對媒介治理概念的使用既包括政府及公共機構對媒介的治理[1],又包括媒介集團的自我治理[2],還包括將媒介平臺納入到社會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過程。[3](2)媒介治理研究主要在國家治理范疇內開展,缺乏在全球層次的探索。目前對媒介治理的研究仍局限在國家、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難以擺脫方法論民族主義的窠臼。[4](3)媒介治理研究的碎片化傾向嚴重。當前有關媒介治理的研究向平臺治理方向聚攏,缺乏對全球媒介體系建設、價值觀念和互動模式的整體性思考。本文將通過對全球治理理論的梳理,提出媒介與全球治理的三重路徑,它們環環相扣,循環共生。通過連接、包容與賦權促進各行為主體對全球治理議題的平等協商,進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
一、羅西瑙式全球治理觀與對媒介的治理
媒介與全球治理研究的第一重路徑是對媒介的治理。“治理”一詞來源于法語詞匯“La Gouvernance”,在18世紀,它被廣泛用來指代一種與公民社會融洽相處的開明政府。[5]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治理”的概念再次復興,并用以指代與主權國家主導下的“統治”手段截然不同的政治管理過程。與“統治”不同,“治理”是全球化與現代性的產物,是權力彌散、權威轉換和邊界模糊化的一種自反性概念創新。[6]
羅西瑙式的全球治理文化具有四個特點:治理主體多元性,治理流程的辯證性與碎片化,行為體的次國家屬性和跨國家屬性,治理權威的重塑。在羅西瑙式全球治理觀的指導下開展的對媒介的治理是媒介規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一種延伸和拓展。用Manuel Puppis的話講,媒介治理是指一整套用以組織媒介系統的規制結構。[7]Sarikakis進一步對規制結構的特點進行了定義,她指出治理的概念有助于我們理解媒介如何在一系列正式/非正式的結構中,在時空分散的行為體互動中被形塑。[8]
全球媒介治理的目標隨著全球媒介體系與時代發展要求而演變。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媒介治理的核心在于改革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之間不平衡的信息流動,第三世界國家與西方左派學者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平臺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最終這次運動失敗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和兩極格局的終結,美式新自由主義與互聯網全球化一道席卷全球。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愛爾蘭學者肖恩和吉拉德倡議通過跨國公民運動來重建高質量的公共媒介服務,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包容、賦權、激發知識創造與自由流通的全球媒介治理體制。[9]在中國的語境下,這種重塑媒體公共性的責任更多地被賦予給了國家。[10]
這種多元多層協商共治的路徑在互聯網時代尤其受到全球治理學者的擁簇。美利堅大學教授Laura
DeNardis指出,依托信息社會世界峰會等平臺,互聯網治理實現了由政府管理向私營部門、認知共同體和公民組織等行為體共同參與,自下而上制定全球互聯網政策的轉變。[11]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安全問題、數據安全問題和經濟安全問題的日益凸顯,互聯網空間的全球治理實現了國家的回歸和再主權化。[12]隨著平臺化社會的到來,大型互聯網數字平臺以基礎設施的形式和邏輯融入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每個角落,以JoséVan Dijck為代表的學者呼吁理順國家、公民、市場三者的關系,建立一個更加民主、透明、公正、開放、負責的平臺管理機制。[13]平臺型媒介所具有的生成性和參與性使平臺所產生的內容效益和社會效應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也令多元主體模式的全球媒介治理成為必然。[14]
羅西瑙式的全球治理觀為全球化語境下的多元主體對媒介進行治理提供了理論進路。然而這種治理觀將媒介單純看作被治理的客體,沒有充分考慮其作為社會組織所具有的主體性。另外,這種治理理念忽視了平臺背后的政治權力邏輯,即網絡化、平臺化的全球媒介格局與國際權力分配高度重合的事實。因此,我們需要借用福柯的“治理術”和“話語/權力”概念重構媒介參與的全球治理理論框架。
二、福柯式全球治理觀:媒介參與的全球治理
如果說羅西瑙式的全球治理觀將我們引入一個百家爭鳴的美好愿景,福柯式的全球治理觀則帶領我們透視全球治理背后權力邏輯的變遷。福柯的理論為我們重新審視全球化視野下的媒介參與的治理提供了兩點啟發:一是福柯的“治理術”概念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媒介的主體性。二是媒介的權力與行動能力來自于對話語的建構,對知識的生產和對現實環境的表征。
首先,福柯認為現代國家的“治理術”通過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如健康、衛生、出生率和人均壽命等手段加以管理,而非單純依靠暴力懲罰或威脅。在這樣的理念下,生命政治的實施就在于使被統治者內化某種價值觀,成為能夠自我規訓的主體,進而促進整個權力體系完整運行。[15]在全球治理的場域中,媒介、公民社會和社團等組織因對自身所在團體和社會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和代表性,彌補了由統治向治理轉變的過程中,政府退場造成的權力真空。在中國,抖音一方面為消費者提供視頻娛樂服務,一方面通過響應政府促進地區間均衡發展,為人民群眾創造好生活的政策來彰顯自身的主體性。[16]其次,如福柯所說“話語能傳播、生產和強化權力,也能展示、弱化和消滅權力”。[17]在社會中最能集中動員符號化的力量進行話語生產和現實建構的組織莫過于媒介,[18]它能在全球范圍內塑造“擬態環境”[19],是塑造價值觀與認同的重要行為體。[20]例如吳詩晨和胡遠珍的研究就表明,在疫情期間,媒介對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過程的云直播就為全球觀眾提供了一道“媒介奇觀”,引發全球民眾對中國疫區建設者們的共情和對中國速度、中國能力的稱贊。[21]而此類活動在政治和外交意義上,將用以促進共同價值觀的建立以及外交互信和經濟合作。同樣受到“一帶一路”倡議啟發的沈悅和孫寶國則表示,中國媒介的國際化將成為形塑新型國際秩序的敘事空間,在跨文化協商中改變國際偏見,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22]
要發揮媒介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設性作用,需要對媒介的定位與倫理進行全球場域下的更新和再定義。建立在西方民主理論基礎上的新聞倫理集中在對客觀性、公正性、真實性等價值的關注上。新聞媒體上要起到對公權力的監督作用,下要起到為人民代言,守護人民民主的作用。[23]然而這種媒介倫理模型具有地理和身份意義上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基于民族國家范疇內的媒介往往承擔著構造“想象中的共同體”的作用。[24]二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媒介文化可能會損害地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自主權。[25]三是媒介的客觀性與中立性可能導致新聞報道缺乏一種全球化關懷。[26]
建立一套有利于全球治理的新聞倫理要求媒介從業者進行一場意識層面的自我變革,從一種對民族國家的忠誠發展為一種對全體人類的命運心懷責任的世界主義精神,也就是擁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盡管全球媒介格局中的霸權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但媒介內容的生產者若能減少由他者視角帶來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在歷史和社會的情境中理解其他文明的風俗、習慣、價值、信仰與生活方式,并能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傳播敘事,全球媒介信息流中則會包含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樣性。
三、哈貝馬斯式的全球治理觀:實現媒介的全球治理
如果說羅西瑙式的全球治理觀到福柯式的全球治理觀實現了媒介的主體性從無到有的轉換,那么哈貝馬斯式的全球治理觀則要求媒介主體性調節為一個紐帶性實體。哈貝馬斯的全球治理觀發源于哈氏哲學理念的兩個核心概念:“公共領域”和“交往理性”。前者為媒介在全球治理的實踐提供定位,后者為行為體在媒介化的公共領域中活動提供行為規范。
與福柯相同,哈貝馬斯對當代資本主義自由主義體系下國家公權力對私人領域的過度控制與干預表示擔憂和反思。福柯較為悲觀,只為我們揭示權力的運行規則,卻沒有給予解決方案。而哈貝馬斯則懷抱著一種懷舊式的浪漫主義色彩,將視野拉回到了18世紀的歐洲。在那里,他宣稱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公共領域。他主張在國家社會化和社會國家化的當代社會,重建能容納自由辯論和理性反思的公共領域,并由此搭建國家與社會間的橋梁,挽救民主危機。[27]
在全球化時代,建構媒介化的公共領域既有必要性,又有挑戰性。在時空延伸的背景下,Castells指出,一個涵蓋全球的公共領域需要通過互聯網和無線通信技術,為全球民眾的辯論、對話和集體決策提供組織的平臺與工具。[28]這樣一個理想化的全球公共領域的建立面臨三方面的挑戰:一是基礎設施的全覆蓋性。全球數字鴻溝對全球媒介公共領域的形成造成挑戰。聯合國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全球仍有37億人沒有連上互聯網,其中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女性。[29]二是全球價值認同的可到達性。公共領域的展開是以公民對民族國家的集體認同為基礎的,而共識的求得也要求以共同的文化標準與社會實踐為前提。[30]三是權力政治的侵擾。主權國家可能會將全球公共領域看作是一個國家利益的談判桌,通過操縱談判過程,將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施加到談判與協商過程中。[31]
在媒介化的全球公共領域,國際組織、主權國家、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商業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等行為體可以通過媒介平臺進行交流和互動。為更好地應對三方面挑戰,在基礎設施方面,互聯網與數字技術為商業機構提供了參與全球治理的新空間,借由數字“一帶一路”,民營企業可以參與到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多媒體網絡運營、全球性內容生產與分發過程中。在全球價值認同方面,主權國家及國際組織可借由公共外交,通過真誠、平等的溝通,塑造信任、共識與共同意義,為尋求符合全球廣泛利益的全球治理政策創造話語空間。在權力政治方面,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為互聯網時代通過媒介的全球治理制定了互動的行為規范,通過對各種觀點的賦權和包容促進全球范圍內政治共識的達成,使作為私人的個體以全球意識、全球價值和全球利益為藍圖建構成一個公民共同體。媒介化的公共領域,將為底層、邊緣化、弱勢群體賦能,允許他們將個體的、情感的表達上升到全球層面,借以抵御覆蓋在權力和資本之上的理性霸權。
四、結語
歷史的時鐘轉動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的洗禮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在應對如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球性挑戰中逐漸難以為繼。西方內部孕育出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浪潮和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內生性金融風險和貧富分化加劇,使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難以引領世界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機制創新推進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媒介與全球治理集合體的目的在于:第一,在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化的框架下,使媒介在羅西瑙式、福柯式和哈貝馬斯式的治理觀的基礎上與全球治理相融合。這要求全球主要行為體通過對媒介基礎設施、信息生產和分發機制的形塑,使媒介充分參與到全球意識、全球價值和全球認同的建構中,進而成為搭載全球民主協商,賦權全球公民社會的全球公共領域。全球媒介治理要實現對媒介的治理、媒介參與的治理與通過媒介的治理三個環節的動態平衡和循環促進。全球媒介治理的三重路徑要充分考慮全球治理的要求與媒介自身發展規律,平衡好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秩序與以公民個人為單位的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要求,統籌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其中,以媒介為治理對象的全球治理,要求政府、國際組織、企業、技術專家和個人等行為體協調互動,在多元多層治理模式的指導下,對媒介進行全球治理。第二,塑造媒介的主體性,充分發揮媒體的能動性,深度參與到塑造全球意識、全球價值、全球認同和全球方案的過程中。第三,媒介充分發揮好平臺作用,實現媒介的治理。這要求媒介同時協調好國家、市場、社會的關系和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系,為治理主體搭建溝通平臺,為全球公民社會塑造開放、平等、賦權、負責的公共領域。媒介與全球治理三重路徑的研究不僅將開創傳播學與國際政治研究的學科增長點,也將為推動全球媒介秩序的民主化,塑造對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的認同,提升中國在全球媒介治理中的地位,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諸多領域提供理論依據與現實啟發。
[本文為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俄烏沖突背景下俄羅斯輿論戰策略與效果研究”(2022M71294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李維安,常永新.中國傳媒集團公司治理模式探析[J].天津社會科學,2003(1):75-79.
[2]滕朋.社會治理,傳播空間與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路徑[J].當代傳播,2019(2):48-50.
[3]虞鑫,蘭旻.媒介治理: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媒介角色: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傳播與政治[J].當代傳播,2020(6):34-38.
[4]趙永華,王碩.全球治理視閾下“一帶一路”的媒體合作:理論、框架與路徑[J].國際新聞界,2016(1):86-103.
(作者為英國華威大學國際關系學博士、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師資博士后)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