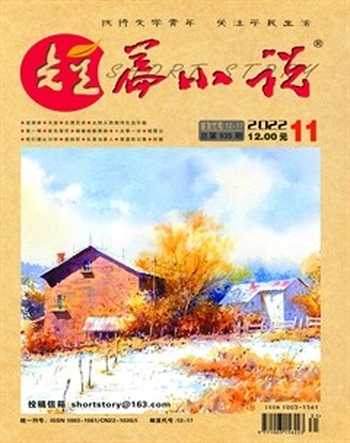太陽從西荊河東邊升起
彭永鋒

一
平原土地是肥沃的,只要輕輕一擠,就可以擠出金黃的菜籽油。不過,勤奮不擠。
太陽爬上西荊河頭頂的檔口,我和胡庸走訪來到勤奮家,大門緊閉。“出門趕集過早去了?”
胡庸搖搖頭,徑直走上前狠狠地拍著門,“勤奮,勤奮,王書記來看你了!”
屋里沒有回音。胡庸又連拍了幾下,還是沒有動靜。“算了,可能不在家,改天再來吧。”等我們轉身離開,走過相鄰的人家禾場,身后傳來開門的聲音。
勤奮瘦小的身影倚在門框里,左手攏進披在身上的衣袖,張口打出一個哈欠,滿嘴的齙牙便跑出了身體。“就知道他在家睡懶覺。”胡庸嘀咕了一句。
走訪的目的是為了制定幫扶措施。胡庸讓勤奮把流轉出去的七畝多地收回來自己種,增加收入。自從評上了低保,勤奮的耕地開始撂荒。鄰居看不下眼,商量勤奮,一畝地一年兩百元的流轉費,接下了拋荒地。翻過年,勤奮索性一股腦把承包地全部流轉給了鄰居耕種。
“你看我這身板,搞不動啊。”
“如今機耕機作,只需要你操心一下田間管理,一年少說也能多收入五六千。你呀,我看就是懶。”胡庸搖頭,罵一句,活該你窮一輩子。
“我一不偷二不搶,窮又沒礙著誰,知足,知足常樂,你懂不?你喜歡拼命掙錢你去掙,別拉上我。我活該,窮死跟你也沒有半毛錢的關系。”
勤奮懟過來幾句話,嚇了胡庸一跳,明明是在心里罵了一句,難道不小心罵出聲自己沒感覺,還是勤奮意念感知到了?
胡庸再一次搖搖頭,“神經病。”
“你才神經病,你們一家都是神經病。”勤奮揚起手臂指著胡庸,“別以為我人老實好欺負,你當個村干部就能隨便罵,告訴你,兔子急了還咬人。”
這次,胡庸確實罵出聲了。胡庸揮手打開勤奮揚起的手臂,一步上前,雙掌朝著勤奮胸前猛一推,“罵你怎么啦,欺負你又怎樣?你還能翻天?”
胡庸的步伐向前移動,手臂再次蓄力,準備第二次推向勤奮。不過此時勤奮踉蹌后退幾步,已經歪倒在墻角。“村干部打人啦!村干部打人啦!”勤奮倒地后迅速撐臂,屁股都離地好幾厘米了,卻又一軟癱坐在地叫嚷。這一瞬間發生得太快,不是我遲鈍,實在是我已經轉身走開幾步,背對著他們。直到胡庸提起腳要踹窩在墻邊叫罵的勤奮,我才沖到他身邊攔下他。
“出人命啦!村干部打人,出人命啦!王干部快救我!”雖然事后我極力給勤奮做工作,胡庸在我的要求下,也上門給勤奮道了歉,但勤奮當面原諒胡庸,背地里還是將告狀信寫到了縣、鎮紀委。
“窩囊。不干了,不干了。”胡庸分別跟我和張大山談心,不想給村里抹黑。
“好不容易培養一個干部,有頭腦,懂電腦,能付出,我可是指望他接班的。”張大山跟我說,“這點糾紛,不至于說要免職處理吧?王書記你是縣里下來的干部,關系廣,去縣紀委找找人,給個警告處分之類的,只要不免職就行。”
“其實,他主動辭職未必是壞事,這樣對上對下都好交代,甚至可以免予黨內處分。等到下半年換屆,再把他選上來,民意不可違,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至于這一段時間的工作,你們幾個村干部分擔一下,會計上的事情讓治保主任兼著,反正他遲早要接手會計。”
“平時挺穩重的一個人,怎么就動了氣?”我不理解。
“都是勤奮這家伙嘴賤,揍他活該。”張大山并不同情他這個遠房表侄。
“這狗日的,就該兩腳踹死他。”胡庸將煙頭扔在地上,用腳狠狠地碾,似乎腳下踩的是勤奮。
至于嗎?打心里講,我也不喜歡勤奮,不是我以貌取人,實在是勤奮尖嘴猴腮,長得不咋樣也就算了,整日里衣服沒一次穿得工整,且充滿污垢,像殺豬佬的圍裙。
偏偏數他找我最多,到村里接手駐村工作不到一個月,他找了我不下五次,每次也不明確地提要求,瞎侃拉呱,浪費我不少時間。在我到這個村之前,扶貧工作已經推進了三年,全村評定的貧困戶十九戶,都是因為疾病殘疾或者意外橫禍造成的家庭困難,唯獨只有勤奮,無病無災四肢健全,雖然掉了伴,但才五十出頭,兒子又在外打工,若換我早一步到村里駐村,肯定不會將他納入貧困戶。
“王干部,做飯呢。您在村里工作,辛苦、辛苦。”越是不想見,越是來得快。我剛炒了一個青菜,勤奮提著塑料袋,站在廚房門口說:“吃了午飯沒有?要不要加一點?”
他倚靠著門框,滿頭黑發有點油膩和凌亂,身上的金利來夾克污漬斑斑,松松垮垮罩著他瘦弱的軀體。顯然是接受捐贈的衣服。我見他喉結動了動,趕緊說,“我只炒了一點菜,飯也只做了一個人的,你若是吃,我再炒一個菜,下碗面。”
“不了,不了。”勤奮擺擺手,將提著的塑料袋放在餐桌上,“給您帶了幾個土雞蛋,您辛苦了,補補身體。”我打開袋子看了看,大約裝著十來個雞蛋。
“你家又沒有養雞,這雞蛋哪里來的?”
“親戚家討的,不是偷的,王書記放心,違法犯罪的事情我不做。”
“你還是帶回去,留著自己吃。我這里什么都不缺。你若是有什么事情直說。”
“我沒事,沒事,就是給王干部您拿幾個雞蛋來。”勤奮說完轉身小跑下了樓。我拎著雞蛋追了兩步,在樓梯口停下了。小廚房是在村辦公樓樓梯拐角的小屋,出了辦公樓,旁邊衛生站、小超市有不少老百姓,我不想為了幾個雞蛋在眾人面前和勤奮推推搡搡,更何況他已經跑遠了。
二
村里開會研究低保續保問題,十一戶二十五人,唯獨最后討論到勤奮的時候,三個副職沒有一個表態發言。
“有想法你們可以說,不能什么都不講。”我提示大家,“治保主任你分管這項工作,你先說。”
“我對業務還不熟。本來胡會計搞得好好的,都因為這個嘴賤的勤奮,領導也是,怎么能同意他辭職?”治保主任放下撥弄的手機,說話的語氣和平時不同,語速有點快,還有點結巴。
“這個問題不要說了,我們有我們的考慮。王書記讓你談勤奮續保的問題,你談這個就行。”張大山拿眼睛橫著治保主任說。
“禮都收了,態也表了,我還能說什么?按照領導的意圖辦唄。”治保主任垂下眼皮,說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耳語。話里有話,但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話。我用詢問的眼神看向張大山。張大山咳嗽一聲,吸了一口煙。“說了王書記別生氣。有群眾跟我反映,說勤奮先前給您送了禮,他的低保續保問題您表態了,妥妥的,村里只要有一個低保名額,那肯定是他的。”
我猛然想起廚房里勤奮拿給我的雞蛋,已經吃得只剩下一個。當初我讓胡庸拿去退給勤奮,胡庸不干,還說吃他幾個雞蛋又不違紀。我想也是,才十一個雞蛋,一斤來重,頂多十塊錢,偶爾早上煮一個雞蛋吃也不錯,再說當時勤奮也沒跟我說啥,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操,跟我玩套路。我在心里罵一句。“態沒表過,收了他十一個雞蛋,已經吃了。大家不用考慮我這個問題。”我掏出一百元錢,遞向婦女主任,“你幫我去買十斤雞蛋,回頭和我一起送給勤奮。”
“既然領導這么說,我的態度是不同意勤奮續保。”治保主任挪了挪屁股。
三個副職意見一致,張大山看向我。“就按你們的意見辦,我沒有意見。”說完我在心里又罵一句。
喊來村民代表和黨員,準備召開低保續保評議會議,我接到單位一把手的電話。他詢問工作開展情況,說單位正在考慮安排一筆資金用于村里搞建設,最后他說,“勤奮是我包聯的貧困戶,聽說村里考慮取消他的低保。村里的意見我不反對,但你作為我們單位派駐的第一書記,我包聯的貧困戶不能脫貧,你是有責任的。低保取消后,勤奮的收入問題你要安排好。另外如果他因此上訪,發生影響穩定大局的事情,你和村里都要負責。”
我明白,這個電話是專門為勤奮低保續保打的。但我不明白的是,這么快一把手就關注到了。難道勤奮聽到風聲,找了一把手?我趕緊找張大山,商議貫徹落實一把手的指示精神。“當初若不是你們單位一把手提議,我們沒打算將勤奮納入貧困戶并給他搞低保。本來就懶的一個人,自從有了低保,七畝多地一分不剩全流轉出去,一年的流轉費才一千五,還不夠他抽煙喝酒。如果政策是養懶漢,那還不如不要。”張大山搖搖頭說。
“單位正在研究拿一筆資金給村里搞建設,這兩年也沒少支持村里。領導考慮也沒錯,勤奮這個人是懶了點,但看他家里,也確實窮酸,低保取消了,他生活都困難,到時候纏著領導上訪,最終還是要解決,不如主動一點。”
“行吧。”張大山苦笑一聲,搖搖頭說,“我來做工作。”
這一點我很欣賞張大山,六十有三的人,本應該退休回家帶孫子,就因為鎮里要求,留任在位沒有一點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想法,依然兢兢業業,大局意識和政治意識不輸于縣直單位的任何班子成員。張大山在會上用了三句話把這個事說清楚了。第一句他說縣財政局沒少給錢幫助村里搞建設,近期又在研究拿一筆錢給村里修路。第二句話說勤奮是局長的包聯對象,局長很關心他,勤奮懶惰大家都知道,取消低保他沒了收入,沒有收入去找局長,局長會責怪我們沒把工作做好,以后對我們的支持幫助減少,鋪路修渠搞不下去,大家不要怪村里。第三句話說勤奮這個人有點二百五大家都曉得,取消低保他若到處找領導要飯吃,村里就把他領回來送到反對他續保的人家里把他養起來。
這樣說,既減輕了我的壓力,也把反對勤奮續保的路堵死了。只是我看到,三個副職一臉驚訝地看著他們的村支書,像看著外星人一般。
三
“我早說了,村里只要有一個人有低保,那這個人一定是我。有人還想取消我的低保,那是做夢,取消我低保的人還沒生呢。”去送雞蛋給勤奮,他正在和鄰居吹牛。他背向著我們,我們走近時,看見他回頭了一次,但他卻提高了嗓門,似乎是故意說給我們聽。
“段勤奮,不吹牛你嘴癢啊。”婦女主任說起來是勤奮的晚輩侄媳,不過這個女人潑辣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直呼其名勤奮也只能受著。勤奮轉身,一臉諂笑走過來。看到我手里提著的一箱雞蛋,搓了搓手說,“王干部您來就來,還帶什么慰問品啊。”
“什么慰問品,這是還給你的雞蛋,上次你送給王書記十一個雞蛋,王書記買了一百一十個還給你。王書記他這叫你敬他一寸,他還你一丈。但你也別耍小聰明,玩把戲,以后不許給王書記送東西。”我正在想怎么接勤奮的話,婦女主任搶先說了。話糙理不糙,直白,正是我想要說的意思。
“那我哪里受得起。”勤奮嘴里這么說,手卻伸出來,接過這箱雞蛋,“來,王干部進屋里坐坐。”推開門,門后有什么東西倒了,嘩啦一聲,嚇得我心里一驚。我一腳跨進大門,屋里靠右墻幾把椅子相互擁擠在一堆,布滿了灰塵和蜘蛛網,正面墻角堆放著編織袋、水桶、釣魚用具等,靠左墻邊一張折疊餐桌上,中間的碗里是吃剩下的魚頭和魚刺,另一個碗沿上粘著幾粒米飯,筷子交叉睡在碗邊,一個一次性的塑料杯倒扣在一個五斤裝散裝酒瓶口。
一股說不出的異味撲面而來,一陣反胃,我趕緊退了出來。婦女主任伸頭看了一眼屋里說,“亂得像狗窩,怎么走得進去,有吹牛的時間,把家里多收拾收拾,自己住著也舒服。”
“才收拾了。”勤奮的臉上寫著委屈,在墻根放下箱子說:“條件差了,王干部別嫌棄,比不上您城里的房子干凈。”
“今天就不在你家坐了,還有點兒事要回去處理,改天再來吧。”異味令鼻腔難受,我連著打了幾個噴嚏,招呼婦女主任離開。
“本來,他的老房子快塌了,村里用危房改造政策資金給他新建了這棟房子,剛搬進來時,沒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還能走進屋,沒隔三天,家里就亂糟糟像廢品回收站。前兩年,因為你們單位領導經常來看他,張書記每個月都會帶兩個人幫他收拾房間。他這個人命賤,亂七八糟的垃圾,給他扔了,回頭他又撿回來堆在家里。次數多了,領導知道他的德性,往后來只在禾場里站一會兒,張書記也就沒再幫他收拾屋子了。”婦女主任這么介紹,我心里坦然了。有的人從小適應某種生活環境,外界任何試圖改變他們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除非強力介入,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有不一樣的生活習慣。比如我自己,如果茶杯放在辦公桌左手邊,那么它在這個位置將伴隨我一生,家里的物件也是一樣。
收拾好居家環境,也是一種家庭傳承,一種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不是一兩代人可以改變的。從另一個角度講,只要他自己覺得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中,別人眼里的臟亂差,和他有什么關系呢!換一種說法,街頭涂污有人稱之為街頭藝術,有人卻難以容忍,這是一個道理。
回去的路上,遠遠看見一個人在蝦池里忙。“那是胡會計的蝦池。”婦女主任指了指。胡庸辭職有小一個月了,鎮紀委在縣紀委的要求下,還是給了他一個警告處分。村里的黨員在討論這個處分時,爭議還是很大的。
“他們家這陣子很忙。”我想去他家看看,婦女主任說:“等他們忙完再去吧。”
胡庸辭職后,一門心思建設他的家庭農場。他有二十畝蝦池,流轉了鄰居八十畝耕地,還有一個十來畝的葡萄采摘園,家里的小四合院改建成了農莊,正在裝修,垂釣池也正在建,一家人特別忙。
“幾年前,胡會計還是治保主任的時候,西荊河發大水,防汛缺了編織袋,胡會計騎著自家電動三輪車去鎮上買,回來路上發生車禍,胡會計膽和脾臟都切除了。那時候村里窮,只幫助貼補了一點醫藥費。禍不單行,車禍后沒半年,他兒子好端端在大學得了精神病,送回來在家養病,病情穩定的時候跟正常人沒兩樣,發起病來家里什么東西都拿出去扔。頭兩年到處看病,花了不少錢,實在沒得治才放棄,開始苦做掙錢。要說我們村,最該評上困難戶的就是胡會計家,村里欠他,他家庭遭受的磨難也多。別看他現在辦了家庭農場,人模狗樣,其實欠了一屁股債,日子過得苦,比勤奮的小日子差了不知多少倍。他這么苦做掙錢,無非是想替兒子多攢下幾個錢,等到他百年之后,兒子衣食無憂。”
聽完介紹,我大約明白了勤奮挨揍的原因,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
四
胡庸的處分決定還有溫度,勤奮居然找到我,想讓我把他弄到胡庸的家庭農場打工。“他那里都是農活,你不是說你細胳膊細腿干不動農活嗎?”
“我打聽過了,他的垂釣池缺一個管事的。我幫忙喂魚飼料,打秤、送盒飯之類的小事還是可以的。”
“你們鄉里鄉親的,你如果覺得能勝任他那里的工作,可以自己去找他啊。”我看他一臉諂笑的樣子,覺得惡心,便又補了一句,“胡會計也不是小氣的人,如果覺得你可以勝任,他絕對不會因為你告過他,害他干不了村干部而懷恨在心不請你。”
“對對,您說得對。我也不是小氣的人,我不怪他打我,所以我才來找你,讓他請我工作。”
這是什么邏輯?我一下子接不上他的話,想了又想說,“胡老板現在不是胡會計,我這個駐村干部管不到他。不過既然你找我了,抽時間我去一趟,把你的想法跟他說說,成不成,取決于胡老板。”
沒隔兩天,勤奮來找我詢問結果。看到勤奮,我才想起這個事,只好跟他說抱歉,“這兩天比較忙,還沒時間去胡老板家。”
“我就知道,您沒把我的事放在心上。”勤奮一臉堆笑,“您是大干部,日理萬機,心里放的都是大事。我看您現在不忙,能不能麻煩您幫我問問?”
本來我很想問他一句,哪里看出我不忙了,話到嘴邊,生生咽下去了,針鋒相對挑起矛盾,萬一他寫封信說我不把貧困戶的事當回事,玩忽職守,欺上瞞下,那真是黃泥巴掉進褲襠,太不劃算。
我猶豫地拿出電話,一邊撥號,一邊盤算該怎么跟胡庸說這個事。“胡會計,不,胡總,有個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稱呼我是反復斟酌了的,先稱呼胡會計,提醒他過去我們一起共事,我也算是他的領導,馬上改口稱呼胡總,是恭敬他,和我平等,商量的事,看著辦。
“我就是養條狗,還能看家護院,他能干什么?”等我把話說完,胡庸直接拒絕了,“別說我在創業,養不起懶漢,就算我有很多錢,也絕不會把錢讓他掙。”
我開著免提,胡庸的話勤奮聽得很清楚。掛了電話,我說,“勤奮,你看,這個事……”
“這個事不是這么搞的,”勤奮似乎并沒有因為胡庸的話生氣,“你這是在敷衍我,電話里哪能說得清楚,你要去他家當面做工作。做工作你們干部最在行。”
“那你別著急,等我跟張書記商量商量,再去找胡老板。”我賠上笑臉,站起身說,“你放心,你的事情我肯定放在心里,就算搞不定,那是我能力有限,你也別往心里去。”
看著勤奮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早春的夕陽里,有那么一刻,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實際上我并不知道為什么笑,有什么值得笑。張大山一聽我提起勤奮,直搖頭。引導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家庭成員就業,是我的職責之一,明知道張大山不愿聽不想管,我還是得說。等我把事情說清楚,張大山來了一句,“他?不是我瞧不起他,就他那副懶勁,誰會瞎眼睛請他!今天是個艷陽天,不要辜負了這么好的天氣。”
喝了兩口茶,又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說完,抱著茶杯走出辦公室。我知道他這是在回避,我卻不好要求他。
一把手的電話恰在這個時候打來,“聽說你現在對工作不上心,群眾有要求推三阻四?同志啊,不要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咱們老百姓,沒有誰愿意過窮日子,沒有誰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團糟。你們在下面做工作,要學會換位思考,站在群眾的角度,從深層次去發現問題,扶貧先扶志,懶惰有懶根,找出根由,對癥下藥,才能事半功倍。有些事情,不要一根筋,一棵樹上吊死,打開思路天地寬。”這是在給勤奮說話。這個勤奮,肯定給一把手打電話提要求了。
為啥只想著在胡庸的家庭農場這一條繩子上吊死?一把手的話點醒了我。聽同事說起單位門房大爺前陣子說想辭職回家帶孫子,正好讓勤奮去頂班。
但這個想法被管家領導否得一干二凈,“我那個祖宗,他來?我駐村兩三年,對他再熟悉不過。先不說門房大爺沒辭職,就算辭職沒有人,我寧可不要門房,也不能請勤奮來。這個心思你就別動了。”
“誰來說都不行,除非不讓我管這個家。”回頭他又補了一句。
工廠、企業、建筑工地,春季都在大量招人,此路不通再想他法。我打電話和勤奮商量,問他愿不愿意進廠上班。勤奮在電話那邊沉默了一小會兒說:“王干部,進廠也不是不行,但我得把丑話說在前面,我初中沒畢業,沒文化,沒技術,沒力氣,肩扛不動,手提不動,您若是能找到適合我工作的崗位,我愿意去,等領了工資掙到錢,一定好好感謝您。”
我一下子啞了語,想起電影《讓子彈飛》的一句臺詞,“躺著把錢掙了。”世上哪有這等好事。“實話跟王干部說,早些年我養過魚池,有點經驗,也喜歡,每天扛兩袋魚飼料的力氣還有。”話說到此,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五
我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去的胡庸家。倒春寒下起了連陰雨,北風也吹得緊,才收進櫥柜的羽絨服又拿出來穿上了。雨后初晴的陽光照在身上,便有些熱。
我沒有喊村干部,不想他們為難。油菜花在陽光的照射下,泛起一層金黃,整個村莊被這一層金黃籠罩。這樣的陽光,這樣的金黃,令人心情愉悅,適合談攏某些問題。路過西荊河,河邊有人在釣魚,令人羨慕。吹著溫暖的春風,曬著暖洋洋的太陽,誰不喜歡垂釣呢。
胡庸家里有客人,是農信銀行的工作人員,其中一人有過一面之緣,于是我熱情地打招呼,并介紹胡庸是我們村的能人,有頭腦,有事業心,能干事,能成事,銀行貸款給他雙受益,如果有需要,工作組愿意提供幫助,比如擔保之類。這么明顯的好意,胡庸聽后一點兒反應都沒有。等送走農信銀行的人,胡庸板著臉對我說,“王書記若是為勤奮的事情來,恕我事情多,不接待。”
“開口就把門堵死,哪有這樣的待客之道?我今天來,不完全是為了勤奮……”話還沒說完,胡庸接了一個電話,臉色驟變,撒腿就往外跑。我愣了兩秒,馬上意識到可能出什么大事了,也撒腿跟著胡庸跑出來。他朝河邊有人釣魚的地方跑去。
等我氣喘吁吁地趕到,胡庸正和一個人扭打在一起,是勤奮。兩人不能說是扭打,胡庸騎在濕漉漉的勤奮身上,揮舞著拳頭砸在勤奮頭上、身上。在他們旁邊,躺著一個清秀的少年,也是渾身濕漉漉。
我似乎明白了。我沒有理會胡庸暴揍勤奮,跪在少年身邊,探脈,按壓胸膛,掐人中,人工呼吸。少年沒有反應。
“打120沒有?”
“打了,打了。”是勤奮的聲音。
胡庸這才放開勤奮,爬過來抱住少年,如狼一般號叫起來。鼻青臉腫還淌著血的勤奮癱在旁邊,嘴里喃喃地念叨著什么。我攥緊拳頭,用力地伸出食指指點著他說,“你呀,搞什么事!”
“不是我,我是救他。”即便勤奮鼻梁骨折了,肋骨也斷了兩根,還是被派出所的警察帶走了。
打電話給胡庸的老大爺說他路過河邊的時候,看到他們兩個正在奪魚竿。雖然只是片面之詞,并且也無法證明少年落水與勤奮有關,但在當時痛失愛子的情況下,胡庸做出非理智的判斷,產生了比較嚴重的后果,情有可原,可以理解。
我這樣解釋,聽起來似乎沒什么不對,實際上我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沒有阻止胡庸毆打貧困戶勤奮。這個嚴重的問題讓我背了一個警告處分。胡庸就不用說了,派出所將他行政拘留了十天,好在執法人性化,在他處理了孩子的后事之后才執行,另外責令他支付了勤奮的治療費用,紀委還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處分。幸運的是勤奮沒有對他追訴民事賠償。
派出所通過大量的調查走訪和技術勘察,查明真相:胡庸的兒子釣魚過程中,受到狡猾的魚不上鉤的刺激,犯了病,拿著魚竿拍打河面,鬧出很大的聲響,其他釣魚人紛紛收拾釣具離開,唯有勤奮勸他回家,在勸說過程中發生了爭奪魚竿的場面。在勤奮也準備收拾釣具離開時,胡庸的兒子突然跳進河里,不會游泳的勤奮大喊救命,四周無人,只能自己跳進河里救人。好在水并不是很深,勤奮勉強施救,將胡庸的兒子拖上岸。
唯一的目擊證人是河對岸垂釣的鄰村村民,當時他正在油菜田里拉大便,透過油菜花,目睹了一切。隔著一條三十多米寬的河流,加上勤奮及時跳進河里救人,所以他沒有參與施救。他在胡庸毆打勤奮的時候報了警,之后悄悄離開,他不想惹麻煩。
六
陽光從西荊河東岸升起,照著一片青綠的村莊,充滿活力。
胡庸找我,說想請勤奮到家庭農場工作。“我冤枉他,心里不安。好幾次夢到娃兒,他濕漉漉地從河里爬起來,抱著勤奮笑。娃兒自從得了病,很少見他笑。他這么托夢給我,肯定是想讓我雇勤奮。”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理解胡庸做這樣的夢。想到張大山的話,我有些擔心,不能因為心懷歉意,雇請一個不中意的人,影響家庭農場的發展。我有些猶豫要不要提醒胡庸,胡庸卻說,“垂釣池確實需要人管理,給他機會,也給我心安。如果他實在做不了,我再辭退他。”
這么說,我只能順胡庸的意。等我上門把胡庸的意思說給勤奮,他張大嘴,一副不相信的樣子,結結巴巴地說:“我,我……”
“你這是幾個意思,敲盤子?先前不是想方設法想要去嗎,現在因為他兒子,原本你可以救活他?你心虛,怕了?”
“天地良心,我都差點淹死,嗆了好幾口水。我是怪自己本事小,沒有救活娃兒,心里不安。”
“這么說還有點兒良心。再怎么說胡庸明事理,很感激你。雇請你,也算替他娃兒報答你舍命相救之恩,你去工作不要給自己丟臉,不要辜負了娃兒。”
走出勤奮家,從西荊河東岸升起的太陽已經爬到了村莊頭頂,那些掩藏在旮旯里的陰影,此時一覽無余,整個村莊一片光鮮亮麗。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幅畫面:勤奮在垂釣池投食機旁,欣喜地看著前來搶食嬉戲的魚兒。他身上的衣服干凈工整,不再像殺豬佬的圍裙。想到這個畫面,我笑了。
日子過得飛快,青油油的秧苗已變成黃燦燦的稻子。有一天一把手突然來到村里直奔胡庸的家庭農場,采摘園、蝦池、農莊,前前后后看了個遍,最后來到垂釣池,一把手開口問,“聽說我包聯的對象勤奮在你這里工作,怎么沒見他?”
胡庸一怔,眼神有些慌,看向我。發生了意外?我心里直咯噔。“是這樣的,一星期前,他從我這里辭工了。”
“小王,你不是說他在這里干得好好的嗎?”我詫異地看向胡庸。
“本來是干得好好的,也不知他怎么想的,突然說不干了。我以為他會跟王書記說一聲,就沒有給王書記打電話。”
“小王,你的工作還有提升的空間啊!走,到勤奮家看看。”
勤奮家大門緊閉。鄰居說他到鎮上打酒割肉去了。給他打電話,他卻說到市里看兒子。
一把手看了我一眼,對鄰居說:“聽說勤奮在胡老板的垂釣池打工,怎么好好的辭了工?”
“是呀,胡老板給他開的工資不低,對他特別好,我想去,胡老板還不要呢。”
“那他為什么要辭工?”
“他跟我們說,胡老板家的生活太好了,餐餐大魚大肉,還有酒喝,他吃不來。”
“你不是說他到鎮上打酒割肉么,他吃自己的吃得來,吃胡老板的咋就吃不來?”
“這你就要問他自己了。”說完,鄰居望著張大山笑了笑。
張大山扭頭看看我,我干咳一聲,望著一臉慈祥的一把手。
“哦,有意思。”一把手臉上堆出笑容,感染了大家。于是,大家臉上也掛滿笑容,但笑容里充滿尷尬。
責任編輯/董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