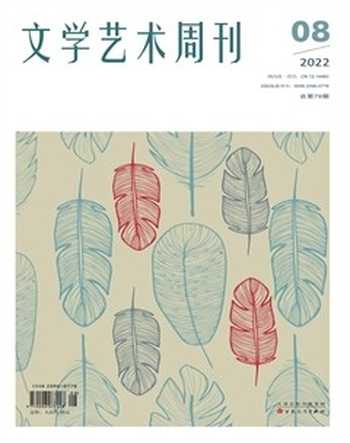《樂記?師乙篇》和《唱論》中的聲樂演唱研究
談及中國音樂理論著作中的聲樂演唱,筆者自然地想到《樂記·師乙篇》與元代燕南芝庵的著作《唱論》。這兩部著作中的理論不僅指導著中國古代聲樂演唱前輩,也對現當代歌者們的聲樂演唱及教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樂記·師乙篇》所蘊含的演唱關系
(一)歌者性格與選曲曲風的對立統一關系《樂記·師乙篇》主要論述子貢與師乙論
樂。前半部分,子貢問師乙他適合唱什么歌曲,師乙回答:“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由上述可知師乙為不同性格的歌者給出他們適合演唱的曲目,即歌者具有什么樣的品行、性格應對應選擇什么樣風格內涵的歌曲。歌者不同的性格特征、品格修養、文化水平、生活閱歷決定了他適合演唱的曲目的類別。值得注意的是﹐師乙在談論《商》和《齊》時,強調了擁有正直、柔和、慈愛性格的人適合歌唱剛強、堅毅的《商》,由柔化剛;擁有果斷堅毅性格的人適合歌唱溫和純美的《齊》,由剛化柔。看似將性格與演唱風格置于一個矛盾體之中,實則是表達了希望用音樂來改變性格、調和性格的美好愿景。我們認為這種歌唱是值得肯定的,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得到改變,歌者通過演唱旋律和歌詞,可對其性格、身心、思想進行鍛煉、內省、立德。
(二)演唱時氣息與音樂的關系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意思是歌者演唱高音的時候聲音要昂揚,要用大力氣;唱低音時聲音要沉重、響濁,不需要用太大力氣。力氣大小在歌唱中是通過氣息運動來調節的,唱高音的時候需要“上抗其喉”,氣息在橫膈膜附近的肺部底端,氣息流上升時,氣息和喉頭會產生一種抗力,喉頭則順勢向下,回應氣息的沖擊。唱低音的時候需要實現“下墜丹田”,仿佛氣息穩固地落在地面,產生支撐力,感受腸肌發力。“上抗”和“下墜”講究氣息的充盈,這樣才能擁有好的演唱效果。
“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旋律轉折時,要唱得干凈、舒展,不要拖泥帶水;微曲部分的演唱講究平穩、規矩,要唱得中規中矩方能動人心弦;樂句收尾時,要唱得圓潤,聲音要像珍珠碧玉那般完滿。“貫珠”是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即珍珠被線一顆顆貫穿起來。其中“珠”比喻唱出來的字像珍珠一樣飽滿而圓潤;“貫”則是更強調穿珍珠的線,強調連貫性。從整體來看,演唱要顆顆分明,飽滿圓潤又極具線條感。這里強調了歌曲的細節處理,想要達到“折”“止”“矩”“貫珠”的藝術效果,自然是離不開氣息的調節,控制好氣息回收的量與速度才是實現它的唯一途徑。
二、《樂記·師乙篇》演唱關系與個人的“碰撞”
筆者學習聲樂演唱六年之久,在實踐中產生了大量演唱感受,有些部分與《樂記·師乙篇》所言有些許出入,以下僅為個人感受。
《樂記·師乙篇》所言氣息應當“上如抗,下如隊(墜)”,起到較強的支撐、沖擊作用和有下墜的感受。但筆者認為不論聲樂還是器樂﹐最終的歸宿都是“自然”。所謂“自然”,就是自己的身體各個部位、器官不應受到任何不適的壓迫,不論演唱的是高音還是低音都應保持在同一個發聲位置的基礎上,氣息穩定而自然地供給,不存在力氣大小、對抗的感覺。值得關注的應該是高低音所需要的氣息量不同,若能做到如上所述,才能達到聲音音色自然、身體器官自然。如若按照“抗”“墜”之說,聲帶久而久之會產生疲憊感,嚴重的話,甚至可導致聲帶疾病。筆者認為《樂記·師乙篇》在聲樂審美方面體現出側重追求音量大小和音色的特點。音色是個人所決定不了的,過度追求只能創造出“不自然”的聲音,且損害聲帶。
筆者分析認為,此“碰撞”產生的原因有可能是《樂記》其實更強調的是音樂的教化作用,所以當描述聲樂演唱感受、方法、效果時,不免也與教化作用有所關聯。筆者認為寫作意圖和理解角度是導致《樂記·師乙篇》所描述內容與筆者個人實踐感受不同的主要原因。
三、《唱論》中所蘊含的聲樂演唱知識
筆者在研究《唱論》的過程中受到了頗多啟發,該書作者燕南芝庵僅通過一千余字,簡潔而精練地描述了宋元時期的聲樂發展概況、演唱審美以及規格標準,還總結了一些聲樂演唱時常出現的弊病,提醒演唱者們應該具體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描繪了正確的聲樂審美要求。筆者在研究《唱論》時,發現現代的聲樂審美與宋元時期的聲樂審美有共通之處,甚至發覺宋元時期的審美比現當代聲樂審美更為嚴苛,這對筆者產生了莫大的觸動。
(一)作品再次創作的“度”
著名聲樂理論著作《唱論》中,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及演唱時的“唱病”,這便是演唱者在演唱時再次創作的“度”。聲樂作品的曲牌詞牌在宋元時期要求是相當高的,但是在嚴格之中演唱者和創作者又有自由發揮的空間,所以當聽眾欣賞作品時,這個作品呈現的表演規格是否能夠做到張弛有度,主要在于演唱者的個人控制能力。《唱論》中提出:“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嗓,有堂聲,背合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拭的,失之乜斜。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搯的,失之本調。”每位歌者天生音色差別甚大,所以不同歌者對于同一首作品的演唱所呈現出的效果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有些歌者唱得過于氣勢磅礴,缺少了村落寧靜的本質;有些歌者唱得過于柔和委婉,缺少了作品暗喻的內涵;有些歌者唱得過于機巧靈動,缺少了作品散懶隨意的生活態度;有些歌者演唱得過于中規中矩,缺少了創新和新意;有些歌者唱得過于自由,忽視了作品的本來面目。所以對于演唱者而言,應當提高對作品的認知程度,把作品的風格以及作品本身的創作目的和含義都了解清楚,避免“唱病”的出現。
對演唱者來說,把作品本身的風格和內涵研習清楚,并將聲音和風格及內涵準確地結合和表達﹐同樣也是一件尤為重要的事情。每一首被世人接受和認可的作品都包含了作者成熟的創作思想和內涵。經過筆者對《唱論》的研讀,不難發現其中早已有了正確把握作品呈現的標準。第一步便是從作品本身的旋律和調性入手。早在宋元時期,先輩就已經用調性將音樂的性格內涵劃分出來。我們要想把音樂風格內涵研究得更加透徹,不僅可以通過調性,還可以更加關注音樂的旋律走向。通過對音樂旋律走向的研究,我們發現,當情緒激昂時,旋律線條多呈現上升趨勢;當情緒迷茫時,旋律線條多呈現下降趨勢。結合旋律走向與對應部分的歌詞和創作背景,我們便離準確理解作者創作的風格內涵更進一步。除此之外,演唱者在速度上、力度上、表情上的掌握也依賴于音樂術語,它可以提示歌者應該如何去演唱,幫助我們更準確地表達作品。伴奏與演唱者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歌者需要正確認識伴奏的重要性,發揮人聲與伴奏交輝呼應的作用,最大程度還原相應音樂作品蘊含的情感本質。在《唱論》中,先輩們總結演唱經歷和經驗,目的就是避免后人產生“過”與“失”的錯誤,為后人提供幫助與支持。但是落到實踐中來,演唱者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去增進、提升自己對歌曲的了解。
(二)演唱中的規范
對作品風格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想要把作品演唱好,《唱論》還要求演唱者關注一些演唱方面的問題,譬如“唱聲病”“添字節病”和“歌節病”等,這些都是為了在音準、音色及歌詞等方面對演唱者起到規范的作用。
第一點“唱聲病”,即歌者演唱時聲音的毛病。《唱論》中的描述為“散散,焦焦;干干,冽冽;啞啞,嗄嗄;尖尖,低低;雌雌,雄雄;短短,憨憨;濁濁,赸赸”。我們可以從這些疊詞中發現先輩們對于演唱的規范和審美,將“散散”“干干”與“啞啞”結合起來分析,大致說的是由于咬字不清晰、元音和輔音沒有配合好、氣息松散不集中導致的聲音虛啞。將“雄雄”“憨憨”“濁濁”與“尖尖”結合起來分析,大致說的是由于氣息沒有沉下去而是浮動在胸腔部分,導致喉頭不放松,呈現出捏著嗓子般的尖銳、嘈雜、遲鈍、不純粹、不干凈、不靈活的音色。另外,我們從《唱論》描述的“唱聲病”所呈現的聲音問題中不難了解到前人所追求的聲音是圓潤飽滿、讓聽者感到舒適的音色,是線條感明晰的天籟。在外部演唱形態上《唱論》也有要求,即演唱時應避免“格嗓”“囊鼻”“搖頭”“歪口”“合眼”“張口”“撮唇”“撇口”“昂頭”“咳嗽”,不要在演唱時增加一些多余的動作,追求儀態自然大方。
第二點“添字節病”,就是演唱者不嚴格遵循作曲家的意圖,而是根據個人的理解隨意地改變作品的面貌,使作品不能表達出其蘊含的本質和內涵。這種改變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增加后綴字符,另一種是刪減字符。我們必須要明確的一點是,演唱時不論增加還是刪減字符都是不合適的,我們對曲作者、詞作者都應該保有最起碼的尊重,演唱時要遵照作品所蘊含的一切。我們還需要思考,作品之所以能廣為流傳定是經過了時間的考驗和無數次的打磨,作品的成熟度是很高的,隨意地增加、刪減大概率會歪曲作者的創作意圖。此處之所以用“大概率”一詞,是因為如若作者本人并不是演唱者且不通曉演唱技藝,的確有可能導致韻律與歌詞并不匹配,不利于歌者演唱。所以有些作品經過演唱者對歌詞的增刪處理后,反而更加流暢和諧。此類情況較少出現,但不是完全沒有。
第三點“歌節病”,這一弊病說的是演唱者的音準問題。《唱論》中記載:“不入耳,不著人,不撒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嗓拗。劣調。落架。漏氣。”這短短的一段文字,卻提及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四不”(不入耳﹑不著人﹑不撒腔﹑不入調)即從聽者的角度出發,描述了演唱者不能給聽眾帶來愉悅的感受,音不準、調不明。“四少”? (功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即分析演唱之所以“不入調”的原因是練習、演出次數少,而聲樂是非常講究基本功的,需要日積月累地練習,最終量變產生質變,才能把聲樂作品完整地呈現出來。“嗓拗。劣調。落架。漏氣”這段文字是對前文的總結,若是不勤加練習,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宋元時期聲樂演唱有派系之分,在音色、風格上有著明顯不同,演唱者不可“混搭”,需要仔細研習自己演唱的派系特征。演唱者想要避免“歌節病”的產生,就要勤勉練習、注重實踐、增加思考,這樣才能演唱出被聽眾所欣賞的作品。
四、《唱論》蘊含的聲樂演唱知識對筆者聲樂學習的啟示
關于《唱論》中描述的作品再次創作的“度”,筆者在聲樂學習過程中得到的啟示是:謹遵作者意圖、謹慎擅自修改、忠于作品本身,應在仔細研究過作品之后,結合個人演唱技巧和理解來完成作品的“再次創作”。
《唱論》中描述的“唱聲病”“添字節病”“歌節病”這三大病癥是所有歌者都應該重視的問題。在“唱聲病”方面,除了勤奮努力以外,我們更需要結合科學的發聲方法,形成正確的聲樂理念,否則只會導致努力和收獲難以達成平衡。科學的聲樂理念是注重輔音咬字出氣,元音隨著輔音的氣流順勢發出,而不是元音與輔音前后分離,即輔音在唇齒舌阻氣的前面位置,元音在喉嚨的后面位置,前后位置不統一則會產生啞音或虛音。“添字節病”方面,應多閱讀和了解國內外作曲家和詞作家的創作背景,讓自己擁有對作品的敬畏之心。“歌節病”方面,我們要善于借助鋼琴延音踏板的功能,彈奏作品中的每一個音并哼唱,達到音準重合時,就能有效避免出現“歌節病”。
五、結合《唱論》談對《樂記·師乙篇》的理解
《唱論》通篇篇幅短小,全文不足兩千字,但是涵蓋的聲樂演唱知識卻非常細致、豐富。相比于《唱論》,《樂記·師乙篇》更突顯禮樂教化的作用,其主要觀點涉及歌曲選擇的適宜性與不可替代性、歌曲的特點與演唱的關系、聲樂演唱的技巧及特點等,提出了在選擇歌曲、理解歌曲、表演展示歌曲、音樂的作用和社會功能等方面的見解和啟示。當然在這些方面的選字用詞也與教化功能緊密相關。
《唱論》和《樂記·師乙篇》這兩部著作在我國聲樂史上地位非凡,研讀《樂記·師乙篇》和《唱論》這兩部著作中的聲樂演唱內容,對筆者和廣大歌唱者來講都是終身受益的。
[作者簡介]莊妍妍,女,漢族,廈門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舞蹈與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