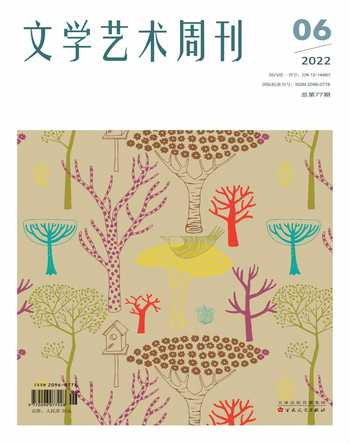淺析朱熹《詩集傳》
陳楚玥
《詩經(jīng)》在我國文學(xué)史和漢語發(fā)展史上占據(jù)至關(guān)重要的地位,讓歷代文人學(xué)者不斷對其研究注析,由此產(chǎn)生了很多《詩經(jīng)》注本和研究《詩經(jīng)》的著作。朱熹的《詩集傳》是宋學(xué)在《詩經(jīng)》方面的代表作,是繼《毛詩故訓(xùn)傳》(簡稱《毛傳》)、《〈毛詩傳〉箋》(簡稱《鄭箋》)、《毛詩正義》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詩經(jīng)》注本。本文主要闡述《詩集傳》的內(nèi)容、創(chuàng)新之處及其所存在的爭議,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輔以自己的見解。
《詩經(jīng)》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經(jīng)典之一。無論是《左傳》《論語》,還是其他的先秦古籍,都或多或少有關(guān)于《詩經(jīng)》的論述與記載。《論語》中孔子更是直接提出“不學(xué)詩,無以言”等闡述《詩經(jīng)》重要性的名言。
在孔子儒學(xué)的影響下,自漢代起,詩經(jīng)學(xué)就成了一門顯學(xué)。其中傳詩者共有四家,即齊、魯、韓、毛。古文經(jīng)學(xué)的《毛詩》一直在民間傳授,其地位不如齊、魯、韓這三家被立為學(xué)官的今文經(jīng)學(xué),但隨著東漢鄭玄為《毛詩》作箋,《毛詩》戰(zhàn)勝三家詩,成為正宗。而三家詩學(xué)也先后消失在民眾的視野里,只留下些許殘缺的片段,直到唐代孔穎達(dá)作《毛詩正義》,給《詩經(jīng)》漢學(xué)做了總結(jié)。
宋代,學(xué)風(fēng)開始轉(zhuǎn)變,出現(xiàn)了與漢學(xué)相對的宋學(xué),其主要特點(diǎn)是注重理學(xué)。而宋學(xué)在《詩經(jīng)》方面的代表作,便是朱熹的《詩集傳》。本文主要通過闡述《詩集傳》的內(nèi)容梗概,就自己能力所及談?wù)摗对娂瘋鳌匪w現(xiàn)的創(chuàng)新之處及其所存在的爭議,來對這部傳世經(jīng)典進(jìn)行品析。
一、《詩集傳》內(nèi)容梗概
(一)集“百家之言”
南宋朱熹撰《詩集傳》,簡稱《集傳》,除開篇的《詩集傳序》外,內(nèi)容共二十卷,為《詩經(jīng)》的研究著作。總體上來說,朱熹的《詩集傳》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毛詩序》的束縛,但它同時(shí)也吸收了《毛詩序》對詩義的理解。這看似矛盾的說法,其實(shí)與他的成書思想有關(guān),朱熹指出,凡是關(guān)于詩義的看法都要經(jīng)過《詩經(jīng)》原本的檢驗(yàn),不能盲從一家之說法。
《詩集傳》成書后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因它集合了前人的觀點(diǎn)看法,所以命名為“集傳”。雖然吸納了百家之言,但《詩集傳》內(nèi)容并不顯得雜亂,因?yàn)橹祆鋵η叭说淖⒔膺M(jìn)行了甄選,所以其注解簡明扼要,不顯冗雜,可謂集百家之說鍛煉而成的注解《詩經(jīng)》的經(jīng)典著作。
(二)具有理學(xué)特色
除了內(nèi)容上集百家之說,《詩集傳》作為朱熹的著作,也貫徹了其理學(xué)的精神思想。
朱熹在《詩集傳》的開篇《詩集傳序》中就明確指出,他希望學(xué)習(xí)《詩經(jīng)》的人可以通過抑揚(yáng)頓挫地誦讀,根據(jù)上下文具體語境來通曉《詩經(jīng)》的意義,即通過“熟讀諷詠、據(jù)文求義”的方法,明白《詩經(jīng)》中的美丑善惡,達(dá)到自我警醒的作用;通曉《詩經(jīng)》中存在的三綱五常的“天理”,抑制自己情勝性動的人欲。
《詩集傳》中理學(xué)精神觀念的突出表現(xiàn),就在于朱熹打破了《毛詩序》“美刺之作”的思想主張,提出了《國風(fēng)》“淫詩說”的觀點(diǎn)。他將《國風(fēng)》篇中的二十四篇?dú)w為“淫詩”,其實(shí)就是為了達(dá)到警醒世人、抑制人欲,廣泛傳播理學(xué)價(jià)值觀念的目的。但是光有反面教材還不足以達(dá)到朱熹想要的說教效果,他需要一定的正面教材來補(bǔ)充說明自己想要傳播的精神理念。因此他一方面否定《毛詩序》的部分主張,提出《國風(fēng)》中有“二十四首淫詩”的說法,另一方面又遵循《毛詩序》的說法,將《周南》與《召南》中的《關(guān)雎》《摽有梅》等情詩套上“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光圈”,不再認(rèn)其為“淫詩”。這自相矛盾的做法,其實(shí)是因?yàn)樗枰凇秶L(fēng)》中確立正面教材,利用注解來達(dá)到自己說教的目的,進(jìn)而將自己的政治、哲學(xué)思想滲入其中。故《詩集傳》又是其傳播理學(xué)觀念的教材。
總而言之,南宋朱熹的《詩集傳》是通過搜集前人的注釋,以《詩經(jīng)》原本做參考,對前人的注解進(jìn)行甄選后著成的。因其簡明扼要,相較于《毛詩正義》而言使用起來更為方便,同時(shí)對詩旨滲透了理學(xué)的思想精神,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再加上朱熹南宋大儒的身份地位,所以該書自南宋起就影響巨大,受到很多人遵奉。
二、《詩集傳》的創(chuàng)新之處
(一)突破“疏不破注”,主張“據(jù)文求義”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jìn),造極于趙宋之世”。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教育高度繁榮的時(shí)代,這個(gè)時(shí)代孕育了不少影響后世的思想家、大文豪,宋明理學(xué)即在此時(shí)誕生。宋代“重文”的風(fēng)尚,讓宋人不僅在思想上重新挖掘儒家的思想資源、闡述新的理解,更在文獻(xiàn)研究上做出了不小的貢獻(xiàn)。不少的儒家經(jīng)典都經(jīng)過了他們新的譯注,提出了新的理解方法。
就宋人注解《詩經(jīng)》而言,他們不再遵奉唐代孔穎達(dá)《毛詩正義》中提到的“疏不破注”的解詩方式,而是開辟了一條新的解詩途徑——“據(jù)文求義”。所謂“疏不破注”,通俗而言就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觀點(diǎn)是如何注解的,就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注解,其中核心標(biāo)準(zhǔn)就是《毛詩序》對詩旨的闡釋。而這里便有一個(gè)問題:《毛詩序》通常用一個(gè)具體的歷史事件去解釋《詩經(jīng)》文本,但是就讀者而言,他們是很難從《詩經(jīng)》原文本身看出詩句和《毛詩序》提出的歷史背景之間是有何關(guān)系的。所以,在這個(gè)問題的基礎(chǔ)上,宋人便提出了“據(jù)文求義”的解詩途徑,即拋開《毛詩序》舊說,直接從《詩經(jīng)》原文入手,探求其詩句的含義。
首次提出“據(jù)文求義”觀點(diǎn)的是宋代文豪歐陽修。他具有很強(qiáng)的懷疑精神,對于古說權(quán)威從不盲從是他提出這一觀點(diǎn)的內(nèi)在原因。最能體現(xiàn)“據(jù)文求義”思想的,便是他的《詩本義》。這部書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其目的就是探討《詩經(jīng)》的本來意義。這其實(sh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yàn)閺摹对娊?jīng)》注解的來源來看,無論是《毛詩》還是齊魯韓三家詩說,都是一家之言,即便《毛詩》相傳傳自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是師徒相傳難免有一定的偏差,所以理解《詩經(jīng)》的最好方法便是“據(jù)文求義”,以《詩經(jīng)》原文作為理解詩義的基礎(chǔ)。因此宋人在《詩本義》的影響下,逐漸拋棄古人舊說,突破了《毛詩序》的束縛,從《詩經(jīng)》原本人手理解詩義。
朱熹便在此基礎(chǔ)上,繼承了歐陽修“據(jù)文求義”的觀點(diǎn),將其作為自己《詩集傳》的闡釋方式,同時(shí)也延續(xù)了歐陽修的懷疑精神,大膽質(zhì)疑《毛詩序》的舊說。比如《召南·江有汜》一首,《毛詩序》中言,“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其中“嫡”與“媵”是指女子在出嫁時(shí),娘家往往會為其準(zhǔn)備隨從侍女,一起嫁人夫家。朱熹通過分析原文的言辭,指出并沒有體會到勤勞無怨的意思。除了大膽質(zhì)疑舊說,對于從文本無法推知詩歌背景的作品,他主張保持“闕疑”的精神,要實(shí)事求是,不得妄下斷言。如在對《秦風(fēng)·車鄰》進(jìn)行評價(jià)時(shí),朱熹指出,這不見得就一定是秦仲之詩,除了《秦風(fēng)》篇里的《黃鳥》《渭陽》有一定依據(jù),其他的詩篇都沒有依據(jù)可以證明它們一定是秦仲之詩,對于不確定的事情不可妄下斷言。
(二)注《詩經(jīng)》體例的改革
1.廢除《詩序》
作為先秦時(shí)期的經(jīng)典,《詩經(jīng)》一直受到歷朝歷代的廣泛關(guān)注。在漢朝,注解《詩經(jīng)》成了一股潮流,出現(xiàn)了齊、魯、韓、毛四家并存的局面。其中齊、魯、韓被立為學(xué)官,而《毛詩》則在民間傳頌。然而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相較于被立為學(xué)官的齊、魯、韓三家,在民間傳頌的《毛詩》則成了后世爭相研究的對象。之后的鄭玄《〈毛詩傳〉箋》、孔穎達(dá)《毛詩正義》都是在《毛詩序》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新的闡釋。直到北宋時(shí)期,歐陽修《詩本義》對《毛詩序》提出質(zhì)疑,這種疑序、反序思潮才開始慢慢深人發(fā)展。
在宋代疑序、反序的思潮下,朱熹對于《詩序》的態(tài)度也受到影響,有一個(gè)從認(rèn)為其合理到認(rèn)為其應(yīng)該被廢止的過程。關(guān)于朱熹《詩集傳》為何廢除《詩序》,應(yīng)該有兩點(diǎn)原因:一方面,朱熹認(rèn)為《詩序》的存在會對《詩經(jīng)》文本的解讀產(chǎn)生誤導(dǎo),在讀《詩經(jīng)》原文之前先讀了《詩序》,會使讀者因?yàn)椤对娦颉返慕榻B而將《詩序》的旨意融入于《詩經(jīng)》文本之中。這種先入為主的思想,會使得《詩經(jīng)》原文面目全非,不利于對其原意的正確理解。另一方面,他認(rèn)為《詩序》把《詩經(jīng)》的每一篇都用來陳古諷今,這曲解了《詩經(jīng)》作者的原意情感,更有害于溫柔敦厚的詩教。
在廢除《詩序》之后,為了更好地解讀《詩經(jīng)》,朱熹直接提出了另一種解讀《詩經(jīng)》的方式,即上文提出的“據(jù)文求義”,通過原文理解其本義。
2.葉韻說
朱熹受到了吳械葉韻說的影響,即通過把一個(gè)字臨時(shí)改變注音的方式,達(dá)到臨時(shí)的押韻。比如《衛(wèi)風(fēng)·氓》中,為了與“朝”“暴”押韻,朱熹將“笑”葉音為“燥”;《衛(wèi)風(fēng)·碩人》中,為了與“敖”押韻,朱熹將“郊”與“驕”都葉音為“高”,“鑲”葉音為“褒”。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葉韻說”在如今看來是不太科學(xué)的。高本漢在其《詩經(jīng)注釋》的前言中寫道,朱熹用葉韻說的方法為《詩經(jīng)》注音,把一個(gè)字臨時(shí)改變讀音,以求押韻,這種做法是不夠科學(xué)的。他沒有遵循上古音韻學(xué)的規(guī)律與特點(diǎn),只從葉韻說出發(fā),會使人們產(chǎn)生不必要的誤解。
3.對《詩經(jīng)》“六義”的重新闡釋
朱熹對詩經(jīng)的風(fēng)、雅、頌、賦、比、興六義做了新的解釋。他主張從音樂和創(chuàng)作群體方面來劃分“風(fēng)”“雅”“頌”。對于“賦”“比”“興”,他歸納為“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因此,他在每首詩、每一章下,都增標(biāo)賦、比、興。比如《邶風(fēng)·靜女》,朱熹認(rèn)為該篇第一句話采用了“賦”的寫作方式,直言陳述男子等待心愛姑娘出現(xiàn),卻遲遲不見她的焦急之情;而對于《鄘風(fēng)·柏舟》,朱熹認(rèn)為該篇第一句話采用了“興”的寫作方式,以“柏舟”起興,表達(dá)女子對男子的思慕之情。
與《毛傳》的單標(biāo)興體和只標(biāo)首章的做法相比,這樣的做法更好地揭示了《詩經(jīng)》藝術(shù)手法中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是《詩經(jīng)》注疏史上的創(chuàng)新。
三、關(guān)于《詩集傳》的爭議
朱熹《詩集傳》成書后,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也收到了或褒或貶的評價(jià)。其中,書中關(guān)于《詩序》之辯和《國風(fēng)》“淫詩論”的主張更是引起了后人的極大爭議。筆者在這里主要以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為參考,對《詩集傳》的這兩個(gè)主要問題進(jìn)行論述。
(一)對其廢除《詩序》的指責(zé)
朱熹廢除《詩序》,主張以“據(jù)文求義”的方式,通過原文理解《詩經(jīng)》本義。這種新的解讀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fù)了《詩經(jīng)》的原貌,如《國風(fēng)》中許多詩篇從前人所說的“美刺之詩”變成了純粹的“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民歌,但是在馬端臨看來,這種“廢《序》言《詩》”的解詩角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馬端臨認(rèn)為,《國風(fēng)》作為一種文體,其中許多詩篇都運(yùn)用了“比”“興”的手法來進(jìn)行諷刺,導(dǎo)致其本質(zhì)意蘊(yùn)很難把握,所以《詩序》會在詩作之首就道明作詩之人的意圖與旨意。而朱熹廢《詩序》,主張“據(jù)文求義”的做法,其實(shí)是增加了讀者閱讀《詩經(jīng)》原文的難度,使得詩義更不好理解。
(二)對《國風(fēng)》“淫詩論”的批判
在朱熹“廢《序》言《詩》”的思想指導(dǎo)下,《詩集傳》把《詩經(jīng)》中《國風(fēng)》篇的許多詩作都從前人所言的“美刺之作”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但是作為南宋時(shí)期著名的理學(xué)家,朱熹一方面還原《詩經(jīng)》中《國風(fēng)》篇男女之間戀愛的曖昧情愫,一方面又從理學(xué)思想觀念出發(fā),維護(hù)封建倫理道德,將它們歸為“淫詩”一類,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后人對《詩集傳》的批判。
對此,馬端臨指出,朱熹之所以劃分出了二十四首“淫詩”,是受其理學(xué)思想的影響。孔子講解《詩經(jīng)》是從美刺的角度出發(fā),本著《國風(fēng)》的主旨應(yīng)是反映勞動人民真實(shí)生活,表達(dá)勞苦人民在剝削與壓迫下不平的心境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在一些太過曖昧的言辭上,孔子也是本著“思無邪”的態(tài)度看待;而朱熹從理學(xué)思想的角度出發(fā),因?yàn)閷δ信異矍椤惱淼赖碌倪^分看重,即使是再純正的詩詞,也會被當(dāng)作“淫邪”之作看待,這才導(dǎo)致了所謂二十四首“淫詩”的出現(xiàn)。
之后,馬端臨先生更是從孔子刪《詩》的旨意出發(fā),對朱熹的“淫詩說”進(jìn)行批判。他指出,孔子刪《詩》并沒有刪除被朱熹認(rèn)為是“淫詩”的《詩序》,所以其“淫詩說”是不符合孔子的旨意的。總而言之,對于朱熹的《國風(fēng)》“淫詩論”,馬端臨指出“所謂的‘淫詩實(shí)則是變風(fēng)、變雅的刺上之作,并且《鄭》《衛(wèi)》之詩能用于宗廟祭祀和朝廷宴饗,而非‘淫聲”。
四、結(jié)語
朱熹的《詩集傳》雖然在“廢《序》言《詩》”及《國風(fēng)》“淫詩論”上遭受爭議,但是它也有獨(dú)到之處。它不僅吸納了百家之言,通過對前人注解的甄選,達(dá)到注解內(nèi)容簡明扼要、不顯冗雜的目的,更闡述了“據(jù)文求義”的解詩途徑,對詩經(jīng)“六義”——風(fēng)雅頌、賦比興提出了新的闡釋,對《詩經(jīng)》學(xué)的研究發(fā)展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宋學(xué)的代表作,也是我們學(xué)習(xí)《詩經(jīng)》的重要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