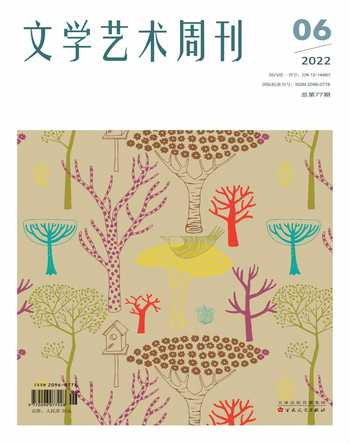“勇”視閾下中日文學作品對子路形象的重塑
董瑜靖
孔子是萬世師表、天縱之圣。儒家學說依靠各位孔門弟子進行傳播,孔門弟子三千,其成就表現在孔門四科及代表弟子,以德行聞名的弟子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方面突出的有幸予、子貢;以政事為人所知的有冉有、子路;擅長文學的有子游、子夏等。而在《論語》一書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子路,根據楊伯峻《論語譯注》統計,子路(包括季路、由等別稱)共出現82次,遠遠多于其他弟子出現的次數。子路是獨具特色的孔門弟子之一,其思想言行并未完全限制在孔門四科之內,在解讀孔子其他思想內涵方面呈現出獨特價值,突出表現為“勇”的特質。本文將從“勇”的視角,尋找《論語》中的子路之勇。同時,在此基礎上,聯系先秦時期相關典籍與近現代日本文學作品,探究子路形象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別作品中的演變,對子路之勇進行更深層次的分析。
一、《論語》中的子路形象
《論語》記錄了孔子與諸孔門弟子之間的對話,是子路形象來源最為直接的材料。《論語》對子路形象的塑造主要體現在言語、行為及思想這幾個方面。
(一)言勇——快言敢答
子路“言勇”的特點在《論語》中主要表現在與孔子的對話之中。對孔子的言行或是所提出的問題,子路總是第一個反應,總是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即使對方是老師也無所忌憚,以言之迅速與直白表現出他“勇”的一面。子路表達感情直接,為人處事有自己鮮明的態度。因孔子見了有失道德的衛靈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悅,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直至孔子誓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除此之外,子路提出和回答問題不假思索也足以見其“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坐孔子,回答問題的順序與態度不同,從而襯托出子路的直率,子路是“率爾對曰”,急匆匆第一個回答,而曾皙是“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孔子問問題時曾皙正在彈琴,孔子問:“點,爾何如?”他才慢慢將琴聲稀落而盡,放下琴來回答問題。一急一緩塑造了孔門弟子極為不同的兩種個性,反襯出了子路說話無所顧忌,追求先人一步之“勇”,更直指子路提出問題也有過于直率輕浮的特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路不滿孔子“必也正名乎”的回答,認為孔子迂腐,直接訴諸言語,對孔子說:“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的話惹怒了孔子,孔子批評道:“野哉,由也!”從孔子的態度及子路的表現可以看出,子路言語率真,即“言勇”。
(二)行勇——重情重義
言語與行動是不可分離的,“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正是行動證明了子路的忠勇。子路在言語上體現出的直率付諸行動便是大義凜然的君子豪情,他是儒家義利觀與生死觀的堅定守衛者和踐行者。雖也有莽撞如孔子所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顏淵》),但更有一片赤膽忠心。“子疾病,子路請禱。”(《論語·述而》)“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論語·子罕》)孔子生病時,子路是孔子最忠實的守護者,并為他祈禱。從孔子評價子路“衣敝缊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論語·子罕》)也可見其對待朋友、身邊人的重情重義,不為外界因素所左右,也正是他身上俠義之氣的體現。
(三)心勇——喜言政事
“心勇”是思想之勇,子路在思維方式上很直接,通常在談論政事時表現出來。比如齊桓公殺管仲之主公子糾,管仲非但沒有自殺反而為齊桓公服務,就此,子路問孔子管仲是否“仁”。子路認為管仲非仁,這是以臣子是否為君主犧牲為“仁”的評價標準,而孔子思維則體現出較為靈活的一面,考慮的是管仲為桓公相之后所產生的積極效應,這樣的效應帶來了普惠的“仁”。子路的回答并未經過精細縝密的思考,更多是依照自己的價值標準,直截了當地闡發自己心中所想。
也正因為孔子了解子路的心理特點,對待軍事之事缺少考量,于是針對他的心性,孔子步步引導子路從單純的“勇”向“謀”的方向發展。在談論軍事時,孔子也會特意指出軍事思維中“思”的重要性,較無畏的“勇”,小心與謹慎更能帶來軍事上的成功。因此,當子路問孔子,如果能統帥三軍會選擇與誰共事時,孔子回答:“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空手打虎,徒步過河,雖喪命而不后悔的人,正是指像子路這類想法較為簡單,崇尚以勇力治軍的人,因此孔子給出了在軍事方面應善于謀劃的建議。
喜言政事在某種程度上,是子路內心強大、思維闊大、抱負不凡的體現。子路在軍事與政治方面渴望有所作為的雄心壯志正是君子之勇強有力的例證。子路快言敢答、重情重義、尚武好勇、喜言政事,這充分說明了他性格當中“勇”而“野”的那一部分特質。這種性格特點賦予了孔子主“禮”偏靜的儒家思想以粗獷的生命活力,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形成了良性互補,為后人提供了進一步研究闡釋儒家學說的空間。
二、先秦及漢代典籍中對子路形象的補充
以《論語》中塑造的子路形象為基礎,子路形象在先秦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挖掘與闡釋,先秦兩漢典籍《說苑》《左傳》《史記》《孟子》等都有子路事跡的記載,具體而言,先秦時期的子路形象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子路“勇”中有原始之“野”,勇莽沖動,需稍加點化。先秦典籍中交代了子路的出生地及入學前的背景環境,如《韓詩外傳》曰:“子路,卞之野人。”這句話交代了子路的出生地。卞之野人,是相對于王畿地區而言的鄉下,地處偏遠之地,身份又非貴族,少禮教,自然缺少等級禮制的教化,呈現出一種原始的“野”。另外《史記》謂:“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這段描寫突出了子路生性粗鄙,崇尚力氣,志氣高,不聽人言,甚至對人不尊重。頭頂公雞,扛著小豬,這樣的力氣加上不羈的性格,較《論語》中不斷發問的子路形象更多了一絲生活氣息。這種不受約束的“勇”是子路純樸生命力的體現,也是人物生命力與故事新鮮感的主要來源。同時也交代了子路需要孔子的點撥,這成為子路入學的契機。
以上兩則材料交代了子路的身世背景,交代了子路是“野人”。出身背景造成了子路少禮教、好勇的性格,解釋了子路“勇”中帶有“野”的原因。從《論語》中也能感受到子路身上因從小不受禮教約束而產生的質樸之氣,他言語行動上不拘禮節,甚至連孔子也嘆道:“野哉,由也!”這與先秦時期典籍中塑造的子路形象相符。
第二,為政方面,子路“勇”中有稚氣,輕浮固執。《論語》中子路問政,子路與孔子之間的政治理念探討在其他先秦典籍中變為了實錄,也記載了子路在實際治理中魯莽和倔強的地方。《說苑·臣術》中記載,子路當上了蒲令,要安排百姓預備對付水災。他春天和百姓一起修溝,因見百姓困苦,于是發給每個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憤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雖是出于“仁”的愛人之心而無所畏懼,但子路卻忽視了用私糧來救濟百姓帶來的后果。不僅如此,子路面對質疑時仍態度堅決,語氣強烈,并沒有進一步思考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因此這種沖動便帶有了“稚氣”。子路解決問題時眼界不夠開闊,思維并不成熟,往往僅就問題本身出發,在小范圍內尋找解決問題的最快途徑,卻忽視了最佳途徑。帶有“稚氣”的處事風格是對子路在《論語》中“心勇”的補充。
“勇”中亦有“思”,知錯能改。子路之勇不是孤勇,而是善于聽取別人意見認真思考的智慧之勇。《孟子·公孫丑上》記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路遇到別人指出他的過錯就大喜。對待別人的建議加以思考,不會因為是指出其缺點而抵觸、拒絕聽從。這種從容大度是一名勇武之人難有的優秀品質。更有《說苑·臣術》載“子路心服而退”,對待孔子的訓誡,子路由堅決的“不受”到“心服”,只需孔子兩三言便可。子路只需稍加點撥,便能體會老師的用意。這不僅需要有接受意見教導的意愿,還需要有勤于思考、善于領悟的能力。這種能力便是子路平日里善思鍛煉積累形成的。
若要看清一個人是否真能聽取意見,可以觀察他在極端情緒下是受理性還是感性支配。追殺的士兵圍困子路與孔子,極度危險之中,出于本能,子路變得慍怒。而孔子在旁提醒著“仁”的內涵,邀子路一同歌唱。在孔子的勸說下,子路順利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最終只殺了三人。
這樣的重塑使得原本簡單的子路形象變得多面。在缺少史料依據的條件下,《說苑》作為小說雜史,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子路的生動描述。記言體《論語》從對話入手,記事體《說苑》則從多方面塑造子路形象,用完整連貫的情節敘述子路的事跡,大大豐富了子路的形象。
子路之死素來有爭議,《春秋經》與《史記》所持意見不同。《春秋經傳集解》中,子路與子羔相遇,子路孤行入內營救孔悝,認為吃了孔悝的俸祿就不應該躲避禍難,最終由于太子派人圍攻,子路沒能安全離開。《史記·衛康叔世家第七》記載,孔悝叛亂立了新主,子路死于城中。
兩者對子路死法的描述是一致的,那就是都維護了其作為君子最后的尊嚴——“結纓而死”,但在死因上出現了分歧。按照《左傳》的描述,子路救孔悝正是體現了子路重義氣的特點,而《史記》中蒯聵、孔悝都是以下犯上的逆臣,子路單槍匹馬赴死是出于對政權的維護,更有忠君的思想在其中,以此角度看待子路之死更有一種崇高的悲劇美學意味。有學者對《左傳》和《史記》中子路之死呈現出差異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司馬遷對子路勇猛無畏的性格欣賞有加,于是改動了其中的情節,提高了子路之死的價值,更符合儒家的價值觀。除此之外,司馬遷修改子路之死更多是基于本人更傾向于《公羊傳》的主張而非孔子的主張,這是歷史觀上的差異所致。
子路形象在先秦時期的補充與重塑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子路形象演變歷經了長久的過程,從先秦時期開始,文獻中有大量關于重塑子路形象的例證,大大豐富了子路形象中“勇”的一面,同時也從多方面揭示了子路“勇”之外的多個側面的特征。深入探究可以更加真實地還原子路這一人物形象,解讀孔子與弟子們的價值觀,豐富儒家思想的內涵。
三、近現代日本作家對子路形象的塑造
近現代,日本諸多漢學家也開始了對孔子及孔門弟子的研究,他們依托先秦史料文獻與《論語》加以理解,詮釋出基于儒家思想,同時符合日本審美特征與評價標準的孔門師徒形象。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中島敦的《弟子》、井上靖的《孔子》,它們以各自不同的視角竭力還原《論語》對話之外的故事。中島敦的《弟子》聚焦孔門弟子日常故事,而井上靖的《孔子》則將《論語》對話連接成孔子完整的一生。他們對子路形象也進行了各自理解。
《弟子》由十六章、三十個情節構成,除了三處情節是中島敦完全自創的外,剩余二十七處都是基于典籍素材做了創造性地增寫或改寫。
中島敦對子路形象的還原是史實與自我想象的疊加。如《史記》中的“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獺豚,陵暴孔子”,在中島敦筆下則為“(他)左手提著公雞,右手拎著母豬,氣勢洶洶地朝著孔丘的家門而去。他一路搖著雞晃著豬,企圖借用動物嘴里發出的嗷嗷叫聲,來擾亂儒家弦歌誦讀的聲音”。
中島敦的描寫中既有基于《史記》的場景還原,也有自我創造,加入了生動的動作描寫及對子路當時心境的揣測,以突出子路頑劣無畏的性格。除此之外,中島敦的《弟子》中,子路由最開始的不敬重父母到以孝聞名,在先秦典籍中并沒有相關記載,只有“為親負米百里之外”的相近敘述。中島敦書中加入了子路最初沖動易怒,對父母少尊重的情節,增加了子路性格的轉變,既突出了子路善于明理的聰慧,也彰顯了孔子教導有方,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可讀性。
中島敦的《弟子》對子路形象的重塑也體現在更為冷靜地展現了《論語》中缺少的情節。《史記》《說苑》中涉及子路的描寫同《論語》中的描寫相結合進行全面地敘述,將子路“有勇”的另一面“有思”也凸顯了出來,其中有子路對“天”的思考,以第一人稱心理描寫展現他對孔子觀點的疑惑,甚至懷疑,“雖然在老師面前的時候好像感覺能夠接受這種觀點了,但是等到回來之后一個人再試著想一想,還是會覺得有些地方怎么都無法釋然”。子路的形象不再是簡單接受知識、踐行所學的單方面接受者,更是一個有自我獨立思考能力、判斷能力的個體。中島敦筆下的子路,帶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美感,多種描寫手法與故事的編織使得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中島敦的《弟子》的語言風格為通俗易懂的口語,減少了文言文晦澀的成分,填補了細節的缺失,更加貼合子路直率、不拘小節的個性特征。
井上靖的《孔子》又對子路形象進行了另一個視角的理解與補充,首先體現在對子路之死的描寫上。子路之死在《孔子》中有詳細的描寫,井上靖采用了《左傳》的說法,即子路為救孔悝而犧牲,也重在突出孔子預言的真實,“鄙人覺得夫子預言相當可怕。唯有深知子路其人者始能如此出言。今日講起來,鄙人仍能感受到夫子做此預言時內心的哀傷”。作者帶入弟子身份,選取《左傳》作為史料依據,回避了司馬遷出于敬佩而作的結局,尊重了客觀史實,以突出文中描述的嚴謹細致與真實客觀。對夫子情感的揣測帶有主觀色彩,卻使子路在孔子心目中的價值得到了凸顯,讓子路之死更添一重悲劇感。
其次,井上靖在《孔子》中增加了抒情性描寫,進一步完善了子路的形象。由于《孔子》的整體語言風格偏向冷靜客觀,子路形象在文中便不似《弟子》中那般粗獷豪放,更有一種冷靜與內斂。“夫子如此知我、惜我,不枉我終生侍奉師尊——子路想必滿懷感念,心滿意足地閉上雙眼。”井上靖讓子路對孔子多了一種感恩之情,像是彌補了子路再無法開口的缺憾。這種感激之情正與慷慨決然赴死之“勇”構成了互補——子路雖處事粗魯直率但情感卻真摯細膩。
除此之外,子路對知識的渴望與對孔子的體貼在文中得到了細致地勾勒。相比于《論語》,《孔子》使情節更加合理化,人物形象也因此顯得更加自然。《孔子》中,改子路生氣地問孔子“君子也有窮困的時候嗎”為“陡然沖著夫子擲出這么一句,好似有怨,或許是真的生氣了”,同時增加了子路重復問了兩遍問題的情節,使子路少了一些粗魯的怒氣而多了一些刨根問底的倔強,也顯示出子路為人心地善良、單純。在這個情節中,井上靖也一改孔子形象,在回答子路問題時對聲音的描寫加上了“強有力”“使眾人一震”這樣的修飾語,一來現場的氣氛達到了最高點,人人情緒高昂,打破孔子原本沉靜的形象;二來在與子路的對話中將子路的激憤與孔子的沉著的關系從對比變為了襯托,子路的兩遍疑問點燃了孔子內心的慷慨大義,將情緒推到了頂峰。子路從原來那個沖撞魯莽的形象搖身變成能夠引出孔子內心所思的忠實陪伴者。接下來作者以第三人口吻揣測子路:“此時,子路可是在哭泣?‘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想到從師尊口中討得這句嘉言,饑餓算什么,餓死算什么!子路必是欣喜——毋寧說感動得禁不住手舞足蹈。”
這段描寫添加了子路受到教誨后的欣喜,多了一種樂于學習、勤于受教的謙虛及對知識的尊重景仰,相比于簡單地提出問題更能凸顯其性格的多面性。
最后,作品采用的視角對理解子路有別樣的作用。《孔子》與《弟子》不同,《弟子》屬于直接由作者觀察,聚焦門人弟子;而在《孔子》中,作者將自己化身為孔門中最不起眼的一名弟子,目光始終追隨孔子,以一種局內人的局外眼光完整翔實展現孔子及其門人弟子的生活言行。這樣的視角一可身臨其境,增加真實感,二可突破時間局限,不止敘述《論語》中的言語與其他史實,還可以用超遠的目光講述孔子死后所發生的事,以旁觀者的身份冷靜回溯與反思,筆尖文字中帶有沉重的回憶性質。子路在與他一般的同學眼中,展現出的是真性情而不帶偏見的樣貌,作者不再如記錄史實一般帶入記錄者的價值觀與評價標準,塑造形象時不再偏激,而變得更加柔和與生活化。
上述兩部還原孔子及其門人弟子的日本文學著作,對子路的人物形象都有各自的構建。中島敦創作《弟子》的背景是特殊的,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政治壓迫下,許多有氣節的日本作家拒絕與軍國主義合作,選擇以自由身份投入自己的文學天地,彰顯自己的自由意志,《弟子》正是那一時期的產物。其對子路形象的塑造沒有完全依照《論語》而是進行了再提煉,以詼諧幽默的筆觸展示自己超然的態度,對子路的贊賞也是對“勇”的價值的認同與偏愛。中島敦自幼體弱多病,與父母關系也并不融洽,不善于融入集體,自身帶有一種孤敏的個性氣質。中島敦筆下,子路的健勇、直率正是中島敦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對子路的“勇”并不帶有任何批評色彩,更多是一種欣賞。也正是中島敦身體的缺陷與敏感善思的特質,使子路增添了思索者這一身份。中島敦將自己對人生與世界的思考投射到子路身上,除“勇”的性格之外還為子路增添了一絲理想化色彩。
井上靖曾任中日文化交流協會常任顧問,對中國傳統文化及思想有著深厚的感情與獨到的理解。《孔子》是井上靖的絕筆之作,寫書初衷是愿以漢學文化闡明一種豁達的生死觀、勇于與“天命”斗爭的人生觀。子路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待夫子教授事理時的尊重,無不展現著如子路一般的井上靖對孔子的欽佩之情以及對中華文化、儒家思想的敬重。另一方面,子路死后不久孔子去世,文中透露出濃重的感傷色彩,對“死”這個命題的探討持續深入,不論是子路之死還是其他弟子的死,對生者來說都是寂寞的。子路的“勇”背后透露出對孔子恩重如山的感激,可以說是對生的一種追念。井上靖筆下,子路的死對雙方來說都是不舍的,讀者通過這部作品更能理解身患癌癥的井上靖對生死的體悟。
四、結語
《論語》中的子路形象具有獨特的人格魅力,后代文人在特定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作用下,不斷對子路形象進行加工,傳至海外仍具有影響力。后世文獻中,子路形象的塑造方式非常多樣化,人物形象更加鮮明飽滿,雖然是對子路形象的接受與重塑,但實際上反映的是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對子路形象的探討對深入研究孔子與孔門弟子具有重要意義,單方面從孔子角度解讀儒家思想文化可能具有研究視角上的局限性,不同于傳統,通過還原子路形象回溯孔子與弟子們的交往場景、交往方式,把握孔門弟子各自的性格特征,是對先秦孔門弟子日常生活與思想活動的再挖掘,為重新深人解讀孔子儒家思想,傳承弘揚孔門學風、儒家經義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