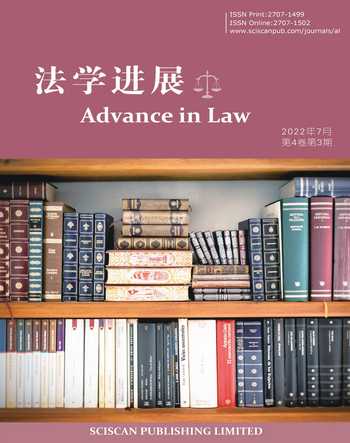襲警罪的規范分析與司法適用
孫承程 苑嘉輝
摘 要|襲警罪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設罪名,為了確保該新設罪名得以正確適用,本文將從規范層面和司法適用的角度予以分析:第一,該新設罪名保護的
法益為警察的執法權和人身健康權,并且該雙重法益中還存在主次區分;第二, 對本罪的犯罪對象的范圍應當進行“先實質后形式”的審查,從而將輔警納入 此罪的保護范圍之內;第三,本罪的暴力行為的作用對象應當包含人員和警用 物品;第四,本文將從教義學角度對本罪的相關概念如“暴力行為”“正在”“依法執行職務”“嚴重危害人身安全”等進行解析,并且和妨害公務罪進行區別, 以便更為精確合理地適用本罪名;第五,對于該罪的司法適用的展望,筆者認為, 只有嚴格遵守審慎入罪、寬容出罪的態度,才能符合刑法謙抑性的要求,真正 彰顯司法的權威與公正。
關鍵詞|襲警罪;妨害公務罪;刑法謙抑性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明確襲警罪的規范和具體適用具有必要性
對于襲警罪的設立而言,必須肯定的是,由于警察職務的特殊性,會比其他職業面臨更多的風險,因此襲警罪這個新設罪名的設立符合了警務工作的現
作者簡介:孫承程(1998-),女,浙江杭州人,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學; 苑嘉輝(1996-),男,河南周口人,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學。
文章引用:孫承程,苑嘉輝.襲警罪的規范分析與司法適用[J].法學進展,2022,4(3):111-123. https://doi.org/10.35534/al.0403011
實需求,通過加大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的處罰力度,有力地保障了警察的執法權的正常行使,保護了警察在履職過程中的人身健康權。但是,執法者在享受該新設罪名帶來的法益保護便利的同時,也應當清晰地認識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公安機關的執法環境也日益復雜,因此,在處理一般的違法行為和沖突事件時,應當嚴格遵守本罪的構成要件,以審慎入罪、寬容出罪的態度處理警民關系,不宜輕易地動用刑法規制警民沖突,防止公權力的濫用損害司法的權威和公正。
二、明確襲警罪保護的法益內容
法益指的是某種特定罪名所要保護的刑法上的利益,確定新設的罪名所要 保護的利益的范圍及適用的界限,有利于明晰嚴格的入罪門檻和合理的出罪標 準、此罪與彼罪的科學劃分,通過精準的定罪量刑更好地規制實施了相關行為 的行為人,同時彰顯刑法的權威性與公信力。襲警罪的“罪刑價目表”較為嚴厲, 因此,明確其保護的法益有利于約束公權力,防止司法權無謂地擴張導致濫用, 從而真正體現司法的公正。對于襲警罪冀圖保護的法益內容,目前學界主流的 觀點為該罪名的設立是為了保護警察的執法權,防止執法相對人以暴力的方式 干擾警察執法、擾亂社會秩序,另一部分學者認為該罪名保護的法益是警察的 生命健康權。筆者認為,該罪保護的法益應當為警察的執法權和警察的人身健 康權的結合,并且主要側重于前者,理由如下。
第一,從刑法分則的不同章節的特定保護法益來看,立法者設置襲警罪, 并且將其置于刑法第六章的“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章節之中,該章節中的罪名共同規制的行為均為破壞社會秩序穩定的行為,因此,襲警罪作為妨害公務罪的第五款內容,其主要規制的行為也就不言自明,也應當是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而非以暴力的手段和方式侵害警察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為a。更進一步而言,如果認為該法條描述的行為中包含了對于危害警察人身安全的行為的規制,那也應當是由于該種暴力襲擊的行為在擾亂社會秩序的同時還危害了警察的人身安全,因此才能納入該新設罪名的保護范圍之中。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警察的本質僅是一個職業,其人身安全和其他公民的人身安全應當受到同等待遇的保護,如果警察在執行公務時,執法相對人以暴力行為進行襲擊導致侵害了警察的人身健康,完全可以以刑法第四章的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進行規制,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傷害的目的,則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論處,如果行為人主觀帶有殺害的目的,則也可以通過故意殺人罪論處,并不需要刑法第六章單獨規定一個新罪名對警察這一特殊群體的人身權利進行重復強調,這樣會導致立法資源的浪費。
第二,從防止對某一人群過度保護的角度來看,一方面,設立襲警罪已經使得警察這個群體的人身健康受到了優于其他國家公職人員法律層面的保護, 雖然承認警察相較于其他國家公職人員,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確實會承擔更多的危害人身安全的風險,但是在實踐中,其他國家公職人員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多種多樣的危險,例如,法官也有可能因為負責宣判某一社會影響力較大的案件而被當事人記恨,稅務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有可能遭遇頑固抗稅者的攻擊。由此可見,如果認為刑法有必要對所有的國家公職人員的人身安全進行分類保護,那么就會導致出現襲擊法官罪、襲擊稅收人員罪等大批龐雜的、荒謬的罪名出現,這種過度保護勢必會造成刑法分則罪名泛濫;另一方面,如果刑法僅以新設罪名保護警察的人身安全而不保護其他國家公職人員的人身安全,那么就會由于過高地夸大了警察的法律地位而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更進一步而言,在警察內部也有不同的分工,不同警種面臨的風險也各不相同,例如,對于刑警而言,其職責就是與各種違法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因此需要刑法傾斜性保護其人身安全,對于網絡警察而言,其日常的任務就是坐在辦公室里操縱著計算機穿梭于虛擬空間之中,因此面臨因為職務行為導致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可能性較低,由此可見,刑法單獨為所有的警察設置罪名保護人身安全并無必要。
第三,從襲警罪本身的構成要件來看,該罪為抽象危險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暴力襲擊正在執法的警察的行為即可入罪,在法條的后半部分將嚴重危害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具體危險規定為該罪的加重情節,由此可見,要構成該罪,造成被害警察的人身健康損害并不是必備的犯罪結果的構成要件,這就可以順勢推導出該新罪名的保護法益的內容也不應當僅僅局限為警察的人身健康法益 ?。
第四,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在普遍設立了襲警罪的英美法系中,襲警罪 保護的法益僅為警察的執法權,這是因為該罪的法定刑設置較輕,因此不能包 含對于生命健康的法益保護,如果執法相對人以暴力的方式襲擊警察導致損害 警察的生命健康,則通過其他的重罪進行規制,如一級謀殺罪、二級謀殺罪等。但是對于我國的襲警罪而言,其量刑幅度最低三年、最高七年,故意傷害罪致 人重傷的量刑幅度最低三年、最高十年(排除手段特別殘忍的情形),由此可見, 我國的襲警罪可以包含重傷以下的損害結果,因此本罪除了維護社會秩序之外, 其保護的法益中還應當包括一定的人身權利。
第五,結合立法目的與立法精神,也應當認為襲警罪保護的法益之間具有明顯的主次之分,必須予以肯定的是,設立該罪的目的是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但是行為人實施的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是通過侵害警察的人身安全得以實現的,一言以蔽之,兩個不同位階的法益之間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b,即保護警察的人身安全的法益僅是手段,保護社會秩序穩定的法益才是立法者最終想要達成的目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襲警罪保護的法益內容應當是社會秩序法益與人身權利法益二者兼而有之,并且,較為重要的是保護警察這個群體承擔的維護社會機能的運轉秩序的職責之上。
三、明確襲警罪的犯罪對象
襲警罪的客觀行為構成要件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履職的警察,對于在本罪保護的犯罪對象中,除了具有編制的正式警察之外,是否還應當包含輔警,學界對此眾說紛紜。
認為該罪的保護對象不應當包含輔警的學者主要給出了如下兩方面的理由:其一,從刑法的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輔助即協助、幫助的意思,輔警并沒有警察的法定身份,因此缺乏相應的職務范圍內的權限和責任 ?,根據權責一致的原則,具有正式編制的警察因其法定職責而較容易招致潛在的危險,因此需要專門立法加以保護,輔警由于不具有法定職責,因此不具有專門立法加以保護的權利;其二,從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法目的來看,在 2000 年,最高檢發布的《關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為玩忽職守罪主體問題的批復》指出,合同制民警在執行公務期間,具有代表國家強制力的權力外觀,因此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相應規范予以規制,但是輔警只能由具有政治編制的警察帶領履行職責,其并沒有單獨執行公務的權限,因此不能代表國家公權力的權威與尊嚴,由此可見,將輔警認定為襲警罪保護的對象屬于類推解釋 b,導致對于該罪名的犯罪對象的設置明顯超出了立法目的的射程含義之外,違反了刑法解釋的基本原則。
認為該罪的保護對象應當包括輔警的學者也主要給出了如下兩方面的理由:其一,正如刑法認定身份犯時應當以實質職務為核心,對于具有特殊身份的犯罪對象的認定也應當淡化外在的身份,才能更好地實現立法者保障特定職務正常履行的初衷。在 2016 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規范公安機關警務輔助人員管理工作的意見》中,規定了雖然輔警的履職行為必須依附于具有正式編制的警察的帶領,但是只要其在法定職權范圍內依法履行職責,那么其執法行為就應當視為具有正式編制的警察的履職行為的延伸,由此可見,二者的執法行為具有一體性和完整性 c。另外,正如前文所闡述的保護法益的角度而言, 新設的襲警罪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保護警察執法權的正常行使,那么一切擾亂該執法權的行為都應當屬于該罪名規制的范圍之內,即擾亂輔警的執法行為的暴力襲擊,也應當以襲警罪定罪量刑,這并未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而是對于法條規定的犯罪對象先進行形式判斷、后進行實質判斷,根據邏輯推理所得出的理所應當的結論;其二,對于大部分普通公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能分清輔警和具有正式編制的警察的在實際執法的過程中的外在形象的區別 ?,由此可見,輔警在執法活動中就是象征著國家公權力的權威,代表著公安機關執法者的嚴肅形象,將輔警納入本罪的保護對象之中,符合一般公眾的認識需求。
綜上所述,筆者較為贊同后者的觀點,即將輔警納入本罪的保護對象之中。因為在民事關系中較為注重外在形式的區分,如無權代理行為在被代理人承認之前效力待定,但是刑法是保障法,在其他部門法無力調整某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之時,通過規制該種行為來保障其他部門法能夠正確實施,由此可見,刑法在明確其規制對象之時更應當注重實質而非外在形式。既然襲警罪的設立目的是維護警察執法權的正常履行,那么刑法就應當對于輔警在職權范圍內輔助行使的執法權予以同等保護,是否具有正式編制導致行為效力的不同應當屬于行政法或民法所調整的范疇。
四、明確襲警罪的暴力行為的作用對象
在眾多對于該新設罪名的研究中,對于該罪名所規制的暴力行為是否應當包括對物的暴力還是僅僅局限于對人的暴力的問題,一直是眾多學者探討的熱點。筆者認為,本罪的暴力行為的作用對象不應當僅限于對人的暴力,還應當包括對物的暴力,理由如下。
第一,襲警罪和妨害公務罪的行為對象應當保持一致。襲警罪和妨害公務罪屬于法條競合的關系,在公安部和最高法、最高檢聯合印發的《關以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中指出,毀壞警用車輛和警用設備,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的,以妨害公務罪進行處罰,由此可見,在妨害公務罪中擾亂執法秩序的行為的作用對象包括警察和警用物品,那么襲警罪中規制的暴力行為的作用對象也不應當僅限于人員。
第二,警用物品是警察的外在象征,并且和警員自身安全息息相關。無可否認的是,警用物品通常印有警徽,因此可以看作公安機關權威的具現化象征 ?。并且,襲警罪中的“物”應當進行狹義解釋,僅限于警員履行職務所必要的和警員人身安全密切相關的物品,因為該種物品是警察行使執法權用以保護自身安全的保障設備,如果侵害該種物品,則會間接阻礙執法活動順利進行、危害警察的人身安全,即行為人攻擊警員本身和攻擊警用物品所造成的危害具有等價性,因此將該種物品納入此罪名規制的范圍內符合該罪保護法益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襲警罪是抽象危險犯, 構成其入罪門檻的暴力行為的危害程度小于妨害公務罪,因此,如果暴力襲擊警用設備但是并未危害警察的人身健康,那么應當以妨害公務罪或者故意毀壞財物罪論處。
第三,從比較法的角度而言,日本的刑法學者同樣認同將針對警用物品的暴力襲擊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之內,他們對于襲擊警察的暴力行為的作用對象一般適用擴大解釋,認為暴力行為并不需要直接對警察的身體施加不法的有形力,也可以施加于處在該警察的指揮下輔助履行執法權的輔助人員,或者施加于象征該警察的“手足”、成為其正常履行職務所必要的輔助器具之上,從而在物理載體上實質性地影響該警察的身體健康和工作能力。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于刑法規制對象的解釋應當根據立法目的和實踐經驗進行靈活變通,既然襲警罪保護的法益內容是警察的執法權,那么只要是能夠阻礙執法權行駛、危害警察人身安全的行為都應當納入該新罪名規制的范圍之內,不應當死板地對人的暴力和對物的暴力進行區別。
五、對襲警罪的相關概念的教義學分析
第一,對于“暴力襲擊”的分類和特征而言:(1)“暴力行為”應當僅指有形力,排除無形力。襲警罪規制的暴力行為應當僅指撕咬、抱摔、毆打等能夠給警察造成實際肉體損害及肉體損害風險的有形力,由于該罪保護的法益是警察的執法權和警察的人身健康權,因此只有物理意義上的阻礙行為才有顯示擾亂執法行為和損害人身安全的可能性,以電磁力為代表的無形力并不能產生相近的現實危險;(2)“暴力行為”應當僅指硬暴力,排除軟暴力。硬暴力 和有形力的概念類似,均指物理上的強制力,軟暴力指通過尋釁滋事、聚眾造勢的方式,使得被害人產生心理上的恐慌的心理強制手段,從刑法的體系解釋來看,如搶劫罪、強奸罪等其他將以暴力侵害人身安全作為客觀要件的犯罪都明確要求能夠實際壓制被害人反抗的物理性暴力,因此,為了保證刑法的內在統一性,應當將襲警罪中的暴力也解釋為物理上的暴力而非心理上的強制;
(3)“暴力行為”應當具有出其不意、防不勝防的效果。從一方面而言,以 社會上一般人的標準來看,該種暴力行為應當表現為突然爆發的猛烈行為,正因為被害人難以料到、缺乏預防,因此才有實際造成損害或產生較大威脅的可能性;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執法的警察屬于熟悉對抗訓練和犯罪心理學的專業人士,因此,對于執法相對人的行為的突然性,還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情形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如果依據警方的豐富經驗判斷執法相對人本身就具有較大的暴力傾向,那么在執法活動的過程中,行為人由于情緒不穩定,因此突然實施攻擊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升高,那么其確實對警察實施了諸如毆打、抱摔之類的暴力行為,就不能視為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從而盡可能減小行為人入罪的可能性;(4)“暴力行為”應當具有瞬時性 ?。瞬時性意味著行為人的暴力行為并非持續的、恒定的狀態,而是打破雙方對峙的平衡暴起發難,可以是從無到有的情形,例如,執法相對人在警察實施執法行為的一開始就掏出防狼噴霧對著警察的面部噴灑,也可以表現為行為升級的情形,例如,行為人先進行撒潑打滾、辱罵推搡的行為,然后突然掏出防狼噴霧進行更進一步地干擾執法的行為;(5)“暴力行為”應當具有不可預見性。警察在進行某些執法 活動之時,對于執法相對人暴起發難的可能性是有所預料的,例如,醉酒者、慣犯等群體,前者由于思緒混亂因此難以控制自身行為,后者由于懼怕重罰而具有強烈的脫逃動機。但是,如果警察面對一個初犯的柔弱婦女或孱弱老者, 實現預料對方暴起發難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小,因此該種不可預見的暴力襲擊行為的危害性就更大;(6)值得注意的是,從懲罰犯罪的角度而言,由于該罪 是抽象危險犯,因此行為人實施的暴力壓制并不要求完全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能力,即使尚未完全剝奪被害人的反擊能力,也不影響對于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認定;從保護人權的角度而言,在司法實踐中,執法相對人往往會出現情緒激動、態度惡劣的情形,采取推搡、拉扯警察的行為阻礙執法行動的開展,司法人員應當從刑法的謙抑性出發,明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對于其中人身危險性不大的,不應當以犯罪論處,通過行政罰款等手段就可以達到懲罰的目的。
第二,對于“正在”的時間范圍而言:(1)對于執法工作的事前準備工作和事后收尾工作應當視為執法活動的時間范圍之內,例如,開車前往執法目標所在的場所的行為,正如刑法規定犯罪預備之所以要受到處罰是因為該種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行為是實際著手實施犯罪所必不可少的前置條件,對于法益具有現實的危害性,因此,執法活動的事前準備和事后收尾也應當和實際執法的活動視為一個整體,是完成執法任務所必不可少的環節;(2)警察在非工作時間實施的履職行為應當視為在執法活動的時間范圍之內。結合該罪保護的法益來看,正如前文所言,應當突出實質上的職務履行,淡化形式上的身份和時間條件,從而體現對于警察履職維護社會秩序的積極的立法鼓勵。
第三,對于“依法執行職務”的合法性認定而言:(1)在行政法中,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性判斷的五要素為主體違法、事實依據違法、法律依據違法、程序違法、明顯不合理,一個執法行為只要違反上述五要素其一,就會導致損害執法相對人的合法權利進而應當判定為違法行為,因此,如果執法相對人對于此類違法行為進行反擊,應當視為捍衛自身權益的合法行為,如果對于執法人造成損害結果遠遠超過防衛的必要性和相當性,可以以故意傷害罪等罪名進行規制;(2)在行政法中,瑕疵執法行為指并未符合上述五要素,僅是在程序或處理方式上具有少許缺陷的行為,與違法行為的區別在于并未實質性損害執法相對人的合法權利,例如,交警在開具罰單時應當先敬禮,如果其遺漏敬禮的步驟,雖然不符合執法的流程,但是并不影響其后續開具罰單行為的合法性。筆者認為,執法相對人對于瑕疵執法行為的襲擊,如果符合襲警罪的構成要件, 則應當以該罪名進行論處,理由有三:其一,在司法實踐中,考慮到現實執法環境的復雜多變,并且執法者并非機器人,面對某些情況難免會出現態度上的生硬和言語間的沖突,但是由于該種疏忽和缺乏禮貌的危害性不大,因此可以視為情有可原的缺陷;其二,正如有學者所言“法律在決定某種行為是否應當受到制裁之時,司法者的目光應當始終在行為和規范之間來回流轉,不應當考慮其余與此無關的因素”?,由此可見,執法者的執法行為存在的瑕疵應當以相關的行政法規予以規制,執法相對人對執法者實施的暴力襲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應當以刑法進行規制,即不同部門法掌控的領域不同,二者應當平行處理、區別對待;其三,從損害程度的相當性的角度而言,在襲警罪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中,警察即便實施瑕疵執法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執法相對人的合法權利,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瑕疵執法行為仍然處于合法執法的范圍之內,因此警察作為襲警罪的保護對象,其受保護的程度仍舊大于執法相對人作為瑕疵執法行為的權利受損方的保護的程度。
第四,對于“嚴重危害人身安全”的主客觀的標準而言:(1)從主觀要
件而言:其一,該罪的犯罪對象是警察,因此要求行為人對于執法對象主觀上明知或者應當知道,如果行為人并不知道并且以社會一般人的標準進行衡量, 行為人也不可能認識到對方是警察,則不符合夠成本罪的主觀要件;其二,行為人主觀上對于襲擊警察的態度存由積極追求危害結果發生的直接故意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如果行為人對于損害警察的人身健康和擾亂社會秩序抱有過失的主觀態度,則也不構成本罪,由于本罪的法益內容為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警察的人身安全,因此,更進一步而言,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僅存有損害警察的人身安全的目的而無阻礙執法權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目的,則應當將其暴力襲擊警察的行為認定為發泄情緒或者惡意報復的行為,如果造成了刑法規定的輕傷及以上的損害結果,則應當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進行規制;
(2)從客觀法定刑升格的要件而言:襲警罪的法條規定中,加重情節表述為“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造成具有人身危害性的危險 狀態,對于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達到“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的標準, 目前主要有兩種如下學說:其一為“強調說”,支持該種學說的學者堅持該法 條前后情形并非一個完整的整體,即前半段的使用槍支、管制刀具及機動車的 行為與后半段出現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險并非必須同時具備才能加重處罰, 一言以蔽之,法條前半段對于行為的列舉僅是一種強調的敘述方式,行為人只 要具備了前三種行為,就可以直接升格其法定刑,并不需要切實出現實際的危險。在刑法分則中,采取類似的描述手法并不鮮見,例如,在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 安全罪中,立法者列舉了放火、決水等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手段明確了該罪 規制的犯罪方式的相同屬性,并且以抽象概括的方式規定了行為人的危害行為 只有達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才會以該罪進行處罰,由此可見,要構 成本罪,必須達到危害行為和危險結果二者的相互結合,缺一不可。這種規定 的目的是對允許該罪規制的行為進行限縮,從而達到減少入罪的刑法謙抑性的 目的。筆者認為,該種學說值得更進一步商榷,根據刑法的體系解釋的邏輯來看, 襲警罪的法條描述方式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類似,那么二者的構成要 件也應當類似,要構成前罪,也只有在行為人的行為和造成的結果都符合法條 前后文的程度限制后,方才可以入罪;其二為“遞進說”,堅持該種觀點的學 者認為必須結合現實的案例,通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來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 否達到需要加重處罰的程度。筆者較為贊成“遞進說”,因為在司法實踐和一 般人的認知中,行為人手持槍支給警察帶來的危險一定大于手持管制刀具給警 察帶來的危險,因此在具體的案例中,對于如何判斷是否已經達到“嚴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判斷標準也應當是不同的,這樣才能保證個案正義。
六、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的競合和區分
第一,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存在法條競合的關系。正如前文所言,襲警罪是特殊的妨害公務罪,其在妨害公務罪對于社會秩序法益的保護的基礎上增加對于警察這個特殊群體的執法權和人身健康的法益的保護。由此可見,一個行為如果構成襲警罪,則一定同時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襲警罪和妨害公務罪存在差異。有如下不同之處:(1)前者的法條描述的行為是“暴力襲擊”,后者的法條描述的行為是“暴力威脅”,通過語 義可見,構成前罪要求的行為的暴力程度應當大于后者;(2)前者是抽象危險犯,只要實施符合刑法構成要件的危害行為即構成本罪,而后者必須達到擾亂特定 主體履行職責的危害后果方可構罪;(3)前者可以包含的危害結果的嚴重程度高于后者,正如前文所言,襲警罪的量刑幅度和故意傷害罪的量刑幅度具有重疊, 因此其能夠包含一部分致人重傷的嚴重后果,但是不能包括死亡的結果,而在 后罪中,刑法明確規定其只能包含輕傷的結果,如果造成重傷、死亡的結果的, 應當和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相競合擇一重罪論處。由此可見,構成襲警罪 的行為不一定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
七、對于襲警罪等新罪名的司法適用的展望—— 審慎入罪,寬容出罪
從襲警罪的設立可以看出目前我國的刑事立法犯罪化的趨勢,眾所周知, 襲警案件是作為近幾年社會的熱點問題得到了刑事立法者以設立新罪名的方式 予以回應,除此之外,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還有負有照護職責人員 性侵罪、高空拋物罪、非法催收債務罪等一系列積極回應社會熱點的新罪名一一出現,這不僅是積極預防性刑法觀逐漸成為刑法界主流思潮的具象化,也 是通過擴張刑法的處罰范圍達到對于集體法益的保護的刑法價值觀的逐漸轉變。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通過擴大處罰范圍有利于更好地規范公民行為、調整社會 秩序;從消極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立法領域還是司法領域,過度地犯罪化無疑 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導致刑法公信力降低,更容易激化原有的社會矛盾。因此,必須通過明確罪與非罪的界限、嚴守刑法適用邊界的方式防止不當擴大 刑事處罰的范圍,即通過審慎入罪、寬容出罪的方式,來平衡刑法懲罰犯罪、 保護人權的本質內涵和應有功能。
Normative Analysis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Sun Chengcheng Yuan Jiahui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crime of attacking the police is a new crime i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rim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level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first,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new crime are the polices law enforcement power and personal health right, and there is a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tinction in the dual legal interests; Second, the scope of the criminal object of this crime should be examined “substance before form”, so as to bring the auxiliary police into the protection scope of this crime; Third, the target of violence in this crime should include personnel and police goods; Fou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gma,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is crime, such as “violence”, “being”, “performing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seriously endangering personal safety”, and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public affairs, so as to apply this crime more accurately and reasonably; Finally, for the prospect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by strictly abiding by the attitude of prudent conviction and tolerance, can w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and truly demonstrate the authority and justice of justice.
Key words: Assault on police; Crime of obstructing public servic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