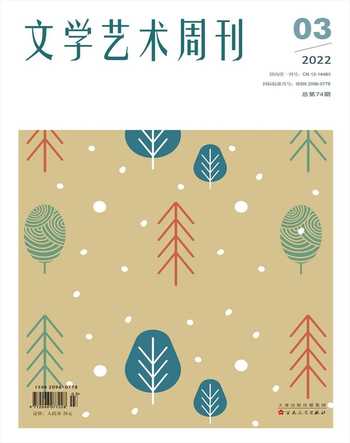繪畫的完成與未完成
王麗云 崔悅洋
有關藝術的完成與未完成的討論,早在古羅馬就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當筆者翻閱眾多文獻,發現相關話題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對藝術作品(即創作成果)的討論。而創作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卻難以引起人們的關注。繪畫藝術從刻劃在巖石表面的線條,到與巫術—宗教—哲學有關的再現真實,再到如今,繪畫逐漸失去了它的神秘和崇高,成為一種體現藝術家精神活動和表達的語言媒介。在西方古典藝術時期,繪畫大多作為商品而存在,一幅肖像訂件顯然有著明確的繪畫目的——即在二維的畫布中再現三維人物的光影和造型。因此人們很容易分辨什么程度的描繪能使畫面逼真,什么樣的繪畫可以算是完成,創作者也對什么樣的成果足以交付訂件有著較為清晰的把握。隨著時間的推移,古典繪畫再現真實的完成度標準早已成為過去,那么在當下,當我們再次討論繪畫完成與未完成的話題時,我們究竟談論的是什么?
如果說一件作品的創作過程是從無到有,那么可以將其比喻成一條射線,在這條可以無限發展的線中,作者必將面臨一個問題:該在什么時候停止創作?
一、繪畫怎樣才算完成
觀看一件繪畫作品時,很容易察覺到,有的作品帶有明顯的留白或殘缺,卻不影響理解;而又有很多作品看似豐富,卻不明所以。通常情況下,觀看者在自己都難以意識到的情況下,抱持著某種固有的標準來評價繪畫,在這些固有的標準中,完整、不完整,完成、未完成,這樣的概念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的審美判斷。對于觀看者而言,能否從繪畫作品中閱讀出內涵,畫布表面是否被顏料填滿,又或是繪畫是否符合藝術家以往作品的一貫風格等,都是觀看者評價繪畫作品是否完成的潛在標準。
對于藝術家來說,選擇在創作的某個階段停止工作,是因為這時的作品達到了創作者的預期。但現實情況是,就連創作者本人也很難說明自己對創作的預期究竟是什么,或者說,創作者的預期往往隨著創作的推進而有所改變。無論在什么階段停止,作品也只能是無限地接近藝術家的理想,卻難以真正地達到。
在更復雜的語境中,觀看者還將對繪畫作品進行再創作,而藝術家在創作中也反反復復地經歷著觀看—創作—觀看的過程,但無論情況如何,我們都能夠大概明白,評價任何繪畫作品完成的硬性標準實際并不存在,即完成的標準對于繪畫作品來說沒有普遍性可言。
既然如此,難道作品的完成度問題是不可談的嗎?若是這樣,那是不是等于說,我們可以就此隨心所欲地在創作的某個階段停止,并聲稱完成了作品呢?是不是任何就作品完成度問題發表的見解,實際上都沒什么意義呢?
在筆者看來,盡管當我們談及作品的完成度而被問及“完成的標準是什么”時,我們沒法舉出一條完善的定義,但并不是說我們無法談論一幅畫作的完成度,即談論作品畫面是否成立、表達是否充分,亦或是創作結束得是否草率。就創作者自己來說,我們從不需要去定義完成,就已經在創作中對怎樣才算完成有所要求。我們通常不會在意一件作品是否完成了,而令我們在意的往往是一件作品的未完成,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完成是什么沒有概念,相反,這恰恰說明我們對完成的意義很熟悉,以至于完成這件事才不那么引人注意,我們不能用“完成的標準并不存在”來消解掉自己對于完成的領會。
我們在看作品時,不會去判斷一個作品是否完成了,相比較來看,未完成才更接近于一種判斷。我們會花一點工夫去思考這件作品怎么沒完成,但“認定一件作品是完成的”這件事卻輕而易舉。應該說完成是種多么理所應當的感覺,以至于它根本不在我們對畫面的觀看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觀看也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那么可否這樣想,完成或未完成也是觀看者的創造力發揮之后的一個結果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倘若從這個層面去認識繪畫的完成與未完成,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沒有一件作品算得上真正地完成。完成與未完成這樣一對具有互文性的概念,就如同好與壞、愛與恨等許多我們難以說清道明,卻又有所把握的概念一樣,被我們以某種方式領悟著,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個略微有些模糊的范圍中去談論它。
二、“未完成”話題的由來
我們這里所說的未完成是擴展到一切關于藝術創作的未完成態的思考,最早有文獻可考的關于未完成概念的討論可能出現在古羅馬時期普林尼的《自然史》一書中,這本書用專門的篇幅記載了一系列藝術家未完成的作品。普林尼將未完成的作品與完成的作品進行比較,認為未完成的作品別具魅力,因為未完成的作品提供了對藝術家創作方法和過程的窺探。
不同于古羅馬時期關于未完成的片面記載,更使筆者感興趣的是來自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未完成概念。在文藝復興時期,未完成概念對應的意大利語為“non-finito”,最早作為一種雕塑技法被多納泰羅發明,指藝術家只粗略地雕刻了一部分形象。大量的文獻研究匯集在雕塑巨匠米開朗基羅的許多未完成的作品上,眾多證據將結論指向這位天才藝術家有意地保留了作品的未完成狀態。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有些藝術家會在作品上使用動詞形式簽署名字,表示作品是未完成的。
為了理解“non-finito”的具體含義,我們不得不結合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做進一步的闡述。柏拉圖的理型論將宇宙分為理型世界和感官世界,他認為塵世之物都是理型世界中永恒概念的影子,因此以再現事物為目的的藝術創作只能算是在模仿永恒概念的影子。新柏拉圖學派的普羅汀(Plotinos,205—270)則認為,世界說的從來都是一個世界而不是(理型/感官)兩個世界,這一個世界只是橫跨了兩極。一端是他稱之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則是完全的黑暗。這樣的世界概念與我們如今的世界概念有所不同,它更接近于一種“秩序”的意思。世間萬物都按照秩序井井有條地排列在這兩極之間。
原本在柏拉圖那里,永恒的靈魂最終歸屬于理型世界,物質歸屬于感官世界。但在普羅汀這里,靈魂來自于神圣之光的照耀,在這兩極之間,人是最接近于神圣之光的,其次是鳥獸蟲魚,再其次是草木花朵,最遙遠的則是泥土、水與石頭這類冷冰冰的物質。在這樣的層級中,距離上帝之光越是遙遠的事物受到上帝之光的照耀就越少,直至最遙遠處,也就最接近于世界黑暗無光的另一極。然而普羅汀認為,不存在一丁點光亮都接收不到的絕對黑暗之處,就像繁星穿越整個宇宙,仍向我們分享微弱的星光一樣,世間萬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帝之光的照耀,即便在一塊石頭之中也能窺見微弱的上帝之光。
與柏拉圖的理型觀念不同的是,普羅汀認為世界之外并不另外存在一個永恒世界,永恒之光或者說“上帝”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我們從任何事物上都能尋找到永恒性的顯現。
因此以再現為目的的藝術創作在這樣的觀點中不再是創造影子的影子,而更像是一種“尋找”。雕塑家在無序的、冷冰冰的石塊中看到了某種東西,并循著這樣的感覺將那樣東西從石塊中“尋找”出來。藝術家看到的那樣東西是什么呢?尋找工作憑借的是一個怎樣的藍本呢?究竟尋找到什么地步藝術家才會停下來呢?停下來是否意味著已經找到呢?
有理由相信,如果那時的藝術家受到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那么他們一定認為他們透過無序的事物表面所發現的那個東西,或者說他們之所以能發現那個東西的原因,與神圣的光照有直接的聯系。要么,藝術家發現自己或許在距離上帝之光最遙遠的事物中,直接看到了事物所受微弱之光的閃爍,于是尋找那道光芒,就是要讓一塊石頭是其所是地顯現;要么,藝術家意識到石頭中閃爍的那個東西之所以如此耀眼,并不是因為石頭本身而是藝術家自己,他也就認為自己具有將無序之物賦予秩序的能力。這種能力得益于照耀,得益于自身是最接近那道光的,他也于是意識到那道光只能通過該能力才能顯現,因此他得通過不斷地將作品完善得更加極致來開展“尋找”工作。
然而事實上,藝術家的觀念并不是單純地處于這兩類之一,而是二者兼顧,他既看到了事物本身所閃耀的的那部分,也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在事物上反射那部分。他無法徹底確定他的工作究竟是要將一塊距離上帝之光最遙遠的石頭拋向那道光,還是通過這些工作尋找那道永恒之光本身。因此在藝術家意識到這些之后,藝術創作究竟為了什么,不但沒有清晰起來,反倒變得更加諱莫如深了。因此,有別于因客觀因素造成的創作終止,“non-finito”顯然承載了藝術家對創作的思考與表態。
到了近代,隨著學科的發展,許多關于未完成的美感、不完整結構的意義的相關理論不斷被提出,如接受美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研究接受美學的學者提出,沒有被讀者觀看和解讀的作品都是未完成的,其中著名的論調有伊瑟爾在《文本的召喚結構》一文里提出的“召喚結構”,以及堯斯提出的“期待視野”理論。接受美學將作品離開作者的“死”,引向讀者再創作的“生”,并試圖將藝術創作的重心移向作品產生的現實意義之上。而二十世紀出現的格式塔心理學則從心理學研究出發,證實了人類審美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完形”現象,即人在審美活動中積極調動感知覺的參與,將作品獨立的、外在的、個別的局部在自身的內部心理活動中進行審美補全,進而呈現為一個完整的藝術品。在格式塔理論下,不完整的作品能在每個讀者那里引出一個完美的想象,因而未完成的作品可能為讀者提供更高的審美趣味。
三、繪畫中“未完成”的表現
在筆者看來,在使用符號進行敘事,繪畫作為行為來留下精神表達痕跡的現代繪畫中,在一個鼓勵多元,放棄統一標準,甚至毫無標準的當下,作為繪畫創作實踐者,如今我面臨的最大困擾,便是難以完成繪畫的敘事與表達。
當然,即便我們知道,任何一名藝術家都處于與筆者相同的境遇,都將在藝術創作中與問題迎面相遇,但相同的問題顯然會被一部分藝術家忽視,而對另一部分藝術家產生更大的影響。這些藝術家在創作中,通過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揭露這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或是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困惑。這其中就有我們耳熟能詳的提香、莫奈,在生命的尾端,這些藝術巨匠的創作不再考慮市場,而更多地關注自身,一改往常潦草和凌亂的筆觸似乎只為了留下一些反叛的痕跡,像是一種不顧一切的激進改革。
而在現代繪畫中,我們處處可見充滿“問題”的作品:有些作品過于潦草,有些作品經歷了過度的覆蓋,有些則是在放棄或保留符號的細枝末節上躊躇不前。如今,我們越來越難以從藝術家的單幅作品中獲取足夠于理解的信息,換言之,現代繪畫似乎正在變得不知所云,這與當下信息碎片化、圖像泛濫的時代環境不無關系。現代藝術家們越來越偏向散文式的表達,創作的不可完成性也越來越突出地顯現出來,因此,現代繪畫除了提供直接的視覺感受和情感把握之外,越來越要求讀者保持耐心,從單個作品中發現藝術家的線索,從系列作品中閱讀藝術家的表述。
四、“未完成”:繪畫在路上
制作一把椅子怎樣才算完成,椅子的存在僅僅是為了提供人休息的功能,但對任何一個有理想的設計師來說,一把好椅子絕不只是達到應有的功能。從最初的手工藝人到如今的家具設計師,人們不停地設想著世界上最美觀和舒適的椅子,并至今仍在朝著各自的方向努力。盡管如此,我們可能還是沒能讓理想的椅子的形象清晰一點兒,因為理想似乎也在無限地發展下去,但每一把椅子的誕生,都是一次嘗試。也許我們此刻坐著的也正是一把“未完成”的椅子。
本文自始至終關注的,并不是繪畫作品中由于不完整的造型和創作者有意或無意的留白、空白等造成的作品似乎未完成的表象。而是針對創作者面臨的表達困境和創作心理的一次漫談,通過揭示這樣的問題而為讀者欣賞繪畫作品提供一種更有張力的角度,這也是筆者身為藝術創作實踐者對自身面臨的實際問題的一次梳理,更是一次發問。
站在一名繪畫藝術實踐者的角度來談,理想的情況是,一幅畫可以不停地精進和修正,無限地畫下去,無限地接近于理想。但更真實的情況是,藝術家根本無法真正地完成一幅畫作,那些畫面看似完整的畫作并不意味著創作者完成了他的表達,這些充滿了意味的繪畫痕跡,是在向著一個模糊的發展道路上驟然截止,在創作者的諸多困惑和遺憾中草草結束……
[作者簡介]王麗云,女,漢族,福建人,天津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表現性油畫。崔悅洋,男,漢族,天津人,中央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實驗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