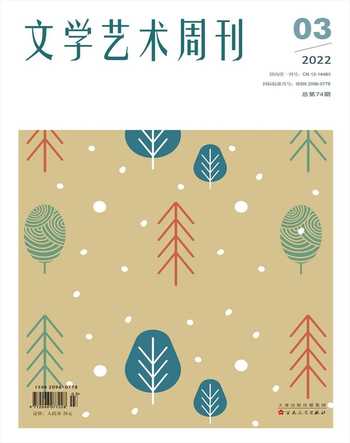一種女性主義敘述學的視角
在英國女權運動第一次浪潮的后期,當時新聞界十分流行的一家民間報紙《每日見聞報》開辟了女性與家庭類的專題。《每日見聞報》同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民眾了解戰況的重要渠道,它涵蓋的范圍極廣,從政治軍事到美妝潮流無所不包,故我們得以從這些古舊的紙張之中看見一個多彩的社會。而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上的新興思潮本就是涵蓋社會生活諸多方面的。目前保存下來的原始報刊一共有358份,但迄今為止國內外均不見通過這些資料探討這一時期英國婦女社會地位的文章。過去學界普遍認為,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男性勞動力短缺,許多女性獲得了工作機會和投票權,因此這一時期女性社會地位大幅提升。然而,當今女性主義思想家在審視以往無論是歷史的、哲學的還是文學的文本時,越來越注意到一個問題,即我們在傳統意義上看作是“客觀公正”的描述方式是否具有性別偏見?“用數字說話”“秉筆直書”這些“標準”真的是完全合理的嗎?女性主義哲學家沃莉(Worley)曾經指出,男性相較于女性而言缺乏融入(merging)世界和他人的能力,所以在男性的思維模式中,主體和世界是“格格不入”(strong boundaries between self and other)的關系,這就導致在男性的話語模式中特別強調“物我平等”的描述方式。 如果把這種描述事物的方式看作是唯一正確的方式,那么我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性別偏見的立場。基于這樣的立場,女性主義哲學家詹姆斯·蘇珊提出了“保護傘”理論:“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婦女與男子相比更易受到壓迫或處于不利地位,而且她們受到的壓迫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然而,在男性中心的話語描述方式的保護傘(umbrella)下,學術界產生了許多對女權主義運動和女權主義者的不合理闡釋,因此,將女權主義視為一種單一的學說,或認為女權主義者暗示一種可以商定的政治方案(agreed political program)是完全錯誤的。”本文通過1915年至1916年英國《每日見聞報》中有關女性主題的報道來探討20世紀初期英國女性的社會地位的問題,就是試圖避免落入過度依賴數據、依賴宏觀的政治經濟描述的窠臼中去。盡管“用數據說話”“如實描述事實”更能顯示出其傳統而“恒久”的權威性和清晰度,但是,我們決心以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探討女性主義的問題,試圖發現掩蓋在傳統話語權威性下的當時英國婦女社會地位的真實情況。
我們要討論的報道是《每日見聞報》第1902期(1915年4月14日)的一篇題為《士兵子女的未婚媽媽》(Unmarried Mothers of Soldiers Children)的文章。這篇報道在開頭附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作者是一位名叫梅尼爾的議員。這篇報道正是基于這段文字在當時引起的巨大輿論沖擊來寫的,這段文字是梅尼爾議員前一天寫給《晨報》的一封信的摘要 :“人們可能不知道,在部隊駐扎的全國各地,大量的未婚女孩兒在幾周內成為母親。僅僅在一個城鎮(town)就有超過2000個案例。”顯而易見,這篇文章報道并且討論了當時出現的英國士兵在駐扎地有了私生子的現象,而且這種情況不是個例,“即將出生的私生子總數達數千人”,甚至比一般人想象得更加嚴重,“其中有幾個準媽媽自己也只是個孩子”。在報道的后半部分,報道的撰寫者列出了當時幾位社會上的權威人士對于這件事情的看法。
報道的撰寫者強調了生命權利之于每個人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這些嬰兒是無辜的,應該享受與他人平等的公民權利。可是接下來他說,這些私生子們是在馬恩河、伊普爾河、新沙佩勒河浴血奮戰的英雄們的后代,所以孩子們是不能被冠之以污名(stigma)的。那么,這些孩子的母親呢?撰稿人寫道:“在目前的情況下士兵子女的母親不應受到蔑視或羞辱。”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目前不是戰爭期間或者說孩子們的父親不是英國現役士兵,這些私生子的母親(包括未成年人)就應該受到譴責,并且(根據下文內容來看)只有女性這一方應該受到譴責。但是這位作者繼續寫道,英國的民眾應該拋開既定的偏見,不能要求士兵們“為不道德行為埋單”(setting a premium on immorality),并且呼吁政府和立法機關立即通過立法對有關私生子的法律進行大幅度地改革,不能再因為道德上的“刻板印象”使得男性士兵們受到原有法律的懲罰。報道接下來列舉了其他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其中一位身份不明的名為格雷厄姆·默里的女士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她告訴《每日見聞報》的記者,這個問題將由一些“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婦女來處理。她說,這個問題如此重要、如此緊迫,公眾絕不能推卸責任。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首先是那些已經陷入困境的可憐的女孩兒,還有那些到目前為止已經逃脫的女孩兒,她們即將面臨危險。國家的榮譽岌岌可危,國家必須以最好的,同時也是最微妙(delicate)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我們至少可以從她的話中抓住兩個關鍵要素,第一是有一些女孩兒在這件事情被發現之后已經逃離出走,并且生活面臨困難的處境﹔第二是這件事情由于與英國正在服役的男性士兵有關系,所以她認為處理起來應該采取一種微妙的手段,即不能夠損害男性士兵以及英國的國家榮譽。還有一位名為阿爾弗雷德·B·肯特的受訪者,他是當時一個名叫“榮譽聯盟”(Alliance of Honor)的組織的負責人,并且“長期致力于保持社會的純潔性”。這位負責人說,(社會上的)邪惡肯定是存在的,當很多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幾乎必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他們(應該指“榮譽聯盟”的成員)已經通過牧師長向遠征軍和駐扎在營地中的男人們發行了一百萬份名為“做個有思想的人”的小冊子。肯特說,有大量的證據表明許多年輕的士兵第一次面對誘惑(temptation)的時候堅守了自己的正確立場。一位在倫敦慈善事業中的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名叫約翰·柯克的爵士認為,如果“父親從戰爭中歸來,并能被找到時,他于道義上應該與孩子的母親結婚,并在法律上負責撫養”。
在《每日見聞報》第1910期(1915年4月23日)報紙的第四頁,一篇文章回顧了這件事情并且報道了最新情況,作者給這件事情起名叫作“戰時寶寶”(War Baby)事件。文章提到,在一次旨在解決這一問題的會議中,人們都對那些在非正常情況下成為受害者的女孩兒表示“善意的同情”,但“沒有對(她們)所犯的輕率行為進行任何寬恕”。有一位讀者在寄給《每日見聞報》編輯部的一封信中寫道:“如果在營地安排幾個明智的已婚男子,每個人配備一條馬鞭,用來鞭打所有喜歡閑逛的年輕女孩兒,這將是結束這種麻煩的一個更快的方法。”
五天之后,也就是1915年4月28日,《每日見聞報》的第1914期上又出現了有關這件事情的報道。撰稿人在名為“戰時寶寶的母親們”的報道的第一行的導語中寫道:“斯科特·里奇特(Scott Lidgett)博士解釋了如何幫助她們:‘不要讓她們成為女英雄(heroine),但女孩兒被直接扔到貧民區的話恐怕會演變為一場災難。”報道的主要內容和前兩次沒有太大差別,仍然是刊登一些社會名流對于這件事情的看法。第一位發表看法的人就是這位斯科特博士,他表示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并與許多重要的國家機構進行了溝通,進行了充分的調查。他認為,民眾應該注意不要讓這些女孩兒成為女英雄,但同時要對她們給予“最大的基督徒的同情”,并且給予她們必要的援助。在這之后,這篇報道又展示了前兩篇報道中沒有寫的兩個細節。第一,有許多“戰時寶寶”的軍人父親是已婚的﹕“還有一個困難是,許多父親是已婚男人,在其他情況下,不可能只把責任歸咎于一個男人。”第二,這些年輕母親的具體年齡﹕“一個女孩兒在第一次墮胎后被介紹到一個工會的產房,這對她以后的健康來說是致命的,有許多案例的母親是16歲和17歲的女孩兒,而14歲的女孩兒成為母親的案例也不是沒有。”在報道的最后,一個名叫斯賓塞的教士說,一些報紙上對英國軍人的行為使用了不真實和不公平的描述,他們的牧師長從英國軍隊的各個部門得到保證,部隊在各方面的表現都“非常好”(wonderfully good)。
有學者在研究20世紀初期英國女性地位時把注意力放在了另一份戰爭期間的報紙——《戰時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War News)上。與我們討論的《每日見聞報》的私人所有和商業性不同,這份報紙由倫敦畫報與素描有限公司(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d sketch,Itd.)發行,被英國政府承認為是與英國國家觀念一致的權威報刊,同時在英國本土和一些海外自治領地發行。《戰時新聞畫報》同樣開辟了女性專欄,關注女性在戰爭中的情況。這份報紙使用了大量的圖片來表現女性在工作崗位上的積極、快樂、輕松的形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表現的是女性在工作之余休閑和娛樂的場景。但事實上,女性在工廠中工作的時候,不僅面臨著被德國飛機轟炸和原材料爆炸的危險,而且還長時間在沒有保護裝置的情況下接觸有揮發性的化學品。她們在這種環境下每天的工作時長可能達到十二個小時之久。在《每日見聞報》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類似的事實,一篇名為《女性工人會成功嗎?》(Will Business Women Succeed?)的報道中寫道:“今天是女工的日子,許多新的職業現在向她敞開了大門……但是,由于女性的健康狀況比男性更容易波動,如果她們對自己的健康要求看得太輕,那么有許多人就會早早陷入困境。緊張的壓力、長時間的工作和長期的精神和身體疲勞,使血液變稀薄,神經變脆弱。這種情況只有在強壯、血氣方剛的體質下才能有效忍受。這對男人和女人來說都是如此,只有‘弱女子(weaker woman)受害最深。”《每日見聞報》第1913期(1915年4月27日)的一則題為《一個呼吁》(An Appeal)的報道中說:“有人愿意把海邊的小屋借給一位牧師的妻子嗎?她有一個非常嬌弱的小女孩兒(四個中的一個),她需要大海的空氣,她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這樣的改變可能是拯救她生命的手段。”
從上述這些細節中我們不難看出,隨著戰爭的深入,英國的男子由于大量參軍并且投入戰斗之中,社會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升。甚至在冷酷森嚴的維多利亞主義的道德世界之中,一些男子致使包括14歲少女在內的女性未婚先孕,不僅仍舊被稱作“英雄”,而且不用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輿論甚至呼吁立法機關通過修改法律來盡可能減輕他們將會面對的懲處。而那些年輕女性卻面臨著整個社會的鄙夷(前文提到,名叫肯特的“榮譽聯盟”負責人甚至用了“誘惑”一詞),唯一的解決方法只有“出逃”并在這以后獨自面對生活的艱難。也就是說,至少是從這些報道的內容來看,戰爭非但沒有提升、反而降低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蘇珊所謂的帶有“保護傘”的描述(通過數據證明戰爭后女性得到工作機會,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顯著提升)和真實情況(男性是明智的、英勇的,女性是無能的、魅惑的)之間的巨大差別。
在《每日見聞報》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了當時經濟上處境悲慘、社會上話語權弱、對男性和家庭依賴性強的英國勞動婦女群像。通過詹姆斯·蘇珊有關“保護傘”描述的理論,我們得以重新使用一種批判性的視角來看待以往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結論,并且能夠基于這種理論和多樣的社會現實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長期以來,海外以男性學者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學術界利用數字圖表和與政治經濟高度相關的男性特有的思維模式描繪這一時期英國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的“客觀”圖景,實際上已經遭到了女性主義思想家的批評,這值得我們深思。
基金項目:蘭州大學萃英學生創新項目“20世紀初期英國女性主義思潮與《每日見聞報》”。
[作者簡介]呂文澤,男,漢族,天津河東人,蘭州大學萃英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為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