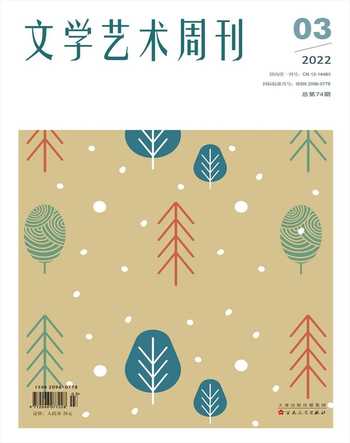康熙四十三年山東荒政與捐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山東地區發生了罕見的大水災,康熙四十三年(1704)又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水旱災情接連而至,引起了山東各地饑荒,社會動蕩不安。康熙帝南巡親見黎民受災慘象,即刻采取了一系列賑災措施。山東捐納事例便是康熙年間較為典型的賑捐事例之一,但后續也產生了諸多問題。
一、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山東受災情況
清代山東地區災害頻發。袁長極等在研究清代山東地區受災情況時統計得出,山東曾發生旱災、澇災200年次以上,幾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旱災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縣統計,山東旱災、澇災都達3500縣次以上,全部水旱災害達9000縣次以上,平均每年受災縣數超過30,占全省縣數三成以上。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便是其中受災程度較為嚴重的年份。
據《清史稿》載,從康熙四十二年五月開始,東阿、江陵等地水深數丈,青城、陽谷陸地可行舟。七月以后,登州、濟南大水。這場大雨在慶云、東明持續三旬之久,沾化、高密、鄒平、齊河等地房屋、莊稼被毀壞者不計其數。至康熙四十三年,山東地區又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旱災,“(康熙)四十三年春,青浦、沛縣、沂州、樂安、臨朐旱”。 淄博人蒲松齡親歷了此次大災,其所作《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秋災記略后篇》等較為形象具體地再現了大災時的場景。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十九以后,“更無滴雨到地,人無復望”“田深半尺無潤土”“而一冬無雪”。盡管期間農民嘗試耕種,但終因“未得霖雨”,各種農作物都歉收,最終導致六郡饑荒,糧食價格騰貴,麥粱一斗達七百文,菽粟五百。可見此次干旱時間之久、程度之深。不僅如此,蜚災也接踵而至,危害莊稼。
災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嚴重的饑荒,糧食稀缺,災民只能以樹皮、樹葉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遙望玉樹成林,楊柳槐因葉及枝,髠之童童焉”,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悲慘場景,人們凌晨驅趕驢車將人肉運至市場售賣,價格甚至只有羊肉的十分之一。時任巡視東城福建道監察御史李發甲奏《請撫綏災黎疏》,言辭中也可見山東受災程度之深。疏中描述了人們無糧可收,只能爭搶水草、劉莖、榆樹皮等充饑的悲慘景象,嚴重的饑荒導致社會動蕩不安,盜竊、流浪乞討、賣妻鬻子、人相殘食的場面比比皆是,“此情真,大可憫也”。
二、政府的賑災措施
康熙四十二年初,康熙帝第四次南巡視察河工,途經山東,親見山東被災甚重,對此“不勝憫惻”。實際上,此次山東的災情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末便有所關注。《清實錄》中記載,康熙帝南巡至德州時,便留意路上的災民,并對此深為軫念。因此,康熙帝及時地采取了一系列賑災措施。
一是派遣官員賑災。從康熙四十一年年末得知山東部分地區受災開始,康熙帝便行令地方官“發票散賑”。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康熙帝下令滿漢官員或革職降級贖罪人員且情愿往沂州等四處者,同地方官分界賑濟。“俟養秋收后,酌量議敘或給銀米。如有情愿去者,有一二人即行啟奏,若等齊多人啟奏,恐誤窮黎耕種”。至七月,又增派佐領,籌集銀兩。康熙帝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一千多佐領每三人出一人,共計三百人;每三人再交銀三千兩,分派各地,奉命養民。隨后,康熙帝又指派三路應差大臣分別賑濟山東饑民。“自泰安至郯城為中路,著穆和倫去;自濟南至登州為東路,著辛保去;自德州至濟寧為西路,著卞永譽去。”政府不僅派遣官員前往山東,對于逃亡至京城的災民也予以安置,“著八旗每旗滿洲蒙古漢軍在各旗內外尋好地方,分為三處煮粥賑濟,每日佐領下有壯丁百人,每人要錢一文,一佐領下百文,十佐領下一千文,朕限每佐領不過百文,所得甚易,亦甚有益,八旗王等亦著于八旗內外賑濟”。康熙帝還令鑲黃旗小舅舅、正黃旗內大臣明珠、正白旗內大臣阿爾達、尚書馬爾漢分別派家仆賑濟,并對各路賑濟官員嚴格要求,“若養濟不周、怠玩,朕查出將都統、副都統絕不輕貸”。
二是蠲免錢糧。蠲免,是指國家對百姓應征賦稅的免除。清朝的蠲免主要集中在康熙中期至乾隆在位時期這百余年間,其中康熙在位時期則是大規模蠲免的發端時期。面對山東地區來勢洶洶的災情,康熙帝蠲免了諸多地區。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蠲免萊蕪、新泰、沂州等地被災州縣第二年地丁錢糧。康熙四十二年正月,蠲免南巡所經德州、禹城、聊城等二十州縣上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免征濟南府、兗州府被災十二縣上一年未完錢糧;十一月,免山東武定、福山等五州縣本年份水災額賦有差。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免山東濟南等府屬九十四州縣、衛所上一年水災額賦,并緩征本年漕運;十月,再次將山東下一年應征地丁銀米通行蠲免。
三是截留漕運。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康熙帝經泰安、新泰、蒙陰等州縣,指出多地倉谷年久朽爛,不益于賑濟,下令截留漕運。先交付漕運總督桑額兩萬石漕米,挑選賢能官員,送往濟寧、兗州等處即刻賑濟。同時桑額再將兩萬石米于泰安一路救荒。七月,又截留漕運尾船。差遣戶部司官火速前往截留漕運尾船米五十萬石,交于山東地方官。后康熙帝駐蹕博洛和屯,仍然密切關注此事:“截留漕糧,亦屬緊要。總漕桑額見今無事,著做速前來,親看截留。其賑濟饑民人員所領銀兩,雖系公物,而勉力自效,有濟于民。事竣回府,一并議敘。”
朝廷雖十分重視這次災荒,實施了諸多賑災措施,卻也難免出現了一些問題。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派張鵬翮、桑額分別運漕糧二萬石赴山東賑濟,時任山東巡撫王國昌卻擅自將程兆麟所運漕米和當地常平倉米谷用以散賑糶賣。這與康熙帝本意不符,因此令王國昌速行賠補。王國昌回奏稱將捐康熙四十二年和康熙四十三年的官員俸祿、衙役工食等賠補,帝不予。
王國昌則繼續上疏請求開辦事例以補其擅自動用常平倉之米谷:“新、泰等州縣復被水災,請將倉谷二十余萬石,并應運漕米十余萬石平糶,但倉谷不便久懸,仰祈圣慈,暫開事例,以實倉貯。至動用漕米,擬將康熙四十三年以后俸工捐補。”但其主張被一一駁回,戶部要求王國昌于次年秋后將擅自所動平糶銀買谷還補;對于其所捐俸工銀,令該地方官用來買籽粒牛只,予民耕種;不許開辦捐納事例。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御史顧素彈劾王國昌隱匿災情,與布政使劉暟欲開事例補虧空。此事最終以相關官員均攤賠完,王國昌卸任、劉暟流放結束。
三、捐納的實施及問題
直至康熙四十三年十月,時任山東巡撫趙世顯奏“山左元氣初復,應廣積貯”,提出參考甘肅現行事例,并酌量加贈,開辦山東捐納事例。相關條例如下:
文武官員捐米三十石紀錄一次,一百石準加級不隨帶,二百石準加一級隨帶,多者以此計算。不論旗民,例監、廩生捐米八十石,增生九十石,附生一百一十石,俊秀一百五十石,俱準歲貢。不論旗民,俊秀子弟捐米八十石,廩生四十石,增生五十石,附生六十石,青衣生七十石,俱準作監生。量增款項:文武六品、七品官員,捐米一百二十石,四品五品一百八十石,三品以上二百六十石,教職捐米七十石,給與應得封典,候選候補一體捐納。除正項錢糧未完不準捐納外,文武因公罰俸、停升官員,罰俸一年者捐米一百石,三個月照半年之數,九個月照一年之數捐納,準其銷案;罰俸銀兩仍行扣追。內外文武官員降級留任者,每級捐米二百石,準還原級;革職留任者三品以上一千二百石,五品以上六百石,七品以上三百五十石,準還原職。武生捐米七十石,準作監生。以上登、萊、青照此捐納,濟南府近河,每十石應加二石。
由于此次捐例是參照甘肅現行事例,根據資料記載,符合該地點和時間的捐例唯有康熙四十二年的甘肅常平事例。兩次捐納的具體條例內容,除了因地制宜的條例,其他的條例基本吻合,只在價格上有所不同,這是兩地發達程度所決定的。相關條例如下:
不論旗民、文武官員捐米二十五石,紀錄一次,八十石準加不隨帶一級,一百六十石準加級隨帶一級,多捐者以此計算。不論旗民、俊秀子弟捐米六十石,廩生捐米三十石,增生捐米四十石,附生捐米五十石,青衣生捐米六十石,俱準作監生。不論旗民、例監、廩生捐米七十石,增生捐米八十石,附生捐米一百石,俊秀捐米一百五十石,俱準作歲貢。
此次捐納事例在實施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康熙四十四年(1705)工部尚書王鴻緒在密折中詳細陳奏了山東養民議敘案內的具體問題。
其一是對官員的議敘過優。根據以往的議敘條例,最多者是升一層,次之為即用或加級紀錄,或免罪,或給予虛銜。而在此次議敘中,多數官員連升兩層,又加即用,完全超出了一般的議敘標準。王鴻緒在奏折內列舉了諸多議敘過優的官員。如原本任員外的顓圖、查爾欽俱升兩層為侍讀學士等官,只捐銀三四千兩;甚至還有官員連加三級。王鴻緒感嘆“今戶部議升一層又升一層,又有即用,又有加級,公論以為太濫”。還有借通倉米同知魏荔彤、員外劉啟楨、同知李元龍、員外程建等官員,分別以道缺即用、以道府缺即用候選,以道員即用,以道府缺即用。可見此次議敘中即升兩層、又有即用的官員甚多。除此之外,筆帖式及主事中的各小京官、旗官的議敘過程中亦有此類現象。
其二是議敘資格放寬。在康熙朝諸多捐納事例中,如貴州捐納事例、大同張家口捐納事例、甘肅捐納事例,都有“貪酷、大計、軍政、失陷城池擬罪革職官員不準捐納”一條,戶部捐銀事例也規定大計、八法及貪酷侵盜錢糧官員不準捐納。但在此案中,均有此類官員捐銀以原官補用。原任知州鈕公旗曾以酷刑使得三人喪命而被革職,此次卻準其官復原職;原侍讀秦布獲罪已交刑部,卻也借此次機會以原官補充;原知州謝廷璣身有未完錢糧之罪,所欠銀五萬兩、米一萬石未完,此次只捐銀一千二百兩便補用原官;更有行為不端者靳治豫、席永勛均捐銀以原官補用,而席永勛卻是一富商,其中不符規格之處甚多。
其三是虛冒頂替。印結早在康熙初年的乙卯捐例中就是報捐時不可或缺的文書,報捐者必須同時提供同鄉五、六品京官出具的印結,用來確認報捐者的身份。康熙二十九年(1690)時,行令各督撫將捐納官員三代履歷、籍貫年貌及有無假冒頂替情弊逐一詳查﹐如有假冒頂替者,則從重治罪,出具印結的地方官員及督撫也要一并議處。而在此案中,卻出現了大批虛冒頂替者,且皆出自東平州。王鴻緒在奏折中指出﹕“又三路養民大臣,止有卞永譽一路,伊奏折內曾有旗員子弟養民之語,然并未曾啟奏姓名出來,今該撫補咨到三十余員內,二十六員皆東平州印結,聞名字多有挖補,不無虛冒。”
其四是戶部在捐納議敘中權力過大。吏部侍郎希福納對于戶部議敘過優之事頗有微詞,與選司郎中提出止升一層,認為連升二層、又加即用等議敘處理有損名器,戶部卻堅決不同意。禮部侍郎、兵部侍郎雖有怨言,卻也無權左右戶部的決定。可見戶部在捐納事例中的主導地位。王鴻緒指出,“今戶部亦一概從優議敘,公論不平”,滿吏部侍郎希福納曾言此事聲名差矣,始終不與,且不愿前來同議。王鴻緒兄長王九齡與選司郎中王奐魯諫言議論官員止升一層,但戶部滿堂司不允。后王九齡因病在寓,王奐魯一人也不敢再言。禮部侍郎邵穆布、兵部侍郎梅鋗雖有異議,但戶部皆不理會。一切以戶部主議之,實為不公也。
山東捐納事例的開辦利于山東地區的災后民生重建,但在實施的過程中也引發了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議敘之法對吏治的損害,出現了用銀免罪、復職、冒名頂替等不良現象,政府部門在處理問題期間也漸失平衡。
[作者簡介]汪茹,女,漢族,安徽合肥人,揚州大學歷史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