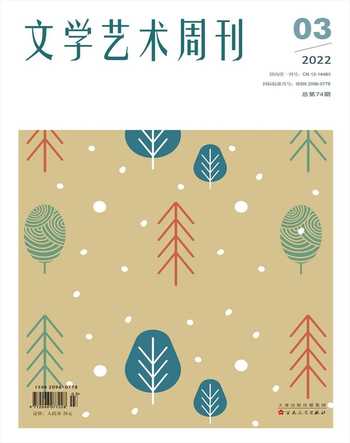從《山海經》中窺探音樂起源問題
《山海經》是中國先秦的一部重要古籍,其內容無所不包,蘊含著豐富的各類學科知識,其成書時間大致在戰國時期至漢代初期,地點主要是戰國時期的楚地和巴蜀。現存《山海經》的最早版本為西漢時期劉向、劉歆父子校勘而成,其書名最早在《史記》中被提及。由于《山海經》覆蓋地域廣、時代跨度大,創作者身份因此撲朔迷離。通過書中與音樂相關的敘述,可以大致判斷書中所記載的音樂為我國新石器時期至階級社會初期的音樂,這些敘述里有樂器的描述,也有先民們對音樂的認知及看法。對此,筆者將《山海經》中有關音樂的字眼進行羅列,并橫向參考了西方眾多學者對音樂起源的看法,發現其中許多材料對研究中國的音樂起源問題助益頗多,對于探討音樂產生及演變軌跡有重大價值,并揭示了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音樂起源的異同。本文中,筆者將《山海經》中對于音樂的具體描述與現有音樂起源推測相結合,整理出自然模仿、巫術、勞動、樂器、作品五個方面進行探究,盡可能揭示出不同觀點中的音樂雛形及細微變化。
一、自然模仿說
自然模仿說是基于人對自然界客觀事物的“模仿”。音樂的起源首先基于自然與人,人對客觀事物做出主觀反應后,利用自然界進行模仿并改造,才有音樂起源于“自然模仿”一說。《山海經》中有關自然模仿說主要從外界事物角度出發,如動物行為、聲調等,并通過行為模仿、聲音分析等進行音樂闡釋。
《山海經》中提到音樂最多的是與動物相關的部分。《山海經》中最早提到有關音樂的文字是在《南山經》中“……有獸焉……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謠”即歌聲,《爾雅·釋樂》中的“徒歌謂之謠”也說明了“謠”即原始的歌聲。關于歌謠的起源,近代學者朱自清在他的著作《中國歌謠》中提到了歌謠的產生早于文字,起初靠口耳相傳,并且具有繼承性特征。筆者在綜合眾多學者觀點后,認為在文字出現之前,歌謠就根據人的本能所產生,并以口耳相傳的形式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從《山海經》來看,歌謠的形式在當時已趨向完備。《山海經》中還大量使用動物的聲音來進行比喻,如“其音如牛”“其音如狗吠”“其音如鴛鴦”等,以及上文提到的“其音如謠”,這些敘述一方面體現了自然界聲音對人的模仿產生的啟發,另一方面說明該時期已出現類似口頭形式的歌,并且人們利用原始思維,把已經認識到的音樂用在說明自然界的各類聲音中,表現了音樂自然模仿起源說的雙重性特質。
《山海經》中還多次提及了鳥類的歌舞,如“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這種擬人化手法同樣是人類對自然模仿的展現。現如今在我國仍有許多民族將鳥、鳳凰等作為本民族的圖騰。遠古時期的民族大多沒有文字,他們傳達信息、日常生活、表達情感等方面大多依靠聲音、形體、歌謠來進行,形成了歌、舞、樂為一體的傳統,并有著自然崇拜等因素。《呂氏春秋·古樂篇》中也記載了伶倫聽鳳凰之鳴作律的傳說,說明遠古時期人類會對動物發出的叫聲產生主觀判斷,也表達了鳥類聲音的多樣性以及人類通過鳥類鳴叫對音樂產生認識。鳥類的聲音在人類早期接觸的自然界中較常見,聲調的變化豐富且復雜,對先民認識早期的律調有重要模仿作用。音樂的起源是人們未有語言、文字時對世界客觀的反映,音樂的出現或許會對語言聲調產生幫助。此外,《山海經》中的鳥類歌舞還說明了原始歌舞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將鳥類擬人化,表示歌舞會帶來和平安寧。早期儒家學說也提到了“樂者樂也”,即音樂是為了快樂。在古代節日儀式中,大量例子都記載了人們扮成鳥的形象進行諸多樂舞活動,并展現當地習俗,這對于自然模仿說是很好的佐證。
二、巫術說
遠古時期宗教的產生可能來自原始人對自然的敬畏,并且從當時嚴峻的自然環境來看,大多數先民相信“萬物有靈”,更多將精神寄托于自然、鬼神等,崇拜各種比人類更強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山海經》中記載了大量有“巫文化”特色的宗教活動,展現了多樣的祭祀文化與禮儀,并將樂舞等音樂文化滲入其中。在《中山經》中提到了“用兵以禳;祈,璆冕舞”,“禳”表示向鬼祈禱消除災殃,并且手拿盾牌舞蹈,祈禱消除戰爭。這里提到了樂舞在原始社會中的效用,一方面是音樂與宗教的關聯,常用于巫術等宗教性質的活動中;另一方面從其手持盾牌的舞蹈可以得出,樂舞在戰爭上的價值被普遍認識,原始民族常利用音樂以輔助戰爭。此外,還有《中山經》中“合巫祝二人儛”“干舞、置鼓”等,鼓是祀神“干舞”的伴奏樂器,利用鼓樂器為巫舞進行伴奏,一方面說明了早期鼓等簡單節奏樂器已被使用在重要事項中,另一方面也說明此時音樂的作用已廣泛滲透進宗教活動中。
從《山海經》的成書時間及成書地點來看,從西周到戰國中晚期,南方楚地諸族文化皆彌漫著神話、巫術的氣氛。東漢王逸在分析《九歌》的產生時認為,楚國“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說明在階級社會早期南方等地因祭祀等活動事項而作樂,樂舞在此時是作為重要的人類活動而存在,但存在于較小范圍,對音樂的固化及后世很長時間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具有局限性,以至于琴瑟等樂器的起源問題在中國其他古籍中也被注入“巫文化”的特征。劉亞虎認為,從屈原《九歌》的篇目中可以想象當時楚地有關神歌巫舞的風貌神韻,它們當是較早時期南方民族的敘事形態。在“巫文化”的注入下,樂舞在祭司、巫師等群體中異常活躍,雖長期在小范圍傳播,形式逐漸固化,但對音樂文化的傳承與保存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山海經》中所記載有關“巫文化”的宗教音樂,同樣具備傳承性質。如今在傈僳族、布依族、苗族等南方少數民族中依然保留著帶有宗教性質的音樂文化,并且這些帶有民族傳統的音樂活動群體成為了長詩體神話演述的主體,在各種節日儀式中展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樂文化。研究現有少數民族宗教音樂文化的展現,可以逆推出人類社會早期“巫文化”音樂的特點。
三、勞動說
勞動說在西方音樂起源中被眾多學者認可。從新石器時代至階級社會早期,先民發現事物發生的節點、事物的前進方向、文化的產生皆與勞動密不可分。《山海經》中大量記載了階級社會初期人類的勞動狀況,并用比喻的方法進行詮釋。如《南山經》中有記載:“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說文解字》中,“判”的含義為“判,分也”。“判木”就是剖開木頭,“其音如判木”就是“聲音像剖開木頭的聲音”。從“音如判木”可以看出,“旋龜”,古人理解其叫聲像劈開木頭時發出的聲音,是根據自身勞動生活中所聽到的各類聲音等經驗得出的。《海內經》中也記載,“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鶯鳥自歌,鳳鳥自舞”,說明此時人類已經開始學會種植,并且可以利用自然自給自足。用擬人化來看待,人類在播種收割時音樂已滲透其中,在勞動時用口頭形式將音樂進行傳播與交流,并在勞動過程中利用音樂進行自娛與放松,說明此時音樂的使用已經擴大到人類所需的各種范圍。現存的勞動號子便是有利佐證,分析勞動號子的起源及發展,可以推測出古代先民在勞動中使用音樂的情景。
四、樂器說
《山海經》的成書時間漫長且內容繁雜,其中記載了大量不同時期樂器產生的傳說及起源。由此筆者認為音樂的起源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古人制成的樂器及其產生的樂律等一系列與音樂相關的問題。古人在鉆木取火時已經會制作石器,在敲打過程中的節奏及音響會不會也激發了人的聽覺以及其他本能,從而制成石磬、鼓等簡單的敲擊樂器呢?前文中提及鼓已經用在重要的宗教儀式中,而在這之前應是發現樂器材料的問題。《中山經》有云:“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鳴石。”“鳴石”是一種青色玉石,撞擊后會發出巨大鳴響,傳說古人會用它來制作樂器,如石磬之類。還有《西山經》中所記載的“其陰多磬石”,“磬石”指用來做樂器的石頭。由此看來,遠古時期的樂器大多是未經改造或制作的、可以發出聲音的原始材料。在樂器的制作方面,筆者認為有存在環境及材料選擇兩方面原因,先民所處環境反映了樂器的材料選取,而選擇材料時則會篩選對比聲調的不同、制作的難易程度等,反映了先民們在音樂概念之上對于音樂載體的認知雛形。
此外,由于《山海經》的成書時間較長,其中還有大量已成型樂器的描述,如《西山二經》中“其音如勃皇”,“勃皇”是指吹奏樂器時薄膜發出的聲音,說明此時人們已經會熟練使用吹奏樂器并懂得其制作程序。還有《西山經》中“其音常如鐘磬”“鐘山。其子曰鼓”“音如鼓音”,《大荒東經》中“……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筆者認為,在遠古時代,打擊樂器應該是最先出現的,并最先被用在諸多重要活動中。《山海經》中關于樂器描述的內容多出現“鼓”這個字眼,表明原始民族的樂器大多為按拍的,以打擊樂器為主,最常見的是鼓。
五、音樂作品說
大量《山海經》中有關音樂作品的描寫都在《大荒西經》部分,而《大荒西經》的寫作手法與《山經》《海經》風格迥異,文中記載了大量的神話傳說,各類王國、神話人物層出不窮,荒誕且伴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在音樂記載方面,對音樂作品的背景、出處也大多帶有神話、自然崇拜的意味,雖不能全部列為信史,但也從側面印證了作品及人物的產生時間。《大荒西經》中有記載“……是處榣山,始作樂風”。相傳祝融是華夏族上古神話人物、火神,祝融的兒子太子長琴住在榣山,并創作了一系列音樂,他創作的作品在世間傳播,并風靡天下。《大荒西經》中還提到:“……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據《竹書紀年》載,夏朝君主稱呼前冠以“后”字,“開”本為“啟”,夏后開即夏后啟,是因為避漢景帝劉啟諱而改作了“開”。這里夏后的形象“珥兩青蛇”“乘六龍”也頗有神話的意味。他曾三次到天庭拜訪,得到天帝賞賜的《九辯》《九歌》這兩首天庭之樂,啟便在“天穆之野”表演天帝賜予的大型樂舞《九招》,其中的“九”表示陽數,寓意“天”“天子”。“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也”,郭璞認為《九歌》《九辯》本是天帝用的神樂,夏后啟私自從天上偷下了《九辯》與《九歌》,從而使世間產生了音樂。該段對于“天”的敘述非常之多,一方面帶有宗教性質,同時也體現出遠古社會人們對音樂的崇敬之意。對于音樂起源“作品”一說,《山海經》中所載主要從自然崇拜方面進行闡釋,原始先民在祭祀、節日等活動中都會使用音樂,對神鬼的崇拜觀念較深刻,認為好聽的音樂是從天上傳來,并在其基礎上加工改造,利用樂器等進行音響的比較,從而創作出優秀的音樂作品。
六、結語
關于音樂起源至今依然眾說紛紜,對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多種闡釋。音樂起源研究最初在西方盛行,但研究領域始終停留在其自身所在的文化圈中,對于亞洲音樂文化的最初形態了解甚少。《山海經》作為中國早期的歷史文獻,其中大量神話傳說、各式奇異怪談始終不被列為重要研究范圍,但在仔細閱讀并分析其中有關音樂的材料后,可以得到諸多有關音樂起源及各類說法的具體印證,并可以與諸多西方說法相對應,說明了多文化圈層早期音樂的共同點,也得出音樂充斥了原始社會的重要文化事項與文化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中國音樂起源研究的支線空白。書中對西方提出的自然模仿、巫術、勞動等音樂起源的推測皆有描述,對打擊樂器的描寫甚多,這與非洲音樂起源最先出現鼓樂器不謀而合。而其中對樂舞的諸多描述、樂舞一體,印證了早期藝術的統一性及相關性。對于樂器材料的使用及選擇,書中也給出對早期人類社會環境的描述。音樂起源由諸多復雜因素交織而成,是人類早期顯現的重要文化雛形。《山海經》作為一部包含眾多因素的地理志,對處于不同自然環境的音樂也有不同記載,造成了音樂起源問題要多維去探討研究的現狀。筆者希望通過《山海經》中對于音樂的闡釋,更深層次地挖掘我國先秦時期對于音樂的說法及不同認知,并從時間上探討《山海經》中所描繪的人類生產生活變化給原始社會音樂文化發展帶來的影響,使有關音樂起源的思考趨向多元化。
[作者簡介]彭楓,女,漢族,山西太原人,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音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