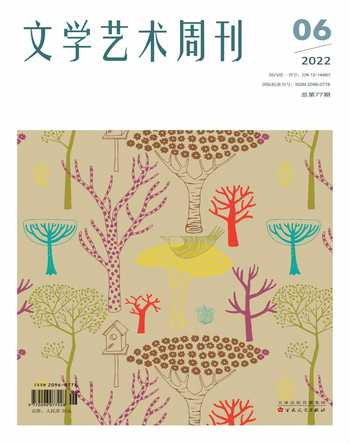傳統文化類綜藝節目的“Z世代”圈層突破研究
王怡然 李靜
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曾發布研究報告,將“Z世代”定義為1995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由于他們的成長深受移動互聯網的影響,因此也被稱為互聯網世代。《2020年“Z世代”洞察報告》統計指出,中國“Z世代”群體的網絡活躍用戶已經達到3.25億,占全網移動網民的28.1%,且近兩年來呈不斷增長趨勢,其使用互聯網時長月均175個小時,可見“Z世代”越來越成為新媒體不可小覷的新生力量。
一、“Z世代”群體的特點
(一)知識訴求
在信息愈加碎片化的時代,“Z世代”與上一代人相比,更愿意在網絡中了解世界、充實精神世界,也歡迎更多傳統文化類節目的出現,這體現出“Z世代”仍有很強的文化自信。不僅如此,“Z世代”也更關注國潮文化,聽國潮音樂、穿國潮服飾、看國潮綜藝已成為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其對于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化更樂于接受,這些標簽特點也使得“Z世代”群體在快速發展的新媒體時代中,對于信息的獲取和表達日益凸顯。與此同時,“Z世代”上網需求也逐漸從娛樂化轉向知識化。新浪數據中心在調研平臺投放的12329份《年輕人群興趣調研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43%的“Z世代”更傾向于為知識付費。而《“Z世代”行為年度報告》顯示,10個“Z世代”里就至少有2個愿意為知識付費。“Z世代”從新知內容中獲取知識,為高品質內容付出時間和注意力,主動為知識付費。
(二)圈層傳播
作為伴網而生的一代年輕群體,“Z世代”不僅更樂于為興趣付費,而且其社交模式也有明顯的特點。他們往往會將自己的個性特點融人以興趣為紐帶的群體圈層中,分享自己的觀點,使其在追求自我的同時獲取群體認同,對于感興趣的新鮮事物會樂于分享到社交平臺進行交流探討。不僅如此,一個圈層的熱門討論甚至會跨圈層傳播。近幾年來,不少教育家、學者、輔導機構紛紛入駐抖音、微博、嘩哩嘩哩網站等互聯網媒體平臺,分享人文、社會、歷史、考試等相關信息或專業知識,增加了平臺的知識性,逐漸促使平臺的年輕使用者在娛樂的同時學習和提升。在2020年五四青年節之際,嘩哩嘩哩網站發布的名為《后浪》的視頻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并在年輕群體的朋友圈內“刷屏”并引發討論。雖然對“后浪”一詞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引發的熱度足以達到破圈狀態。
二、《典籍里的中國》創新呈現
(一)媒介傳遞:頂層設計引領文化傳播
為了更好地傳承與傳播傳統文化,各媒體平臺文化類節目呈井噴式增長,《國家寶藏》《上新了·故宮》以及河南衛視的春晚節目《唐宮夜宴》等多元中國文化題材類節目一經播出便受到年輕群體的關注與喜愛。《典籍里的中國》的播出更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題材節目更廣闊的未來。通過運用影視化語言吸引觀眾主動觀看學習優秀文學典籍,例如該節目邀請大眾心中認可的演員對古籍中的人物進行塑造,比如倪大紅飾演的伏生、李光潔塑造的宋應星,王學圻、張曉龍分別扮演的司馬遷,還有節目中穿越不同時空的當代讀書人撒貝寧跟賢者對話等精彩環節。通過對人物與作品中的故事進行演繹,讓更多年輕人感受中國文化中蘊含的文化精神與文化自信,在媒介的自我表達和分享的實際行動中,將古籍中的精神財富傳承與發揚下去。
(二)故事化敘事:展現傳統與時代的碰撞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古代先賢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一直流傳至今,而面對時代的發展,一批文化類節目也正在以強大的文化底蘊與新媒體創新傳播,用這些精神財富吸引“Z世代”群體的目光。中央電視臺積極迎合時代發展,吸引“Z世代”的目光,連續出品了《國家寶藏》《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說話》等精品節目,收獲“Z世代”年輕人的一致好評和廣泛傳播。
《典籍里的中國》播出至第四期,全網播放量便已達2.5億。《典籍里的中國》將古典書籍的故事搬上舞臺,節目通過現場演繹的方式將典籍中特定的歷史情節展現給受眾,塑造了一個個立體的人物形象,用沉浸式方式演繹了古代文人與當代年輕人的對話,營造出“故事講述場”。而節目中,主持人也改以往的形象,以當代讀書人的角色參與故事創作。比如,在《典籍里的中國》“天問”一期中,主創人員呈現了屈原穿越到當下,目睹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發射成功的震撼場景。舞臺上,主人公屈原面對此情此景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反復吟誦著自己的詩詞。這樣的故事化敘述,簡化了敘述結構,將觀眾帶入故事,不僅展現出傳統文化與時代的碰撞,讓晦澀難懂的書籍“走下神壇”,也讓更多年輕群體在收獲知識的同時產生共情。
(三)技術加持:數字技術下的形式創新
新一代年輕群體更樂于在網絡中學習知識,而以傳統文化為內核的綜藝節目為了取得“Z世代”群體的關注,也積極進行轉型,運用新技術實現節目形式的轉變。在節目播出中可以看出,節目組將傳統文化與視覺特效、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結合起來,通過智能技術以及實時跟蹤、環幕投屏等,使演員的表演和虛擬視效融為一體,帶領觀眾“穿越時空”。在《典籍里的中國》第一期“伏生”中,節目組利用“時空隧道”將撒貝寧、伏生、大禹這三個不同時代的人物組合在同一時空,配合著舞臺特效,呈現出古今對話的穿越效果。
媒體融合是媒介發展的必然趨勢,《典籍里的中國》依托中央電視臺媒體矩陣不斷拓展節目形態,在電視、抖音短視頻、嗶哩嘩哩網站、微博短視頻等平臺不斷拓展傳播,傳播方式更為立體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節目通過創新形式精準滿足年輕群體對于傳統文化表達的需求,實現了傳統文化的“年輕化”傳播。
三、文化類綜藝節目的圈層突破路徑
(一)渠道入圈:節目傳播多屏共振
曾經在電視陪伴下長大的這一代人,打開電視的頻率逐步降低,如今,他們更多活躍在抖音、嗶哩嘩哩網站、微博等新媒體平臺。而這些新媒體平臺的出現,也使得中央電視臺精心打造的視頻節目資源,經過重新包裝在新媒體端以碎片化的形式輸出。但僅止于此,還不足以吸引“Z世代”的目光。經過長時間的摸索,中央電視臺逐漸形成了文化類綜藝節目的傳播矩陣,從《典籍里的中國》開播第一期起,節目便拓展傳播形態,在抖音、嗶哩嘩哩網站、微博視頻等平臺創建視頻賬號,發布衍生視頻,節目僅播出四期便收獲全網近90條熱搜,視頻播放量超5億,且在媒體矩陣平臺中也有節目精彩片段的剪輯。在嘩哩嘩哩網站中,由央視網“快看”發布的《〈典籍里的中國〉戲骨爆棚演技大賞》獲得22.7萬的播放量。而嘩哩嘩哩網站又被稱為“Z世代”樂園,其用戶多為“00后”,約占用戶總數的80%,通過對節目精彩視頻片段的發布以及感興趣的受眾評論的轉發,也側面體現“Z世代”群體對于傳統文化的喜愛態度。《典籍里的中國》通過將節目精彩瞬間剪輯發布到各個新媒體平臺上,通過將有品質的優質內容轉變形態輸送到手機媒體,貼合熟悉碎片化視頻的“Z世代”群體的“接收頻率”,吸引年輕群體觀看完整節目。借此,優質內容滲透到年輕圈層中去,形成熱度并頻繁登上熱搜,也為節目打造了優質口碑,真正實現從渠道出發,大屏與小屏高頻互動、疊加刷屏的傳播效果。這也是節目取得傳播效果最大化的必經之路。
(二)內容呈現:形式與敘事的時尚表達
優質的主流電視文化作品可以對大眾進行思想引導和文化引領。《典籍里的中國》的創作初衷是“用好敘事故事,講好故事敘事”,當好“領讀人和伴讀者”。節目對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進行改編敘事,同樣也是對主流文化的全新探索,從而讓大眾了解典籍、親近典籍。而技術的發展讓“Z世代”群體形成以娛樂消遣為主導的觀看習慣,要想得到這一群體的關注,關鍵要看故事內容本身是否有趣。因而,在這個內容為王的時代,唯有在傳播形式與敘事內容上進行年輕態的融合創新。
筆者認為,《典籍里的中國》節目可為創新文化類節目發展提供借鑒,一是通過“穿越”情景,將歷史搬上了熒幕,一改以往演播室訪談、說教的形式,增加影視戲劇的創新形式,形成“影視化+訪談”的全新形式,受眾可享受節目帶來的沉浸式視聽盛宴。二是將傳統文化與科技結合,將先進、前衛的環幕投屏、虛擬現實技術巧妙結合,展現一本書的撰寫和流傳過程,形成了震撼的文化傳播圖景。如“天工開物”一期,明代科學家宋應星與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實現了跨越300多年的相遇;伏生講述自己一生守護《尚書》的故事;屈原穿越到當下目睹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升空。節目不僅把一部部典籍的故事生動還原,更將其完美呈現在廣大受眾(尤其是年輕群體)眼前。
中央電視臺的主流文化與“Z世代”群體喜愛的亞文化有所不同,但節目組力求尋找兩者的共同點,跨過文化屏障去打造兩者的文化認同,精準找到不同群體的共振點,為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打開新思路。
(三)價值表達:創新與傳承的交相輝映
互聯網發展至今,電視節目制作者普遍認為文化類節目“過于老套”,不受年輕人的喜愛。而中央電視臺《典籍里的中國》開播后的播放量證明了“Z世代”不是不喜歡傳統文化節目,而是不喜歡看“說教式”的文化節目。通過一檔文化節目去說教,或追求流量明星帶熱度吸引“Z世代”年輕群體的注意力,只會適得其反。《典籍里的中國》采用故事先行的手法,將晦澀的古籍生動化,讓“Z世代”群體沉浸其中,對古籍文學產生興趣。《典籍里的中國》之所以在播出后迅速走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創新的節目理念和文化傳承進行了融合。
除了節目的精彩影視演繹,令大眾在觀看后第一時間感同身受外,節目在資料收集方面也同樣下足功夫。《典籍里的中國》每期都會邀請與典籍有關的資深讀者或專家,與觀眾一同進行古籍的品讀,其理念在于從專業視角進行文化價值宣傳,保證節目的專業性。通過演員和專業人士對古籍知識的解讀傳達節目的內涵,對于年輕群體反而更有直達人心的教化效果。節目中,宋應星與袁隆平通過一粒種子找到屬于科學家“求真務實,造福人民”的共同夢想,充分詮釋了科學精神。以《本草綱目》為切入點,聚焦中華醫學古籍,增進受眾對中國醫學的認同感。通過文藝作品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對大眾(尤其是“Z世代”群體)進行隱性教育,在守正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實現文化價值與娛樂價值的有機融合,也更好地引導“Z世代”年輕群體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傳承。
四、結語
《典籍里的中國》播出后在國內迅速突破圈層傳播,這離不開其創新表達和精神內核。社交媒體時代,圈層之間的去中心化明顯,文化類節目的制作者應借助年輕群體的文化話語特點,結合主流傳統文化,改變節目內容敘述形式,通過新媒體平臺實現大屏與小屏共振,將優質內容滲透到年輕群體的圈層中。同時也要避免同質化、泛娛樂化的傾向。年輕群體被優質文藝作品故事吸引,內心獲得滿足感,從而樂意將文化產品傳播出去。節目便可利用好口碑實現圈層之間的互動,更好地實現傳統文化在“Z世代”背景下的圈層突破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