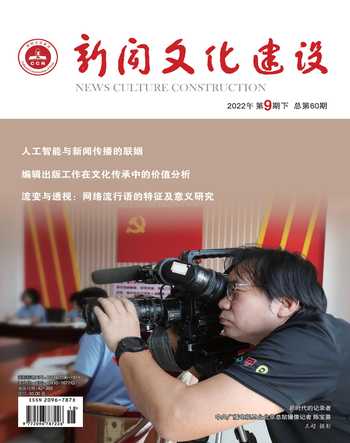新媒體環境下的粉絲飯圈文化探析
羅秋月
摘要:作為互聯網原住民,新媒體時代的粉絲與偶像之間的共生關系更為密切。借助于發達的社交網絡,傳統媒體時期獨立、分散的粉絲逐漸聚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網絡圈層——飯圈,而基于此圈層產生的文化形態則被稱為“飯圈文化”。飯圈粉絲們借由相同的身份標簽、行為規范、符號形式和群體精神來打造飯圈核心,并在一次次為偶像發聲的群體性活動中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然而,飯圈作為一種自發性的粉絲社群,在與其他網絡群體的互動傳播過程中,存在著群體迷失、輿論綁架、網絡暴力和過度消費等諸多問題。本文通過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法等研究方法,在梳理飯圈文化的概念以及形成原因的基礎之上,指出飯圈文化在傳播過程中造成的亂象,并提供相關的解決路徑和思考,以期為后續飯圈文化的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粉絲文化;飯圈文化;群體認同;消費主義
在新媒體時代的網絡賦權下,傳統媒體時代的“偶像文化”在今天大行其道。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Z世代的崛起,新生代粉絲群體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聚集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并逐漸分野出專屬于自己偶像的圈層文化。作為亞文化圈層的典型代表,“飯圈文化”伴隨著偶像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近年來,國內娛樂選秀綜藝和文藝影視劇日益繁盛,為文化工業輸送大波流量明星的同時,也讓人們注意到了偶像背后強大的粉絲群體,飯圈以及飯圈文化逐漸走入主流文化的視野,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一、粉絲和飯圈
粉絲,即英文“Fans”的音譯,最早見于19世紀,形容那些瘋狂仰慕和迷戀影視明星或運動明星的人。[1]隨著大眾偶像文化的發展和普及,現在一般認為粉絲指的是因崇拜或追捧某一名人明星或某一文化現象而自發聚集起來形成的群體,而由不同粉絲群體組成的社群或圈子則稱為“飯圈”或“粉絲圈”,飯圈脫胎于粉絲對偶像的追逐行為。傳統媒體時代,粉絲追逐偶像的方式往往是分散和獨立的,粉絲之間缺乏聯絡和組織,圈層較難形成。而在社會化媒體時代,各種線上交互通道被打通,借助互聯網傳播的便利,粉絲很容易在微博、貼吧、豆瓣、B站(嗶哩嗶哩彈幕視頻網)、抖音等平臺上尋找到彼此。粉絲們聚集在一起,組建各種粉絲群、應援站為自己的偶像搖旗吶喊,這些有組織的群體就是我們所稱的“飯圈”。飯圈具有較強的群體性和邊界化特征,飯圈粉絲成員數量通常較為龐大,群體間具有較強的自發性和號召力。伴隨著偶像文化工業的發展壯大,飯圈逐漸呈現出組織化和產業化的特征,飯圈的“圈”也暗示了互聯網絡時代圈層化的傳播范式。粉絲們從自發的興趣聚集到飯圈內部組織分工的細化,既是媒介技術賦予的社群組織力量,也是互聯網語境下數字原住民對群體認同的渴望。從粉絲到飯圈的演變,其背后也是媒介技術形式的演變,以新媒體作為追星媒介的粉絲相比于傳統大眾媒體時代的粉絲,具有更強的互動性和黏性。
二、飯圈文化興起的原因
人類學家克魯柯亨認為,一種文化,指的是某個人類群體獨特的生活方式和他們整套的生存式樣。[2]而飯圈文化,則是由粉絲群體延伸出來的追星文化,這種文化興起的基礎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水平和精神需求的反映,而飯圈文化的興起則得益于媒介技術的演進、傳媒受眾的心理以及粉絲群體的認同。
(一)社會化媒體平臺賦權
飯圈文化的發展,得益于社會化媒體平臺帶來的自由參與權和平等話語權。自發、平等、廣泛的社會化媒體改變了傳統媒體時期粉絲的追星方式和行為,以往松散的粉絲聯盟在社交媒體平臺的助推下形成了組織化、規模化、效率化的粉絲圈,飯圈文化得以蓬勃發展。以微博為例,作為國內體量最大的社會化媒體平臺之一,微博上有大量偶像明星入駐,是粉絲追星的重要平臺。在微博上,偶像們通過發布關于個人心情、工作行程、生活近況的博文,來維系自己與粉絲的關系,而粉絲則通過微博評論和私信留言等形式與偶像進行實時互動。微博零門檻、低成本的特性幫助粉絲們隨時隨地地獲取關于偶像的資訊,這讓以往松散的粉絲群體找到了聚集地,實現了偶像、粉絲與廣告方、品牌方的聯通,助推了飯圈文化的形成。在微博飯圈,粉絲為偶像打榜、控評、反黑、刷流量、刷數據成為常態,這不僅維系了粉絲與偶像的雙向互動關系,實現了粉絲幻想與偶像同在的參與感,還為粉絲與粉絲之間的多維互動提供了平臺,鞏固了飯圈成員之間的情感基礎。
(二)粉絲的自我投射心理
伴隨著Z世代消費群體的崛起并逐漸參與到偶像文化工業中,當下飯圈中的粉絲群體普遍呈現出低齡化和女性化的特征,年輕的粉絲群體更傾向于將自己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投射到偶像身上。一方面,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Z世代從小就享受著數字媒體和智能手機帶來的網絡便捷,他們的個體喜好、心理特征以及情感寄托等都受到網絡社會的影響,網絡成為他們滿足內在情感和青春期的情緒發泄窗口。娛樂圈的偶像造夢工廠巧妙地抓住這一市場需求,通過打造養成系偶像,讓粉絲參與偶像的成長,甚至號召粉絲為自己的偶像打榜、投票,以此來決定偶像未來的發展路徑,這不僅給予了粉絲見證偶像從璞玉到雕琢成才的全過程,還賦予了粉絲一種類似于“手足情”的虛擬而又真實的在場感和陪伴感,拉近了粉絲與偶像的距離,加強了粉絲對偶像的想象性認同;另一方面,對大部分飯圈粉絲而言,對偶像的崇拜無外乎基于外貌和形象的表層性欣賞,以及基于才華和性格的內在化欣賞。粉絲追逐偶像,不僅將偶像的外貌、性格、才華等美好品質進行自我投射和認同,作為個體對塑造理想自我的榜樣參照,還將個人的情感和心靈寄托于偶像,甚至將其視為疲憊生活的精神支柱,從偶像身上汲取勇氣和信念。因此,當飯圈粉絲在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為偶像的聲譽和前途奔走時,已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追星行為,而被內化投射成對美好自我的追逐。不過,粉絲追逐的并非真實偶像本人,而是真實與幻想相結合的偶像人設,或是文化工業上的藝術品和消費品。
(三)飯圈的群體身份認同
以移動互聯網為平臺,通過相似的興趣愛好相互聯結,緊密聯系并頻繁互動的網絡群體可以稱為網絡趣緣群體。飯圈作為一種以追逐偶像為核心的趣緣群體,依靠群體認同建立了各種群體規范,具有一定的規模性和穩定性。一方面,粉絲社群內部通過使用帶有偶像標識的ID、頭像、簽名等文本符號,能夠幫助飯圈成員快速辨識出同類,消解個體之間的差異,實現自我身份的建構和群體的認同;另一方面,相較于粉絲與偶像之間的直接交互,粉絲與粉絲之間的情感交互是一種更為有效的交流。飯圈成員之間圍繞偶像與飯圈等話題展開實時溝通,不僅可以鞏固粉絲對偶像的喜愛,還能抒發個人情感,化解內心孤獨,在交流中獲得群體的認可和支持,強化飯圈粉絲的身份。然而,社群內部的交流對于飯圈粉絲而言還遠遠不夠,他們除了關注偶像和飯圈,還會對偶像代言的品牌、參演的作品、合作的藝人、宣發的媒體等偶像相關信息進行關注,并隨時向他人進行分享,或者就此信息進行二次創作。飯圈內粉絲的人際交往和社交動態越活躍,就越能增進與飯圈成員的情感,強化自己的飯圈身份,獲得群體成員的認同。
三、淺析飯圈傳播亂象
(一)飯圈粉絲的群體迷失
傳統媒體時代,粉絲追星大多是自發式的個體行為,粉絲可以自主選擇支持偶像的方式和途徑,較少受到他人的影響。而社會化媒體時代的粉絲借由網絡進入社群,展開群體生活,受到飯圈文化和粉絲群體主流意見的影響,容易迷失自我,進而產生從眾等群體失控行為。一方面,由于偶像娛樂行業的特性以及大量消費資本的入駐,一些養成類、選秀類節目刻意引導粉絲以消費的形式為偶像打投,將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相捆綁,再加上飯圈對偶像打投行為的一貫吹捧和贊揚,身處飯圈的粉絲為了維系自身與飯圈的情感聯系,不得不付出時間和金錢成本;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偶像的形象和口碑,飯圈還會鼓吹粉絲與其他網絡圈層的群體展開互動,甚至是辯論或爭吵,這讓粉絲以往簡單快樂的追星行為變得沉重而負累,長此以往,粉絲也易對飯圈滋生不滿情緒,群體認同感日益消耗殆盡。此外,飯圈中的粉絲長期聽從飯圈意見領袖和主流粉絲群體的意見,容易喪失自我意識,甚至打著愛的旗號對偶像的違法失范行為進行無底線縱容,不利于青少年粉絲樹立正確的“三觀”。
(二)飯圈極化現象頻發
“飯圈極化”一詞衍生于“群體極化”,其是指群體決策中的一種極端化傾向,群體中的個人更易提出或做出極端化的想法或舉動。在同質性較高的飯圈中,原本孤立的粉絲連接在一起,個體的想法和特征會被群體中的主導思想所淹沒、取代。個體粉絲進入飯圈后,受到群體極化的影響,逐漸呈現出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征。飯圈粉絲出于對自家偶像的維護,經常會對與偶像相關的輿論進行監控和引導,但群體對輿論的把控較難掌握尺度,一旦失控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真實的輿論走向,還會擠壓其他公眾的話語表達空間。近年來,隨著飯圈的組織化和規模化發展,飯圈粉絲操控輿論,進行輿論綁架的現象也愈發嚴重,面對網友對偶像的負面評價往往采用勸刪、回懟、辱罵、舉報等做法。當罵戰爆發,粉絲在飯圈的強烈認同感召下,個體受到群體感染和情緒鼓動,極易做出一些反常甚至極端的行為。飯圈粉絲的群體極化現象,不僅阻礙了粉絲個體對理性思考和行為的追求,還剝奪了普通網友的話語權,污染了網絡輿論空間。
(三)過度推崇消費主義
大眾娛樂文化工業的繁榮,在為市場輸送大量偶像明星的同時,也掀起了一波新的消費浪潮。娛樂工業和消費資本看到了Z世代粉絲群體為偶像打投的義無反顧,利用他們對偶像的喜愛和支持,引導其進行消費,而粉絲群體的聚合和飯圈文化的盛行則推動了這種消費主義的狂歡化。粉絲社群以愛之名鼓吹對偶像進行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受到鼓動的粉絲消費逐漸脫離個人需求和商品使用價值,基于偶像符號的意義進行消費,而這種消費行為通常具有超常性和成癮性。在極力推崇“愛他就要為他花錢”的飯圈,直接將金錢作為衡量粉絲對偶像的支持程度的重要參考,身處飯圈的粉絲受到群體壓力,以及自身的從眾心理或攀比心理的影響,極易產生超出自身消費能力的購買行為,一些缺乏自我控制的粉絲在重重誘惑之下,不僅透支了金錢資本,最終還透支了對偶像的情緒資本。
四、飯圈文化的反思
隨著移動互聯網絡的發展和偶像文化工業的成熟,飯圈文化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飯圈文化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應,從個體層面上來講,偶像在大眾傳媒上呈現的完美形象,能夠給予粉絲以正面引導,飯圈粉絲為偶像進行的應援行為如修圖、剪視頻等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個體技能。從社會層面上來講,飯圈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亞文化現象,具有強大的文化創造力和感染力。隨著數字媒介技術和傳播平臺的發展,飯圈還不斷突破原有的堅固圈層,參與到政治、文化和社會活動中,尤其是在與“中國經驗”“大國崛起”等國際傳播相關的話題中,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日益緊密,飯圈文化也呈現出主流化的傾向。飯圈中年輕化的表達話語不僅更能引起年輕受眾的共鳴,還能豐富互聯網生態內容,為新時代社會信息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思路。飯圈文化的形成,本質上是傳統粉絲文化在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化媒體的加持下產生的一種新興的粉絲自發性的追星行為和現象,但由于缺乏約束和引導,飯圈在外部資本的消費裹挾和內部趨同極化的影響下,逐漸出現了瘋狂甚至畸形的發展傾向,不僅對網絡社會風氣和大眾造成影響,還會使飯圈這一粉絲社群逐漸被異化和污名化,而飯圈粉絲也會遭受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損耗。
粉絲自身需正確看待追星這一行為,把握好度,學會在不影響正常生活的情況下理智追星,不過度沉迷,保持與偶像的良性發展。粉絲應提升自身媒介素養,客觀理性地看待外界對于偶像的評價,控制個人言行和情緒,虛心地接受合理意見,共同維護健康、有序的網絡秩序。粉絲應理性看待飯圈中的群體行為,遠離從眾、攀比、極端等群體極化行為。針對飯圈盛行的規模化、模板化的控評反黑或刷屏式的追捧行為,應當認清過度的輿論操控行為不僅會掩蓋真實的輿論走向和網友評價,阻礙有效信息的獲取,還會招致路人網友對偶像和飯圈的反感情緒。面對與偶像相關的廣告代言、宣傳促銷和集資打投等行為,粉絲應從個體的實際需求和消費實力出發,合理、適度地支持偶像,切勿因外界鼓吹或攀比心理進行過度消費,警惕被消費主義裹挾和操縱。
五、結語
隨著粉絲規模的擴張和影響力的與日俱增,飯圈這一小眾圈層逐漸走進大眾視野,飯圈文化作為亞文化和社交媒體相碰撞出的產物,極具參與感、凝聚感、互動性等優點,但也存在著失控和無序的一面。在互聯網上,飯圈內部推崇的打榜、控評、刷數據等偶像支持行為可謂是數見不鮮,一些非理性粉絲拋開偶像實力和作品,唯流量獨大的網絡鼓吹更是為眾多網友所詬病。新媒體環境下的飯圈文化既具有價值意義,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如何正確引導飯圈粉絲理智追星,發揮飯圈的群體組織力量,維護健康有序的網絡秩序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參考文獻:
[1] [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的偷獵者[M].鄭熙青,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2] 莊錫昌,顧曉明.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