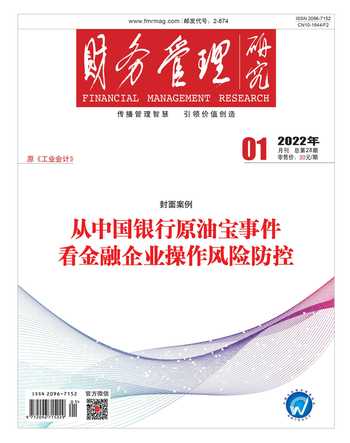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的稅務處理
摘要:網絡直播行業在發展過程中涌現了許多新模式,梳理網絡直播發展脈絡,厘定網絡直播的范圍,是進行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稅務處理的先決條件。在此基礎上,針對目前網絡直播稅務處理中存在的問題,厘定網絡直播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界定網絡直播收入性質,并結合優化稅收營商環境、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大背景,提出網絡直播的稅務處理方案,確定合理的稅目,從而減輕主播的稅負,促進新興業態的發展。
關鍵詞: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稅目;稿酬所得;稅務處理
0 引言
2016年以來,網絡直播快速發展,網絡主播收入不斷增加,偷稅問題也愈加嚴重。2021年11月22日,網絡主播雪梨因偷逃稅款,被依法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9 322萬元。2021年12月20日,網絡主播薇婭偷逃稅被追繳并處罰金共計13.14億元。目前,網絡主播偷逃稅款數額之大、范圍之廣已到駭人聽聞的程度。為解決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征管問題,亟須立足目前網絡直播的特點,確定針對性的稅務處理原則和具體的稅目,明確代扣代繳義務人,使網絡直播的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征管走向正軌。
1 網絡直播的分類與征稅原則的適用
1.1 網絡直播發展現狀
網絡直播發展迅猛,短短10年間,實現了從語音到視頻的躍遷、從單一到多元的轉型[1]。截至2020年,我國網絡直播用戶的數量突破5億,行業營業收入規模暴增至668.5億元。
但在直播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情況不容樂觀。網絡直播高速發展下,相關制度未跟上時代的步伐,網絡直播多方主體之間法律關系性質界定不明、網絡直播收入的經濟性質模糊、未確定明確的代扣代繳義務人等問題的出現,導致在稅務處理上各地差異明顯,同類交易事項適用尺度不同、稅目認定差異較大。面對網絡直播中的稅收現狀,必須從稅務處理方面對網絡直播收入進行管理,明確直播收入稅目稅率,確定具體的納稅主體。
1.2 網絡直播稅務處理原則
網絡直播發展態勢迅猛,應對主播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進行嚴格管理,但是也不能單純課以重稅,阻礙其發展,應遵循嚴格征稅與包容審慎相結合的原則。
當前網絡直播納稅狀況不容樂觀,必須嚴格加以管理,明確納稅主體,確定適用的稅目,確保稅收不流失。同時,要結合我國目前的政策背景,確定最貼切的征收方式。2020年,我國開始施行《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明確指出要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對新業態、新模式采取包容審慎的態度。2020年6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優化稅務執法方式嚴禁征收“過頭稅費”的通知》,明確指出支持互聯網新業態的發展,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都體現了包容審慎原則的要求。
包容審慎原則的適用在經濟法領域已經不是一個新的命題,但是如何針對網絡直播的稅收征收與監管進行適用仍需仔細考量。一方面,由于前期對網絡直播行業稅收征管過度包容,導致偷漏稅現象極其嚴重;另一方面,對網絡直播稅收亂象又不能單純課以重稅,在稅目認定上必須考慮網絡主播的納稅負擔。故包容審慎原則的內涵應該解讀為:嚴守法律的底線,對目前法律中存在的漏洞予以彌補,但在出臺相關規定時,需要秉承寬容與發展的心態,采用鼓勵、引導的方式,為新業態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具體到網絡直播的稅收征管領域,包容審慎原則應體現為:堅持安全底線,打擊違法行為,完善網絡直播稅收征管相關法律規定,確定明確的稅目、稅率、扣繳義務人等。但是在確定適用稅率之前,必須經過周密且慎重的考慮,適用貼合網絡直播收入性質的稅目,確保在規范網絡直播稅收征管的基礎上,不加重主播的稅收負擔,促進網絡直播行業的正常發展。
2 網絡直播法律關系性質界定
要想對網絡直播收入的經濟性質予以厘定,必須先確定網絡直播中的法律關系主體,并對其法律性質進行界定,為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的稅務處理提供基礎。
2.1 網絡直播相關法律主體
在網絡直播過程中一般有4個主體參與其中,包括網絡直播平臺、網絡主播、直播公會、消費者。
2.1.1 網絡直播平臺
網絡直播平臺為主播提供展示自我的窗口。網絡直播平臺有不同的直播分區,大體上包括游戲區、秀場區、生活區等,為主播提供直播的土壤。同時直播平臺還對網絡直播的直播內容進行監督管理,承擔維護良好直播風氣的重任。
2.1.2 網絡主播
網絡主播是網絡直播內容的供給方。對直播有興趣的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在網絡直播平臺上注冊,成為一名主播。網絡主播門檻較低,注冊簡單,受眾較廣,成為現在年輕人選擇的職業方向之一。截至2019年,我國網絡主播人數已突破250萬。
2.1.3 直播公會
直播公會本質上是MCN(Multi-Channel Network,多頻道網絡)機構的一種表現形式。MCN機構建立在新的經濟運作模式基礎上,上游引進原創生產者的內容,下游對接網絡平臺進行變現,憑借機構的營銷、包裝、推廣等一系列運作,最終實現三方利益的共贏。
直播公會就是MCN機構在網絡直播中的表現形式,是介于主播與直播平臺二者之間的中介機構,其實質類似于傳統的經紀公司[2]。MCN機構向直播平臺申請以“公會”的形式入駐,便成為直播公會。直播公會是網絡直播三方主體的中介,一方面與直播平臺簽訂入駐協議,成為平臺入駐公會,獲得對主播的管理權限;另一方面與平臺主播簽訂合作協議,扶持主播,幫助主播獲取流量。
2.1.4 消費者
消費者是網絡直播的資源需求方,是網絡直播收入的最重要來源。消費者不參與直播平臺與主播、公會之間的法律關系,只是作為直播資源的獲取方存在。消費者的打賞是主播收入的最重要來源,打賞的收入在平臺、公會、主播三者之間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從而促進直播的發展。
2.2 網絡直播法律關系性質界定
主播與網絡直播平臺或直播公會關系多樣,三者之間存在多種法律關系性質。
2.2.1 簽約主播
部分主播會與網絡平臺簽訂勞動協議,成為平臺的簽約主播。簽訂協議后,網絡主播會按照平臺的要求,進行協議規定時長的直播,遵循平臺的規則制度,聽從平臺的安排;平臺為主播每月提供工資薪金報酬;網絡主播獲取的打賞收入與平臺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簽約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存在明顯的人身依附性和經濟從屬性,二者之間的關系為勞動關系。
在簽約主播模式下,主播的收入來源大致為工資收入與打賞收入等。作為平臺的簽約主播,與其他未簽約的主播存在明顯的區別:簽約主播有固定的工資,但在打賞分成上比獨立主播更嚴格。
2.2.2 公會主播
一些主播由于初入行業或熱度較小,會選擇與直播公會簽訂協議,接受公會的個性化培養。公會主播與直播公會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目前沒有明確的規定,應按照主播在工作過程中對公會的人身依附性大小決定。
從公會主播的工作內容上看,公會主播與直播公會之間沒有明顯的人格與經濟上的從屬性。首先,公會主播工作內容與時間由自己決定,具有明顯的人身獨立性;其次,直播公會并不會對公會主播每月支付工資報酬,主播的收入來自消費者,主播與公會沒有明顯的經濟從屬性,故二者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公會主播直播自由,二者之間身份獨立,公會幫助主播營造熱度,主播的打賞與公會進行分成,二者之間應該構成勞務關系。
在公會主播模式下,主播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打賞、廣告等。由于公會為主播營造熱度,所以在打賞分成上,主播的打賞收入在經過直播平臺的扣除后,還要與公會進行分配。
2.2.3 獨立主播
在這種模式下,主播與平臺簽訂分成協議,由主播自由安排直播時間、內容、方式等,主播除了遵循國家法律和平臺規則,不受平臺的管控。直播平臺為獨立主播提供基本的條件,主播的打賞收入與直播平臺按比例分配,雙方互相配合,各取所得,是一種合作關系。
在獨立主播模式下,主播的收入來源主要為打賞、廣告等收入。
綜上所述,根據三方主體簽訂合同內容的不同,形成3種不同的法律關系性質。其中,第一種簽約主播的法律關系性質最為明確,為勞動關系,適用法律也爭議不大。第二種和第三種的法律關系性質為非勞動關系,學界對其定性的爭議較大,在確定納稅主體、適用具體稅目和稅率上沒有統一意見。
3 網絡主播收入的經濟實質分析
網絡直播融合性強,行業業態多樣,目前我國對網絡直播的收入性質沒有做出明確規定[3]。所以在明確了不同網絡主播的法律關系性質之后,緊接著需要對收入的經濟實質進行分析,以確定其適用的稅目與稅率。2019年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以后,我國進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收時代[4]。新規之下,網絡主播的收入該如何適用,是目前必須解決的問題。在3類網絡直播法律關系中,第一類勞動關系主播,即簽約主播,其收入性質較明確,第二類非勞動關系主播,即公會主播,與第三類獨立主播收入性質類似,可合并討論。
3.1 勞動關系主播收入經濟實質分析
簽約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構成勞動關系,簽約主播為平臺的勞動者,為直播平臺成員,從直播平臺領取勞動報酬,故簽約主播的收入應當屬于“工資、薪金所得”。
3.2 非勞動關系主播收入經濟實質分析
公會主播與獨立主播的收入來源基本一致,主要為打賞、廣告、分成等,二者經濟實質類似。而在該類收入的定性上,學界爭議較大,觀點較多。
3.2.1 無償贈予觀點
無償贈予是贈予人主動將自己的財物讓渡給特定的對象的行為。網絡直播的收入具有無償贈予的外觀特征;消費者首先購買虛擬貨幣,換取虛擬禮物贈予主播,在此過程中,消費者不求回報,只按照自己的意愿無償地贈予主播,符合無償贈予的特點。
3.2.2 勞務報酬觀點
勞務報酬是指行為人憑借自己的特長,向特定的對象提供演出、講授、特定服務等勞務活動,從而取得的收入。相較于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的特點在于獲取方式的不同,勞務報酬不是以穩定的月薪發放,而是以間斷的、有差異的方式獲取。非勞動關系的網絡主播與平臺關系松散,憑借提供直播演出的方式獲取打賞或廣告分成,符合勞務報酬所得的特征。
3.2.3 稿酬所得觀點
稿酬所得一般特指作者的作品被發表于雜志、報紙、圖書等載體而獲得的收入。雖然網絡直播與傳統意義上的作品差別較大,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機構與高校認可網絡作品作為科研成果的一個種類,將網絡作品與其他紙質作品地位等同,納入職稱評價體系[5]。一定程度上講,網絡直播作為分享主播特長的渠道,類型多樣,特色鮮明,可以視為作品予以認定,從而適用稿酬所得進行納稅。
3.2.4 偶然所得觀點
偶然所得是個人通過意外途徑獲取的收入,如彩票、抽獎活動等。網絡直播的打賞具有明顯的偶然性,消費者的打賞沒有明確時間,大多數處于一時興起,隨機性比較強,因此,此類收入具備一定的偶然所得特點。
3.2.5 本文觀點
對網絡直播收入的認定必須透過其形式特征,把握其內在特性。同時也必須結合我國優化營商環境、大規模減稅降費、大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大背景,對直播收入有針對性地進行認定,以確定具體的稅目稅率,同時不至于加重主播的稅負。
第一,主播收入不應被認定為無償贈予。雖然在形式上直播打賞收入很像消費者對主播的贈予,但打賞都是基于主播的直播內容,消費者在主播的直播過程中獲得了心理上、視覺上或知識上的滿足,可以將打賞作為一種消費,而非無償的贈予。
第二,主播收入不應被認定為偶然所得。雖然消費者對主播的打賞沒有固定的時間、數額,但是一般都具有明顯的目的性,與彩票、抽獎等偶然事件差別較大。一方面,消費者在長期觀看直播的過程中對主播個人直播風格了解,成為主播的粉絲,打賞是表達對主播的喜愛之情;另一方面,消費者可能是被主播直播過程中的技術、知識等感染,從而愿意付出一定金額的虛擬禮物,真出于偶然的毫無動機的打賞基本上不會出現。
第三,主播收入類似勞務報酬所得,但在認定上應當慎重。非勞動關系的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關系松散,平臺除了對主播直播的基本內容進行審核和監督,不會對主播直播方式、類別、時間進行干涉。主播憑借自己的直播內容,輸出知識、舞蹈、歌唱等勞務活動,獲得收入,符合勞務報酬所得的特點。
第四,堅持嚴格征稅與包容審慎相結合為指導原則,綜合我國經濟政策背景,主播的收入應當被認定為稿酬所得。網絡直播內容雖然與傳統意義上的書稿、文稿等作品不同,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應當對網絡作品的正當性予以認定。網絡直播的視頻內容匯集了教育知識、搞笑綜藝、歌舞才藝、生活實況等不同分類,內容眾多,流傳度高,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興起的一類重要作品形式。隨著越來越多的高校與機構對網絡作品的正當性予以認可,將網絡直播收入認定為稿酬所得亦無不可。最重要的是,對網絡直播收入進行定性必須結合我國時代背景和相關政策,選擇最適當的征稅方式。2021年3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明確指出,對新業態、新模式要堅持鼓勵創新、包容審慎的原則。結合我國近年反復強調的優化營商環境、堅持減稅降費的舉措,對網絡直播行業一方面必須嚴格征稅,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包容審慎的原則。在明確網絡直播收入稅目稅率的基礎上,亦不應當給主播較大的稅負。根據新《個人所得稅法》,稿酬所得在減除20%的費用后,還要減按70%計算。認定直播收入為稿酬所得,是包容審慎原則的內在體現,符合我國政策要求,有利于減輕主播稅負,給予其一定的稅率優惠,可激發直播行業的活力。
4 網絡直播收入的稅務處理
在明確了網絡直播三方主體的法律關系性質,界定了網絡主播收入的經濟性質之后,網絡直播的收入稅務處理方式也就較為清晰。
4.1 確定納稅主體
在網絡直播關系的三方主體中,網絡直播平臺、網絡主播、直播公會都從直播過程中獲得收入,三者都是納稅主體。具體由哪一方主體繳納稅款,直播平臺或公會是否負有代扣代繳義務,需要分類加以說明。
第一,簽約主播的個人所得稅應當由網絡直播平臺代扣代繳。簽約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為勞動關系,收入性質為工資、薪金所得,網絡直播平臺作為支付網絡主播工資的單位,應當作為代扣代繳義務人。
第二,公會主播的個人所得稅應當由直播公會代扣代繳。公會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法律關系,公會主播由直播公會進行管理與培養,收入由直播公會分配后匯入主播賬戶。從收入的決定權和實際情況考慮,應當由直播公會作為代扣代繳義務人。
第三,獨立主播的個人所得稅應當由網絡直播平臺代扣代繳。新《個人所得稅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個人所得稅以所得人為納稅人,以支付所得的單位或者個人為扣繳義務人。在網絡直播過程中,“支付所得的個人”為消費者,但是由于消費者數量巨大、地點分散,管理難度大,明顯不能作為代扣代繳義務人。所以應當將“支付所得的單位”認定為網絡直播平臺,在支付所得過程中,直播平臺擁有對收入的分配權和控制權。同時,在數字化交易過程中,直播平臺作為打賞收入數據的直接擁有者,掌握完善的主播涉稅信息,將網絡直播平臺作為代扣代繳義務人更為方便、直接。
4.2 具體稅目與稅率的適用
第一,簽約主播適用“工資、薪金所得”,按照綜合所得合并計算其個人所得稅,適用3%~45%的超額累進稅率。
第二,非勞動關系的主播收入基于合理避稅、降低主播稅負、促進新業態發展的原則,適用“稿酬所得”,使網絡直播能在合法的范圍內適用最大的稅收優惠,提升其直播的積極性。
5 結語
面對網絡直播的稅收征管現狀,需立足于原則指導、性質界定、稅務處理的解決思路,層層遞進地進行處理。首先,確立嚴格征稅與包容審慎相結合的指導原則,促進網絡直播行業發展的同時確保稅收不流失;其次,明確網絡直播三方主體的關系,根據網絡直播主體之間的不同關系,分析網絡主播收入的經濟實質;最后,在明確經濟實質的基礎上,結合嚴格征稅與包容審慎相結合的原則,確定具體的稅務處理方案,以期為網絡直播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征管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唐延杰.基于“網絡直播元年”的批判性思考[J].青年記者,2017(14):10-11.
[2]王桂英.網絡主播收入的個稅征管分析[J].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9,32(3):42-47.
[3]蔡昌,馬燕妮,劉萬敏.平臺經濟的稅收治理難點與治理方略[J].財會月刊,2020(21):120-127.
[4]漆亮亮,賴勤學.共建共治共享的稅收治理格局研究:以新時代的個人所得稅改革與治理為例[J].稅務研究,2019(4):19-23.
[5]韓艷.網絡平臺打賞的會稅處理問題探討[J].財會通訊,2021(3):111-114.
收稿日期:2021-10-26
作者簡介:
張曉港,男,1997年生,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經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