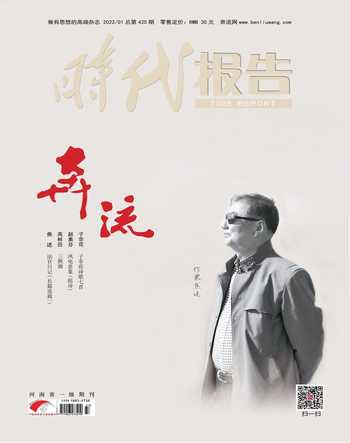黃河情緣
吉項魚 董建芳
這是一個發生在黃河沿岸的真實故事。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一位下放干部心系駐村,為百姓辦好事、辦實事。他用真情回報鄉親的故事,在當地傳為佳話。
五十年過去了,村子里而今已是耄耋老者,嘴里仍念叨著:“王會治,你在哪里…… ”
——題記
一
滾滾黃河,呼嘯著奔騰東流。沿岸水草豐茂,花香鳥語,宛如世外桃源,美不勝收。
在黃河拐彎的地方,有一個美麗的村莊叫大王村。大王村里的人不姓王,大部分人姓史。村里有個叫史狗項的莊稼人,他是大王村第三任大隊長,雖然文化水平不高,長得五大三粗,但是心眼特別好,深得大家尊重。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村里來了一個下放干部,住在大隊部隔壁一個靠崖院的窯洞里。窯洞里環境非常簡陋,一個土炕、一張掉了漆皮且四條腿松動的舊桌子就是全部家當了。
下放干部中等個頭、四方臉、大眼睛,雖其貌不揚,話語不多,但他對人和藹可親,走起路來挺胸抬頭,步履堅定。
下放干部每天同社員一塊兒去地里干農活,挑糞、翻地、收割、打場,樣樣精通。那時候,人們吃的是人民公社集體大食堂,老輩人管這叫“吃食堂飯”。
說起吃食堂飯,大王村楊有賢、史應懷、亢恩祥三位老人就激動得坐不住了。他們漫步在黃河南岸綠油油的麥田里,邊走邊說起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大王村:不是黃水泛濫,就是土地十年九旱,群眾靠天吃飯,糧食總是不能“過關”(不夠吃)。因此,他們不由自主地談到了下放干部王會治,還提到了大隊長史狗項。
作為大隊長的史狗項雖識字不多,但喜歡與通情達理的文化人交流。于是,兩人逐漸走近,很是談得來。那時習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們,與王會治的交流少之又少。快到月底的一天,王會治下工回到窯洞,饑腸轆轆的他拉開抽屜,想找根煙抽,突然發現一個饅頭。王會治好奇地想:“是誰給我的?白天干活都沒有人跟我說啊?難道是誰放錯了地方?算了,先墊墊肚子再說吧。”
第二天,王會治帶著疑問上工了。與此同時,王會治還在為吃飯的事發愁,自己的十幾斤糧票已經吃完。回到家,王會治打開抽屜想翻找看桌子夾縫里是否有散落的一兩二兩糧票,接續住下月的伙食,卻意外發現幾張糧票端端正正放在抽屜中央。“天上掉餡兒餅了?怎么會有這樣的好事?”王會治手捧著糧票,流下了感激的眼淚,真是天助我也!
撿了個寶貝似的王會治難掩心中歡喜,但他不迷信,暗暗留意:“到底是誰給的?”
到了第三天,又有幾個煙卷出現在了抽屜里。王會治心里一驚:“怪了,誰還知道我愛吸煙?”腦子好使的王會治,多了個心眼兒,非要“逮住”這個解他燃眉之急的“神仙”。
上工走到半道,王會治以忘記鎖門為由,返回小院,剛走到門口,他就看見窯洞的門開了,從里面走出來的那個人就是史狗項。
從此,王會治與史狗項的關系更進一步,成了“鐵哥們兒”。王會治時不時為村里建言獻策,史狗項總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1973年,王會治回到了鄭州。走之前的那天夜里,史狗項跟王會治坐在土炕沿上吸著土煙卷兒,一明一暗的煙頭忽閃著微弱的光,透過光,彼此能看見對方的臉。王會治說:“大王村離黃河近,得想辦法把黃河水引到地里來,莊稼才有好收成。”
史狗項猛吸一口煙說:“咋能把水從低處引到高處?”
“想辦法。”王會治語重心長地說,“以后有用得著我的地方,盡管說。”
第二天,天蒙蒙亮,王會治想偷偷地離開村莊,剛走到村口,看到史狗項站在村頭,霧水打濕了史狗項的睫毛,不用說,他已經在這里等了許久。
二
1973年,全國上下興修水利。從省里到縣里,從縣里到村里,上上下下齊動員,引黃灌溉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個道理誰都懂,可是到哪里采購急需物資?大家一籌莫展。
此刻,史狗項想到了王會治,也許他有辦法。于是,史狗項托熟人四處打聽王會治的下落。當聽說王會治還在鄭州,并要來他家地址的時候,史狗項覺得有救了,大王村修水利有救了。
那年頭,村里還沒通電話,人們一般用電報和書信傳送信息。史狗項給王會治寫信,說明村里正在規劃修建抽水站,需要大量的水泥、抽水機等物資,請求王會治幫助解決。
幾天后,史狗項果然收到了王會治的電報,讓史狗項從干店火車站坐慢車,出站后在廣場電線桿下面等著,甚至幾點鐘、幾班次的列車,什么時候到達鄭州火車站,王會治在電報上都說得非常詳細。
一封家書,焐熱了老百姓的心;一個饅頭,拉近了群眾與干部的距離。不用說,王會治沒有變,還是那個不愛多說話,做事有板有眼的他。
對于大老粗史狗項能為大王村購買國家緊缺物資,村里人又驚又喜,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疑慮,最終大隊決定讓史狗項帶上民兵營長翟順義,趕赴鄭州找王會治碰碰運氣。
于是,他們倆背上干糧布袋,踏上了東去的列車。
一路上,“轟隆轟隆”的車輪聲怎么也平復不了史狗項忐忑的心。他害怕萬一事情辦不成,回來怎么見父老鄉親?史狗項沒來得及體驗第一次坐火車的新奇,滿腦子都是抽水機、水管子、水泥以及王會治會不會“放他鴿子”。
到了鄭州火車站,史狗項和翟順義順利找到王會治電報里描述的電線桿。可王會治并不在那里,兩個憨厚的農民背靠背,手同手(一只手塞到另一只袖子里),蹲在地下,四下張望,審視著每一個過往的路人。
眼看天色不早了,史狗項拐回車站,跟火車站的廣播員說:“我是靈寶的,你給我喊‘靈寶老鄉到了,在電線桿下等人來接哦。”
正在開會的王會治并沒有食言,他向司機仔細描述了史狗項的外貌特征,讓他趕快開車到火車站接人。
偌大的火車站,除了兩個農民模樣的老頭靠在電線桿上嘮嗑,再無其他人了,司機開車回了單位。看到沒接到人的司機,王會治心想,史狗項沒趕上火車?于是,就對司機說:“等會兒再去接下一趟車。”
天漸漸黑了下來,電桿下面的路燈依然明亮。已感到饑餓的史狗項和翟順義掏出饅頭啃了起來。這時,司機好奇地打量著他倆:“真逗!在電桿根兒吃上了。”史狗項感覺小青年在譏笑他們,也沒好氣地背過身去。
又跑了一趟的司機還是沒接到人,王會治納悶了:“不會吧?應該到了,我去接。”車子一路飛奔,剛過二七廣場,到達大同路口,王會治一眼就看到遠處電線桿下那個熟悉的身影。王會治急忙下車,上前拉起史狗項粗糙的大手,倆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久別重逢,感情還是那么親切!
司機這時才明白過來,慚愧地低下頭,小聲說:“我以為接的是……卻不知道就是他們,對不起!”
王會治把史狗項和翟順義二人帶到了他的住所,說:“你們在這兒好好歇一歇,狗項,你愛看豫劇,讓司機帶你看戲去。”史狗項哪有心思看戲,他是來給村里辦事的,如果發電機買不到,自己咋給村里人交代?
到了第三天,史狗項怎么也忍不住了。他走到王會治跟前,用懇求的語氣說:“村里急用抽水機,拜托了!我先回去了,家里人著急。我把事兒就交給你了。”有些失望的史狗項,借口趕火車,急忙打開門,王會治只好讓司機把他們倆送到了鄭州火車站。
回到大王村,站在村口的史狗項怎么也抬不起腳來,事情沒辦成,他沒臉見鄉親們。于是躺在麥積垛子根兒,想閉上眼睛安靜一會兒。
突然,翟順義出現在史狗項眼前,史狗項一個趔趄沒站穩,爬起來說:“干啥啊!離我遠點。”
緊跟在翟順義后面的村書記史贊續激動地豎起大拇指說:“你走的第二天,咱們要的抽水機,還有好多物資就到了。狗項,你真厲害,為咱們村立大功了!”
史狗項激動地背過臉哭了起來,他哽咽著說:“王會治他沒變,他是好人,咱們的大恩人!”
有了王會治的幫助,大王村引黃工程南、北兩個抽水站順利建成。甘甜的黃河水灌溉著一眼望不到邊的農田,豐收的喜悅掛在大王及周邊村子每個人的臉上,缺糧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
三
黃河水,黃又黃,黃泥湯澆地糧滿倉。自古以來,黃河水是農民的寶貝。黃河水能讓農民改天換地過上好日子,治理黃河離不開鋼筋水泥來修壩、筑堤。
1974年,退伍回村后的史應懷任大王村會計,懷揣滿腔的抱負要讓社員不但有糧吃,手里還要有錢花。恰逢隊辦工業在靈寶慢慢興起,于是大王村抽調隊長亢戰學、亢林娃、李滿林、史應懷四人搞隊辦工業。目標是購買二手紡紗車,解放婦女勞動力;加工水泥電桿,取代木電桿。沒錢,他們就去信用社貸款。
預制電桿需要的原材料水泥和鋼筋在市場上供不應求。雖然安陽的鋼鐵、洛陽的水泥,再加上東方紅拖拉機,是河南人最時髦、最炫耀的三件東西,但大王村沒有一件能買得起。
村民們再次想到了王會治,想到了史狗項。時任洛陽地委書記的王會治還會幫助他們嗎?村書記和史狗項對視片刻,決定去找王會治試一試,史應懷自告奮勇和史狗項同去。
洛陽地委家屬院的大門口,史狗項怯怯地問門衛:“王書記在嗎?”
“開會去了。”
“啥時候散會?”
“不知道。”
“咱就在這里等,他天黑總要回來吧。”史狗項說。
“王書記,有兩個老鄉找您。”忽然,史狗項和史應懷聽到門衛在打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王會治熟悉的聲音:“他們從哪兒來的?”
“你們從哪兒來,王書記問呢。”門衛手拿電話,朝史狗項喊道。
“靈寶,我們是從靈寶來的。”
“叫他們進來。快點!”
史狗項和史應懷剛進大門沒一會兒,王會治就趕過來了。王會治拉著史狗項的手來到了客廳,遞煙、沖茶、敘舊,然后吩咐做飯。完全沒有當官的架子,只有兄弟般的情誼。
史應懷和史狗項說明了來洛陽的目的。“聽說安陽有個紡紗廠,把他們的舊機器弄來,咋樣?”
“你知道嗎,一臺紡紗機一個小時能吞吐3000斤皮棉。咱大王村有多少棉花?買機器加工紗這不是合適的發展方向,不中。”王會治胸有成竹地說,“你們就搞預制板、電線桿,這樣靠譜。需要鋼筋和水泥,我給你們解決。”
四
從那以后,大王村預制廠的原材料從沒有間斷過。預制廠生產的電線桿和預制板在市場上供不應求。來自焦村、函谷關等鄉鎮的訂單在大王村排成了長隊,集體經濟搞得紅紅火火。
后來,大王村還辦起了磚瓦廠、鉚釘廠、鐵工廠隊辦工業,村里男女勞力都有活干有錢掙。
大王村村民亢恩祥說:“大王村建起的南北兩個抽水站,水澆地一下擴大到2500多畝,是王會治為大王村辦的第一件大好事,解決了糧食緊缺的問題。第二件事,是給我們村批鋼筋和水泥,改變了我們村一窮二白的面貌,村民世代不忘。”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王會治,他做到了。大王村村民們把這個恩人的名字深深地烙在了心里,念念不忘。
如今的黃河灘涂,天鵝高歌,鴻雁列隊,林木蒼翠,百業興旺。沿黃公路像一條蜿蜒的紐帶,把沿線的風景——棗園、杏林、蘋果園和萬畝油葵一個個連接起來,風景獨特,游人如織。春天,白的、黃的、粉的花兒次第開放,養蜂人趕著花兒的芬芳到處流動著、采集著各種各樣的蜜。這些蜜,好似為之付出的人們采集而來的幸福生活一樣,入心入肺,值得一生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