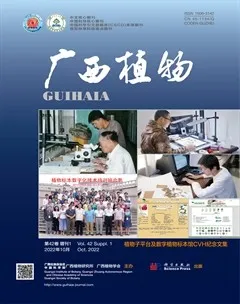植物模式標本數據整合新的機遇與挑戰
謝丹 劉慧圓 覃海寧


摘 要:? 命名模式是分類群名稱永久依附的成分,在分類學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中國復雜的植物采集歷史以及對中國植物標本開展研究的單位各異,導致我國植物模式標本零散分布于全球各大標本館,給分類工作的開展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標本數字化的開展為模式標本數據整合提供了新的機遇,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人名和地名標準化以及模式類型確認等方面的挑戰。我國于2006年開始對模式標本數據進行收集和整理,迄今已完成國內外20余家標本館9萬余條標本數據的收集。模式考證和模式類型清理是我們下一步亟須開展的工作,同時我們應將地名變更資料、人名考證資料進行整合并建立相應的數據庫以推動模式標本數據的標準化。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們摸清中國模式標本的家底。
關鍵詞: 模式標本, 標本館, 采集人, 地名變更, 維管植物
中圖分類號:? Q94-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3142(2022)增刊1-0046-06
收稿日期:? 2021-09-19
基金項目:? 國家植物標本資源庫(E0117G1001); 國家標本資源共享平臺植物子平臺項目(2005DKA21401)。
第一作者: 謝丹(1995-),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植物分類學及生物多樣性相關研究,(E-mail)1925986345@qq.com。
通信作者:? 覃海寧,博士,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生物多樣性信息學研究,(E-mail)hainingqin@ibcas.ac.c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ata
integration of plant type specimens
XIE Dan1,2, LIU Huiyuan1, QIN Haining1,2*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Botany,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Abstract:? A nomenclatural type is the? element to which the name of a taxon is permanently attached and has irreplaceable value in taxonomic research. Types are scattered herbaria across? worldwide,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difficul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xonomy, mainly due to the complex plant collection history and the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lant specimens.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men digitization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ata integration of plant type specimens and also brings some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llector and collection place, and the typification of a specimen. We have begun collecting and sorting the type specimen data since 2006 and about 90 thousand type specimen data in over 20 herbaria worldwide have been collected simultaneously. Type verification and the cleaning up of type status are urgent works that should be carried out next. Meanwhile,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in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ange and collector name that have been verified for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ype specimens. It will help us to updat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type specimens of China.
Key words: type specimen, herbarium, collector, place name change, vascular plant
植物模式標本是指一個分類群名稱發表時所依據的標本,包括主模式(Holotype)、等模式(Isotype)、副模式(Paratype)、合模式(Syntype)、后選模式(Lectotype)、新模式(Neotype)和附加模式(Epitype)等,是物種存在的永久憑證,在保障命名體系穩定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植物分類學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楊永,2012;林祁等,2017;Turland et al., 2018)。它與物種的原始描述均為分類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資料。
中國是全球17個生物多樣性大國之一(Biodiversity, 2014)。區系多樣性居北半球首位(孫航等,2017)。豐富的植物多樣性引起了國家和民眾的高度重視。20世紀60年代,中國開始編撰《中國植物志》,歷時半個世紀,全書全部出版(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1959—2004)。隨后,我國與密蘇里植物園合作編撰了Flora of China,該書在《中國植物志》的基礎上進行增補和修訂,并以英文的形式進行定稿(Wu et al., 1989—2013)。2013年,《中國生物物種名錄(植物卷)》的編研工作啟動,并于2018年完成全書各卷冊的出版,該書主要基于最新的植物分類系統對中國植物名稱、分布和文獻等信息進行整合及年度更新(Xie et al., 2021)。雖然大量植物多樣性家底清查工作已經開展,但物種存在的憑證——模式標本的收集與整理工作仍進展緩慢。這與我國的國情有較大的關系。我國的植物分類學起步較晚(20世紀20年代),較Luca Ghini發明臘葉標本制作晚了三個半世紀,較林奈創立雙名法晚了約一個半世紀(王文采,2011;楊永,2012)。同時,外國學者對我國植物認識和采集較早,外國人對中國植物的認識最早可追溯到13世紀后期,馬可波羅、葡萄牙商人及一些早期的傳教士雖未在中國采集植物標本,但記錄了大量歐洲沒有記載的植物種類,讓西方植物學家對中國植物資源有了初步的印象,致使之后外國植物學家在中國大規模的采集活動。他們在中國采集植物標本始于17世紀,從17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300余年時間里采集植物標本多達121萬余份。這一時期在中國進行植物采集且有記錄的植物學家(包括傳教士、外交官、商人和學者等)有300余位,如英國的Ernest Henry Wilson、Henry Fletcher Hance,愛爾蘭的Augustine Henry,法國的Père Jean Marie Delavay以及奧地利的Heinrich Handel-Mazzetti等(王印政等,2004)。我國植物分類學起步及發展較晚導致大量模式標本保存于國外標本館中。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種類的模式標本由外國人采集并保存于世界各大標本館中(王印政等,2004)。標本數字化工作的開展與網絡共享為模式標本數據的整合提供了新的機遇。
模式標本的數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分類學研究積累的重要反映,數量越多說明該地區的研究越深入,受關注度越高,對分類與區系研究越有利(周友兵等,2017)。但是,我國各地區模式標本的數量仍然不明。近年來已有一些研究者開始著手地區模式標本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如謝丹等(2019)和歐陽學軍等(2019),這些工作的開展將有效地推動模式標本數據的整合與清理。
1 模式標本數字化的興起與發展
數字倉儲(digital repositories)為我們獲得大量標本信息提供了快捷、簡便的方式(Soltis, 2017)。20世紀80年代,植物標本館開始將標本信息整合到內部數據庫中(in-house databases),最終這些數據可以通過萬維網進行訪問(Cantrill, 2018)。澳大利亞是這項工作開展的先行者之一,70年代中期開始了標本館的標本數字化工作(王利松等,2010)。同一時期,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ttingen, GOET)開始建立模式數據庫,數據庫包含模式標本信息8 000余份(Schmull et al., 2005)。這些工作為后期模式標本的網絡共享打下了基礎。2004年非洲植物倡議(African Plants Initiative, API)的提出標志著全球模式標本數字化工作的開始,該項目旨在獲取非洲高質量模式標本照片及相關采集信息。隨著拉丁美洲植物倡議(Latin American Plants Initiative)的實施,倡議得到迅速發展,參加的標本館數量不斷擴增、涉及區域不斷擴大,該項目于2009年演變為全球植物倡議(Global Plants Initiative,GPI)。項目受到Andrew W. Mellon基金會的支持并通過JSTOR(https://plants.jstor.org/)將全球300余家標本館及200余萬份高分辨率的模式標本向科研工作者進行展示,極大地滿足了分類學家對模式標本的需求(https://www.kew.org/ science/projects/global-plants- initiative-gpi; https://about.jstor.org/hats-in-jstor/primary-sources/ global-plants/; Lughadha & Miller, 2009)。我國于2006年啟動植物標本數字化工作,同年開始對模式標本進行收集和整理,迄今已收集了國內10余家主要標本館4萬余條維管植物模式標本數據。同時,我們也對國外標本館已經數字化的中國模式標本數據進行收集,并獲得中國維管植物模式標本數據5萬余條(表1)。
2 國內外主要標本館對中國植物
模式標本的館藏及數字化情況
截至目前,大部分標本館的模式標本數字化工作已基本完成,如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標本館(E)、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P)以及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PE)等。從目前已數字化的模式標本數量來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以22 000份居首位(林祁等,2017),其次為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10 807)、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標本館(10 700)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標本館(A, GH, AMES, FH; 10 139)(表1)。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標本館(K)和東京大學標本館(TI)尚未數字化完全。雖然已數字化的模式標本數量達到了一定的量級,但僅極少部分標本館對模式標本進行了整理。部分標本館在館藏的模式標本上附上了相應的原始文獻信息,如維也納自然歷史博物館(W)、維也納大學標本館(WU)以及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標本館;也有部分標本館對該館的模式標本進行整理并出版了相應的名錄或數據集。例如,Grabovskaya-Borodina (2010) 出版了俄羅斯科學院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標本館(LE)東亞維管植物模式標本名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出版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PE)模式標本集以及方鼎等(2012)出版了廣西中醫藥研究院植物標本館(GXMI)維管植物模式標本照片集等。
3 中國模式標本信息收集與整合
新的機遇和挑戰
標本數字化工作的快速開展和便捷的網絡式訪問為中國模式標本信息的收集與整合提供了新的機遇,有效地改變了模式標本信息難以獲取的局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植物分類學剛剛起步,文獻資料多存于國外,給相關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一批植物分類學家借助在國外學習的機會拍攝模式標本照片。如:秦仁昌1930年在英國邱園標本館利用晚上業余時間,歷時11個月拍攝模式或有價值的標本照片18 000余張;四川大學方文培于20世紀40年代從美國哈佛大學標本館拍回一大批模式,這些照片由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編輯成一套《中國種子植物模式照片集》,成為《中國植物志》編研的重要參考資料(汪振儒等,1994)。雖然現在模式標本信息的獲取較以前更為方便,但同時也給數據的標準化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第一大挑戰是采集地的確定。外國植物學家在中國進行專業性的植物采集最早可追溯至18世紀,期間出現了較多的行政區劃變革,同時在這段采集時間中方言羅馬教會字、威瑪氏音標等廣泛用于人名、地名的注音,這些原因導致地名和人名的復雜多樣化(邢福武,2014)。例如,廣東羅浮山有Loh Fau Mountain、Lofaushan、Luofu Shan等多種寫法,Pakwan和White Cloud Mountain均指代白云山;Langkong指浪穹縣,最初由明朝設置,歸鄧川州管轄,清沿明制,1913年,鄧川州改為鄧川縣,浪穹縣改為洱源縣,1958年洱源縣、鄧川縣與劍川縣合并,稱劍川縣,1961年10月,恢復原劍川縣,同時洱源、鄧川兩縣合并為洱源縣(http://xzqh.org/html/show/yn/19707.html),故標本所記載Langkong應為現在的洱源縣。再如Tchen-kéou-tin,即城口廳,清道光二年(1822)年置,1913年改為城口縣。海南省的行政地名則顯得更為復雜,早期對海南進行植物采集的大多為大陸人,聽不懂海南話和黎話,因而導致所記錄的采集地名多為誤聽海南話或黎話而來的“俗名”,或為與官方所用的地名音調相仿的“別名”,早期的一些植物采集地如定安五指山、瓊海黎母嶺、儋縣鶯歌嶺、定安同甲等與現今縣域的范圍相去甚遠(邢福武,2014)。準確的地理信息在植物分類學研究過程中相當重要,然而年代久遠,地名考證也顯得尤為困難。匯集地名變更資料(Herberm, 1988; 邢福武等,2012),根據行政區域歷史沿革建立新舊地名對應數據庫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地名考證的壓力;同時我們可以追蹤每一位采集家當年的采集路線,從所采植物的生境等野外記錄資料著手,結合當時該區行政區劃與建制的具體情況,把當時的地圖與現今的地圖作比較分析,多番考證后確定其在現今建制中的準確位置(邢福武,2014)。我們應盡可能地將采集地以經緯度的方式進行表示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行政區劃變更。第二大挑戰是采集人的確定。以侯寬昭為例,采集記錄中有F. C. How, How, Foon-Chew, Hou Kuan-zhao等多種記錄形式。Harry Smith則被記錄為Smith, Karl August Harald (Harry), K. A. H. Smith, H. Smith等。此外,有時保存在不同標本館中的同號標本采集人的記錄也會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或記錄為采集隊,或對采集人進行分別組合。這些都給采集人的標準化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針對采集人的標準化,我們首先應統一采集人的記錄方式,采集人最好記錄為英文全稱或中文拼音的形式,并統一為姓前名后,姓名之間以“,”進行分割,采集人多于3人則最好以采集隊的形式進行表述;其次我們可以借助大數據優勢,從同號標本中找出采集人的對應關系。近年來,一些名稱數據庫相繼被建立,如哈佛大學標本館 “Index of Botanists”以及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中國植物名稱作者(命名人)數據庫”,這些資料為人名的檢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第三大挑戰是模式類型的確定。林祁等(2017)對國內外標本館在模式標本數字化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進行了總結,共歸為八大類。其中,類型5“標注為Typus,但并未指定為何種模式類型”和類型8“原始文獻記錄的標本信息與標本上的采集信息不一致”較為常見。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查閱物種發表的原始文獻并結合法規定義對這些模式類型進行確認。易于查閱的原始文獻和可供快速檢索的模式標本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基礎。目前,我們主要通過Tropicos (http://www. tropicos. org)鏈接BHL(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 org)或者Botanicus (http://www.botanicus.org)查閱物種原始文獻。BHL收錄的文獻數量較之Botanicus更為豐富,但網站的訪問并不友好。通過JSTOR (https://plants.jstor.org)查閱館藏在海外的中國模式標本照片,然而我們同樣無法獲取高清大圖,僅能看到縮略圖。與此同時,國外網址訪問較為困難,嚴重影響了分類學研究的開展和模式類型的確定。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完備的信息整合系統以快速獲取物種的原始文獻信息和模式標本數據。
4 展望
隨著標本數字化工作的持續推進,模式標本的數字化工作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包括哈佛大學標本館、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法國巴黎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內的多家大型標本館已經基本完成了本館的標本數字化工作并且通過網絡進行了數據的共享。這些標本館館藏了較多早期西方植物學家在中國采集的植物標本,其中不乏模式,這為模式整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目前,我們已經可以通過數字植物標本館對美國紐約植物園(NY)、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和哈佛大學標本館四家國外標本館館藏的中國植物模式進行訪問,后續更多海外標本館的中國植物模式標本數據也將陸續被上傳。植物模式標本數據的收集工作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量級,未來針對模式標本,我們應該著重于數據的清理。復雜的植物采集歷史勢必會給模式標本數據的標準化帶來一定的困難,詳實的地名、人名以及文獻資料是實現該工作的關鍵。雖然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也設立了“中國早期標本采集地名考”和“中國植物名稱作者(命名人)數據庫”分別對一些重要的地名和人名的對應關系進行了展示,但相關數據仍有較大的缺口。網站后臺人員不僅需要自身對數據進行持續的補充和更新,同時應鼓勵相關科研工作者將有價值的人名對應資料、地名變更資料以及分類學研究相關材料進行上傳并推行“誰上傳誰負責”的原則,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對相關人員進行資金支持。群策群力,推動該項工作平穩、快速地進行。
參考文獻:
BIODIVERSITY A-Z, 2014. Megadiverse Countries definition [EB/OL].[2021-09-19]. http://www. biodiversity a-z.org/content/megadiverse-countries.
CANTRILL DJ, 2018. The Australasian Virtual Herbarium: Tracking data usage and benefits for biological collections [J]. Appl Plant Sci, 6(2): e01026.
FANG D, 2017. The pictorial collection of type specimens of vascular plants in the herbarium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 Medicine Sciences (GXMI) [M]. Nanning: Gu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方鼎, 2012. 廣西中醫藥研究院植物標本館(GXMI)維管植物模式標本照片集 [M]. 南寧: 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EDITORIAL COMMITTEE, 1959—2004.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 1959—2004. 中國植物志 [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GRABOVSKAYA-BORODINA AE, 2010. Catalogue of the type specimens of East-Asian vascular plants in the herbarium of the V. L. Komarov Botanical Institute (LE) [M]. Moscow: KMK Scientific Press.
HERBER G, 1988. Harry Smith in China — Routes of his botanical travels [J]. Taxon, 37(2): 299-308.
LIN Q, YANG ZR, BAO BJ, et al., 2017. The database of type specimens in vascular plant at China National Herbarium (PE) [J]. Front Data Comp, 8(4): 63-76.? [林祁, 楊志榮, 包伯堅, 等, 2017. 植物模式標本的考證與數字化:以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為例 [J]. 數據與計算發展前沿, 8(4): 63-76.]
LUGHADHA EN, MILLER C, 2009. Accelerating global access to plant diversity information [J]. Trends Plant Sci, 14(11): 622-628.
OUYANG XJ, SONG ZQ, FAN ZJ, et al., 2019.Content analysis of holotype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Dinghu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Guangdong [J]. J Trop Subtrop Bot, 27(1): 90-98.? [歐陽學軍, 宋柱秋, 范宗驥, 等, 2019. 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生物主模式標本內容分析 [J]. 熱帶亞熱帶植物學報, 27(1): 90-98.
SCHMULL M, HEINRICHS J, BAIER R, et al., 2005. The type database at G?ttingen (GOET) — a virtual herbarium online [J]. Taxon, 54(1): 251-254.
SOLTIS PS, 2017. Digitization of herbaria enables novel research? [J]. Am J Bot, 104(9): 1281-1284
SUN H, DENG T, CHEN YS, et al., 2017. Curr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floristic geography [J]. Biodivers Sci, 25(2): 111-122.? [孫航, 鄧濤, 陳永生, 等, 2017. 植物區系地理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J]. 生物多樣性, 25(2): 111-122.]
TURLAND NJ, WIERSEMA JH, BARRIE FR,et al., 2018.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 (Shenzhen Code) [M]. Glashutten: Koeltz Botanical Books. DOI: http://doi.org/10.12705/Code.2018.
WANG LS, CHEN B, JI LQ,et al., 2010. Progress in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J]. Biodivers Sci, 18(5): 429-443.? [王利松, 陳彬, 紀力強, 等, 2010. 生物多樣性信息學研究進展 [J]. 生物多樣性, 18(5): 429-443.
WANG WC (WT), 2011. Significance of herbaria in plant taxonomy? [J]. Life World, 263: 1.? [王文采, 2011. 植物標本館在植物分類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J]. 生命世界, 263: 1.]
WANG YZ, QIN HN, FU DZ, 2004.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lant collection? [M]// WU ZY, CHEN XQ.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Tomus 1. Beijing: Sciences Press: 659-703.? [王印政, 覃海寧, 傅德志, 2004. 中國植物采集簡史 [M]//. 吳征鎰, 陳心啟. 中國植物志: 第一卷. 北京: 科學出版社: 659-703.]
WANG ZR, LIANG JM, WANG ZX, et al., 1994. History of Chinese Botany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61-162.? [汪振儒, 梁家勉, 王宗訓, 等, 1994. 中國植物學史 [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61-162.]
WU ZY, RAVEN PH, HONG DY, 1989—2013. Flora of China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St. Louis: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XIE D, LIU B, ZHAO ZN, et al., 2021. Diversity of higher plants in China [J]. J Syst Evol, 59(5): 1111-1123. https://doi.org/10.1111/jse.12758.
XIE D, WANG YQ, ZHANG XS, et al., 2019. A catalogue of plant type specimens and history of plant collecting in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 [J]. Biodivers Sci, 27(2): 211-218.? [謝丹, 王玉琴, 張小霜, 等, 2019. 神農架國家公園植物采集史及模式標本名錄 [J]. 生物多樣性, 27(2): 211-218.]
XING FW, 2014. Plant specimens recorded the change of Hainan geographical name [J]. Hainan Weekly, B04: 1.? [邢福武, 2014. 植物標本記錄海南地名變遷 [J]. 海南周刊, B04: 1.]
XING FW, ZHOU JS, WANG FG, et al., 2012. Inventory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f Hainan [M].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Press: 8-18.? [邢福武, 周勁松, 王發國, 等, 2012. 海南植物物種多樣性編目 [M].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8-18.]
YANG Y, 2012. Holdings of type specimens of plants in herbaria of China [J]. Biodivers Sci, 20(4): 512-516.? [楊永, 2012. 我國植物模式標本的館藏量 [J]. 生物多樣性, 20(4): 512-516.]
ZHOU YB, YU XL, WU N, et al., 2017. A catalogue of animal type specimens from the Shennongjia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 China [J]. Biodivers Sci, 25(5): 513-517.? [周友兵, 余小林, 吳楠, 等, 2017. 神農架世界自然遺產地動物模式標本名錄 [J]. 生物多樣性, 25(5): 513-517.]
(責任編輯 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