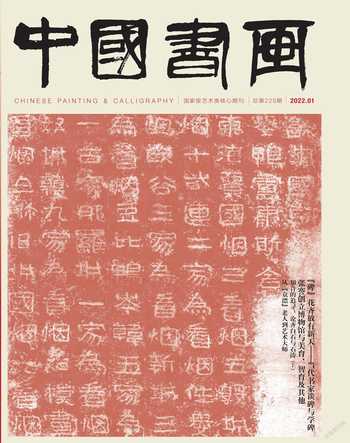一幅嶺南畫派的“新國畫”代表作
羅冰



1959年,黎雄才49歲〔2〕(其出生年先沿舊說),于旺盛之年、才力雄健之時,創作了《護林》一畫(圖1),并被中國美術館收藏。這是黎雄才暨《武漢防汛圖卷》后的又一力作,是一幅具有代表性風格的作品,全畫尺寸為縱159cm,橫322.8cm。此后,黎雄才的大畫力作不斷推出,畫松更是自出機杼、形神兼備。
《護林》一作,遠看畫面雖以山水奪目,但近觀便能感受到故事鮮明,主題突出。該畫的敘述能力,主要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畫中人物形態鮮明,二是場景元素“真實”。
《護林》事件中,黎通過三組人物的刻畫,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護林”主題,護林的重點在于“護”字,這一動詞的節奏是通過“緊中帶緩—緊—快”的方式層層遞進的。第一組:左面大石后的兩名騎馬的民兵,寥寥幾筆,人于馬上,隨時準備參與滅火的神態躍然紙上。其中一位民兵望著遠方,馬欲向前奔,一副急切奔馳支援狀,后一位民兵抬頭張望起火點,憂心忡忡之態,被刻畫得活靈活現。二人好像還通過觀察火情,商議著是否要返回營地,請求組織支援,或商議著怎樣更好地快速滅火。第二組:中景處,澗水滔滔,水面上一位正小心翼翼蹚水過河的民兵,襯托出了已過河的前方三位民兵組像。其中一位民兵牽著馱滿水袋的馬,急著送往救火前線。他前面的兩位民兵更是快馬加鞭趕著支援。這一組人物的描繪讓讀者不知不覺被這種火情如軍情的緊張氣氛所感染,欲參與其中。第三組:沿著疾馳的增援馬隊視線往上而去,右上方的救火前線已經有許多人在行動,有揮鍬滅火的,有用腳踩滅余火的,有潑水的......讓人感受到護林隊員的盡心職守、護林保林的覺悟,同時這樣的邏輯安排已經揭示了故事的結局—山火被撲滅,護林取得勝利,沒有造成大的損失。三組人物被山路以一條“S”形的路線串聯起來,雖有澗水相隔,但筆斷意不斷,自然形成了一個帶有節奏感的空間,完整地講述了一個護林的故事,構圖的精巧讓人擊節。這幅《護林》作品雖然包含了“黎家山水”創作中最重要的三種元素—松樹、巖石與瀑布流水,但此三者均服務于護林的主題。
整幅作品在技巧上展現了黎雄才的傳統中國畫底蘊,以及對日本畫的學習和吸收,但同時畫面個人風格突出,不愧是其代表作之一。下面試分析之。
黎雄才此畫受傳統中國畫技法影響,最主要表現在視點的游移上,平視、俯視、仰視,觀者的視線與畫家一起自由穿梭,卻又很好地統一在一幅畫中。黎雄才深受中國畫傳統浸染,筆墨功力很深。他曾說過:“中國畫要講究筆墨,無筆何能成畫。”“中國畫設色分重彩和淡彩二類,但不管重彩還是淡彩,務須以墨為主。”“色與墨,相得益彰。要色不礙墨,應保留墨之光彩氣韻,顯出筆之精神。”〔3〕此畫的墨與色之關系,正體現了黎雄才以墨為主,色墨相得益彰的色墨觀。他采用大筆揉擦、色墨渲染的方式,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有著照相機式的寫實功力,真實而嚴謹。雄奇的松樹、湍急的飛瀑、奇崛的險峰,在黎雄才強有力的筆法以及變化多端的走筆下,呈現出驚人的藝術效果。在描繪景物之外,陽光穿透崇林,與林中霧氣雜糅的折射,也很好地被畫家通過渲染的方式表達了出來。在火光沖天、煙霧繚繞中,林中蔓延的光感和空氣感,展現了他對水分和筆法的超強控制力,體現了他游學日本,對日本畫渲染技法的學習,以及對營造氣氛的日本朦朧體畫法的領悟。兩方滋養之下,黎雄才結合自己對松樹、巖石、瀑布的創作體會,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個人風格的筆墨語言。
人物造型方面,在近10年(20世紀40年代)的川渝、西北之行的寫生歷練以及《武漢防汛圖》卷(圖2)的成功模式下,黎雄才對人物同樣駕輕就熟。
與楊小彥所分析的《武漢防汛圖》卷不同,《武漢防汛圖卷》側重于整體場面,而非個體細節描繪,因此里面的人物通過意筆呈現〔4〕。《護林圖》正好相反,它通過個體人物形態去傳達事件,為了達到理想的視覺效果,人物處理上以“大”呈現,采用速寫的手法,落筆準確、流暢,形象雖較簡約,卻絲毫沒有影響觀眾對其形態、神態的辨別。細辨之下,可以看到其人物同樣有寫生觀察的細節,而非傳統概念模式下的人像,亦非傳統山水間的點綴。(圖3、4、5)
黎雄才有多幅以森林為題材的作品,如《森林晨曦》(圖6)、《森林》(圖7)等,但仔細閱讀就會發現這些作品在場景營造上存在位置緊張局促的特點(《森林晨曦》的創作時間與《護林》圖一致,或為創作《護林圖》時的一幅構思設計之作),畫面似是以望遠鏡觀測,只有局部感。而《護林圖》則顯得開闊,就像現在手機拍照的全景模式。作者采取的是平視圖取景,這樣的方式從視線上就給予觀者最為自然的畫面帶入感。全畫采用左右式構圖法,左面半封閉式,遮天蔽日的巨松頂天立地,連陽光都不能穿透,交代了事件發生地的地質情況和地貌特點。細看整幅作品,黎雄才還通過塑造樹木、山石、瀑布、急澗提供了可視化的細節。右面則是一個大轉折,不僅視線開闊,集中描繪了中遠景,并在層層暈染中推遠了景致。這使筆者想起另一幅關山月的著名作品《綠色長城》(圖8)。該幅作品同樣具有全景味道,也同為表現“森林”。關山月采取正視和俯視兩種視點創作全畫,在表現手法上直接得多,一排排樹構成密林,似一面墻擋住了觀者視線,樹尖上的重墨點形成遠山及大海。相較而言,《護林》一畫的場景設計就豐富多了,設計圍繞著護林的“曲折”過程展開,一開一合中有節奏地轉折、遞進。
畫面解讀完畢后,所引發的問題是:何以黎雄才在壯年之期,選擇了以“護林”為主題進行創作?
由于筆者目力所及,未查閱到黎雄才本人關于創作《護林》一畫的創作說明。帶著這份疑惑,筆者從1959年的年份往回檢索,有一條資料躍入眼簾: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在全國大規模造林的指示》,發文肯定了此前1956年造林事業的成就,但同時指出了目前的造林規模遠遠未能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該指示的主要內容包括:一、做好規劃;二、堅持依靠合作社造林為主,同時積極發展國營林場的方針;三、努力提高造林質量;四、做好更新和護林工作〔5〕。這份文件開啟了全國大規模造林的運動,而這樣的運動讓黎雄才敏銳地抓到,我想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護林》中呈現出的通俗化、教育性的特點與嶺南畫派的寫生傳統相一致;二是新中國成立后畫家自覺適應改造,尋找新的繪畫主題和進行視覺圖式革命的要求。新中國成立后,畫家們經歷了“為誰畫”“畫什么”“怎么畫”等問題的思想改造,一方面這樣的改造必然會形成新的規范,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的繪畫改造理論凸顯了繪畫為政治服務的功能,有著強烈的“人民性”,而這種“人民性”是與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黨性”相一致的。改造的目的是為了適應新中國社會建設的要求,突出反映中國畫的社會服務功能,特別是對共同的社會理想和國家觀念的認同,共同營造新中國文化環境是新中國在文藝各領域開展改造的目標。因此,這一要求也讓畫家們必須深入生活。傳統的“寫生”,由于與客觀世界的密切聯系性,自然也成為畫家們采用的改造革新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在解決以上三個主要問題的答案中,新中國的寫生要求必然區別于北宋以來所確立的院派格物式的寫生方式(一種帶有文人化的寫生之氣),改變了明清以來多借助程式化圖式創作的方式,從而也必然會帶來對傳統視覺圖式的革命,甚至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山水以“逸”為最高精神旨趣的價值標準。新中國對傳統中國畫的改造探索,根據地緣主要形成了京津、江蘇、西北、嶺南這幾個重要的地域群體。嶺南畫派素以對寫生的重視與訓練而著名。在寫生的方法上,強調觀物即景的方式,在寫生中訓練對景物的取舍和構圖能力、對自然規律特點的把握,尤其是在對山川景物與筆墨語言關系的認識與把握上、在山水畫意境的錘煉與營造等方面有深刻的創新與拓展。E55A3C2D-962D-46DF-84F5-495BFC8BEF02
根據現有的黎雄才學畫淵源的記載,黎在進入高劍父的春睡畫院之前,先受父親黎廷俊的影響,接受了家庭傳統書畫藝術氣息的熏陶。13歲就讀于西江名校肇慶中學之時,師從陳鑒學畫。陳鑒師從居廉,與高劍父是同門師兄弟,人稱其“勤奮過人,心無旁騖,以是盡得師傳;筆致蘊藉,恬靜秀潤,凡師之所能無不能之”〔6〕。正如李偉銘先生所說:“陳氏得益居氏的那種深入傳統堂奧,在寫生中體悟、把握對象韻致風神的藝術素養,成功地為黎雄才的藝術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點。”〔7〕從中可見黎雄才的繪畫藝術源自近代嶺南畫派的正傳。而“在寫生中體悟、把握對象韻致風神”的創作特點,更是嶺南畫派在寫生上的總結和貢獻。誠然,歷來畫家都強調寫生,從應物象形、隨類賦彩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從格物致知到“搜盡奇峰打草稿”等論述都強調了對客觀世界觀察了解體悟的重要性。那么嶺南畫派的寫生觀念又是如何發展的呢?黎雄才作為第二代傳人中的重要代表性畫家又有何獨創性呢?
在探討第一個問題時,我們先來看黃少強的一件作品。嶺南畫派很強調野外寫生。黃少強創作過一幅居廉夜晚觀察蟋蟀的畫作,畫中的居廉提著一盞燈籠,細致觀察蟋蟀在夜晚的習性。居廉那一絲不茍的背影讓人感受到居廉的專注與認真。這幅作品從某種程度來說,也反映了“二居”的寫生創作觀。
高劍父的“折中中西,融匯古今”的藝術主張,將從居廉、居巢二位大師發展出來的細致觀察的寫實主義精神、狀物精微的寫實技能,與西畫體系的技能訓練,尤其是對素描的學習結合在一起,這對傳統的造型能力是一種彌補。而要指出的是,高劍父所提倡的“西”與當時中國向西學的首要途徑是一樣的,同樣借助了日本這一橋梁。高劍父的“西”是被他所接受的諸如竹內棲鳳、橋本關雪、山原春舉、望月金鳳等日本畫家“過濾”了的西畫語言,雖然他也曾赴印度等南亞各國寫生和交流。在日本游學時,高劍父的主要活動范圍在東京,卻對當時亦稱霸日本畫壇的橫山大觀的“朦朧體”興趣不大〔8〕。這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救國主張和個人審美趣味的“主動選擇”。正如徐悲鴻在法學習,主要接受了寫實主義,而對當時正熱鬧著的現代主義的其他流派“視而不見”一樣。
黎雄才與老師的最大不同在于,繪畫要承載的政治訴求并不是他的重點。相較而言,他更是一位純粹的畫家,在藝術道路上執著追求。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川渝、西北寫生時,淡化了大關、春草的迷茫氣息,進一步領會高劍父的雄健之氣,追求大筆揉擦、筆墨渲染的渾融蒼莽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對宋畫的研摹而發展出了一種對大自然物體物理結構“真實性”的探究熱忱和執著表現。他還像馬、夏一樣關注小景寫生,以小景畫大畫,展示了自己獨特的寫生創意。自然物體結構真實的寫實性筆墨與朦朧體所強調的色彩效應、光影氛圍的融合,交織探索出了適宜他的語言形式和創意,從而實現了傳統向現代的轉化。
黎雄才對嶺南畫派寫生的獨創性還在于發展了松樹一科的寫生。如《護林》作品左面完整的那株松樹的描繪,樹根盤抓住泥石,樹干斜傾伸至畫中,松干之堅實,松枝之間的穿插和疏密長勢,松針生長的繁稀,一棵松生長形態的來龍去脈,這棵松與其他松的聯系、交疊等關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可見作者的求“真”之心、他的寫生功力,以及他對松樹的了如指掌。黎雄才在游歷日本期間大量寫生松樹,數量達9本速寫本之多,松的形態從百年老松到初發幼松,均一一涉獵。“他游歷了日本的山南海北,對日本各地不同的松樹、同一種松樹不同的樹齡以及同一種松樹處于不同季節和不同天氣狀態下千姿百態的變化進行過深入細致的觀察和研究,僅松樹的寫生稿就達2000件以上。”〔9〕如他所說的:“寫生一方面是加深對自然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培養自己的表現力,即按各種對象去尋求不同的表現方法。這也是創造的過程。”〔10〕畫中,松樹是以線條作為主要勾勒的形態結構,線條的干濕、長短、粗細都看出作者對線條運用之嫻熟、筆墨之靈動,看似隨意揮灑卻謹慎行筆。畫家亦非照相式地記錄景象,而是取舍得當,合理安排一草一木,這是他高超的寫生能力與創造的轉換,是一則貼近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藝術創作的杰出“范例”。這種“真實”是黎雄才脫離了日本游歷時期“朦朧體”的影響,堅持傳統線條筆墨為基礎,以現場“真實”感為契機,走出的“另類”的創造風格。
黃兆漢先生認為“現實性、大眾化和教育性”是高劍父論畫的三大原則〔11〕。高劍父認為繪畫應“描摹善狀,使閱者可以征實事而資考據”“俾下思之人,見之一目了然”〔12〕。所以高劍父是強調寫實的,他也反復強調:“新國畫是綜合的,集眾長的,真善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圖畫的精神氣韻,又有西畫之科學技法。”〔13〕同時主張繪畫作品做到“雅俗共賞,曲高和眾,要有時代精神,具有個人風格”〔14〕。藝評家曹玉林先生在《當代中國畫體格轉型》著作中提出當代中國畫的四大矛盾,即“中國畫的精英性質與大眾化趨勢的矛盾”“中國畫的傳統觀念與現代精神的矛盾”“中國畫的藝術趣味與視覺化取向的矛盾”“中國畫舊的語言體系與新的表現內容的矛盾”〔15〕。可以說黎雄才的這一大作同樣處于整個20世紀的中國在進行社會、文化、知識、價值觀念等的現代轉型之中,映射出了中西、古今、寫意與寫實、傳統與創新等語匯下,優秀畫家們所作出的探索成就。
同時,也由于高劍父這樣的藝術主張,使得他的兩位高徒黎雄才、關山月在新中國成立后文藝思想觀念的轉換中并不存在太多的思想障礙。他們一方面繼承了嶺南畫派通過寫生反映現實生活和吸取外來藝術優長的畫學精神,同時也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新文藝觀所主張的人民性、生活性的時代要求與嶺南派所堅持的反映現實生活的寫生觀的內在聯系性,讓不管是黎還是關都能較快適應新中國的文藝轉變,并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藝術創作中。黎雄才的《武漢長江防汛圖》、關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嬌》等,便是代表之作。如前所析,《護林》一作也展現出了“現實性”、“大眾化”(通俗化)、“教育性”這三大特征。
由此嶺南畫派從二居的體情察物到“二高一陳”(主要是高劍父)的現實性、大眾化、教育性的三大寫生原則,再到黎雄才的拓展(當然還有嶺南畫派二代人物關山月、趙少昂、楊善深、方人定、黃少強等人的貢獻),展現了“寫生”變化的發展和取徑。E55A3C2D-962D-46DF-84F5-495BFC8BEF02
中國山水畫從宗炳的《畫山水序》時已經開啟了“以形媚道”“澄懷觀道”的功能。文人畫提倡書法入畫、逸筆草草的藝術實踐,又構建了山水畫寫意抒懷的價值譜系。新中國成立后,山水畫成為諸多現實主義繪畫題材的一部分,“人民性”和“現實主義”亦為創作指導的不二法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山水畫在“筆墨當隨時代”的藝術理念指導下,諸多畫家結合著體驗生活與對中西筆法的學習而作出了富有時代個性的創造。王先岳在其博士論文《寫生與新山水畫圖式風格的形成》一文中將幾位山水畫家觀物即景的方式概括為“李可染:萬物靜觀皆自得”“傅抱石:游—悟—記—寫”“石魯:觀物以探真”“陸儼少:從默記到對寫”“關山月:真境逼神境,心頭到筆頭”。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讓黎雄才選擇以大畫的形式創作了這幅作品呢?
如前所述,在人民性和反映新中國建設成就的要求下,新中國的建設及生活新貌都是畫家們積極描述的對象。黎雄才的同門師兄關山月曾說:“畫家們由于明確了‘為人民服務這個根本性的方向之后,都自覺地要求深入到生活中去,他們按著各自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條件、不同的要求,紛紛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到人民群眾中間去,到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上山的上山,下鄉的下鄉,有的是跑馬看花,有的是下馬探花,有的則較長期地深入到火熱的斗爭中去......今天的許多中國畫家,正因為他們能與時代共呼吸,與廣大人民同感受,不論畫的是前人經常畫的山水還是花鳥,也絕不是前人的重復,而是通過自己的作品熱情洋溢地歌頌人民的理想,表現群眾的愿望,反映出大自然的變革時代的精神。畫家通過具體景物來抒發他們各自的新的思想感情,或表現勞動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和他們的優美情操。”〔16〕筆者目前尚未找到黎雄才本人就何以采用大畫形式來創作此幅作品的相關論述,但從關山月的這段論述中,我以為黎雄才的選擇正是這種“筆墨當隨時代”理念下的自主選擇。關、黎二人謳歌時代的激情與其師高劍父當年“革命”的憂患意識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歌頌體現了視覺圖像資源背后的思想轉換,這為他們建構新的語言形式和開拓新的繪畫表現境界提供了觀念支持,也為新中國山水畫注入了新的審美價值。總之《護林》一作,不愧為新中國成立后,嶺南畫派“新國畫”的一幅代表作。
(作者為廣東文藝職業學院副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在讀博士)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
注釋:
〔1〕此處使用的新國畫加上引號,是指1950年經《人民美術》發文所提倡開展的“新國畫運動”,而非民國時期高劍父在廣東畫壇所倡的折中中西、融匯古今的“新國畫運動”。
〔2〕2011年第3期《美術學報》發表了陳跡《黎雄才研究之一:幾則早年行跡的考訂》一文,文中對黎雄才的生年進行了考察,認為黎雄才實際出生于1913年。
〔3〕張展欣:《縱橫黎雄才》,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200、199頁。
〔4〕參看楊小彥:《論黎雄才人物畫》,《美術學報》2011年第3期。
注釋:〔5〕參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大規模造林的指
示》,《甘肅政報》1958年12期。
〔6〕鄭春霆:《嶺南近代畫人傳略》,香港:廣雅社1987年版。轉引自李偉銘:《黎雄才、高劍父藝術異同論—兼論近代日本畫對嶺南畫派的影響》一文,見李偉銘:《圖像與歷史—20世紀中國美術論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頁。
〔7〕李偉銘:《黎雄才、高劍父藝術異同論—兼論近代日本畫對嶺南畫派的影響》,前揭《圖像與歷史—20世紀中國美術論稿》,第80頁。
〔8〕這也可能與彼時橫山大觀赴美考察,日本美術院因資金匱乏而近于名存實亡等因素有關。李偉銘:《黎雄才、高劍父藝術異同論—兼論近代日本畫對嶺南畫派的影響》,前揭《圖像與歷史—20世紀中國美術論稿》,第88頁。
注釋:
〔9〕見翁澤文:《黎雄才藝術生成論》一文。
〔10〕前揭《縱橫黎雄才》,第206頁。
〔11〕參閱黃兆漢:《高劍父畫論述評》,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2年版,第12頁。
〔12〕轉引自李偉銘:《黎雄才、高劍父藝術異同論—兼論近代日本畫對嶺南畫派的影響》一文,見李偉銘:《圖像與歷史—20世紀中國美術論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頁。
〔13〕同〔12〕,第142—143頁。
〔14〕關山月:《有關中國畫創作實踐的點滴體會》,見關山月:《鄉心無限》,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頁。
〔15〕參看曹玉林:《當代中國畫體格轉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版。
〔16〕關山月:《論中國畫的繼承問題》,見關山月:《鄉心無限》,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3頁。E55A3C2D-962D-46DF-84F5-495BFC8BEF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