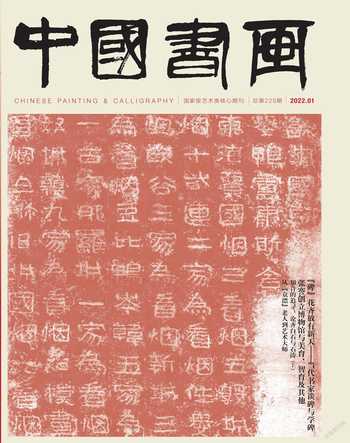張謇的書畫收藏與賞鑒
胡月

一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海門人。張謇的書畫收藏與南通博物苑藏品的整理有直接關聯,南通博物苑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建,是中國最早的博物苑。1914年編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載,全館收錄品物2973號,書畫類登錄101件,張謇捐贈就有71件,每號一至若干件不等。早期博物苑隸屬于通州師范學校,源于張謇認識到近代西方各國趕超中國,是因為“教育之普及”,而博物苑應該“成學校之后盾”,一方面是配合學校彌補學科教育的不足,另一方面是“留存往跡,啟發后來,風義所及,兼蓋有之”,加強對金石書畫等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1〕。《通州博物館敬征通屬先輩詩文集書畫及所藏金石古器啟》中明確了博物館所需藏品需要本地藏家的資助,言辭懇切,“美術部擬求老師先生經史詞章之集,方技書畫之遺。謇家所有,具已納入”〔2〕,顯示出張謇博大的胸懷以及為中華文明延續血脈的苦心,甚至到了晚年,別人祝賀他七十大壽所贈送的極盡珍貴的孔雀明王象牙雕“因贈博物苑南館美術部永寶存之”,先生亦毫無吝嗇捐獻于博物苑。始終具有國際眼界的張謇,以南通為支點,創建南通博物苑,推動了全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使私藏走向了公眾視野,無數的珍貴文物得以保存。
二
清末狀元身份的張謇,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學素養。在文化藝術上,張謇的詩作風格“風華典贍,韻味綿遠”,對于現實生活則極具現實主義特色“惟二張為能自道其艱苦懷抱”。對于農民勞作之艱辛,張謇以簡練筆觸寫道:“誰云江南好,但覺農婦苦,頭蓬脛赤足籍苴,少者露臂長者乳。亂后田荒莽且廡,瘠人腴田田有主。”〔3〕在《題文姬歸漢圖》中道:“漢月何曾老,紅妝款塞來。相看蘇武節,但覺魏王才。故國千兩重,聞茄二十哀。獨憐青冢草,終古向龍堆。”〔4〕張謇在書法上亦造詣頗深,隨著生活閱歷的提升以及汲取了歐陽詢、褚遂良“鋒利剛勁、結體松而不散”的藝術特色,張謇達到了“于平正中見險絕,于規矩中見飄逸”“乍疾乍徐,飛動婉轉,氣貫長虹”〔5〕的書法風格。
深受傳統儒學教育的熏染,詩書造詣潛移默化影響著張謇的書畫收藏。張謇的關注點集中于“人品”與“畫品”的聯通上,對于畫者的高潔之行,必不吝言辭贊之,畫作佳處往往以精煉筆觸記其精彩。在《文衡山小字長卷跋》中“自云比來風濕交攻,臂指拘窘,不復向時便利,而運指于方三分小格之中,正復縱橫伸縮,寬綽有余”〔6〕,正是有著極深的書法造詣的基礎,才能以平實話語詮釋所鑒書畫的妙處。張謇對于書畫收藏的態度頗是隨遇而安,并不會為覓得名家之作而刻意營求。收集作品注重的是畫作質量,而不是畫作名氣。在張謇的書畫收藏中有為數不少的畫作無款,張謇亦做好賞鑒記載,并沒有分別之心。對于喜愛的畫作,也會因為囊中羞澀而放棄,曾記錄:“三十余年前于京都廠肆見馬江香畫牡丹八十幅兩大冊,肆主云本百幅,并致而觀之,百幅之花位置姿態無一同者,嘆為精絕,索值裁五百金,一人不能得,商諸可莊兄弟合致之,亦不能,遂罷。今不知流落何所矣。”〔7〕相比于同時期收藏家,晚年的張謇篤信佛教,對于書畫收藏更多是“不執著”的修行態度。他題劉世儒《萬斛清香圖》時雖然知其為精品巨制,但卻生出空落之感,“更三百年,不知此畫此詩復在人間何許矣”。《題懷素帖》中對于書畫的收藏顯示出超然姿態,“素師書所謂是法即非法,非法無非法者,當以禪理觀之”〔8〕,可見張謇對于書畫收藏的開放姿態與豁達心胸。
(一)
作為從農村走出的狀元,張謇“以天下為己任”作為個人道德操守的準則,這種龐大的民族責任意識也反映到張謇收藏了一大批南通籍書畫家的作品。在張謇為博物苑中館匾額題跋云:“中國金石至博,私人財力式微,搜采準的務其大者。不能及全國也,以江蘇為斷;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為斷。”〔9〕張謇選擇搜集南通籍書畫家的作品是因為博物苑的籌劃之策,搜集本地書畫較為容易,見效快。在其所收集的書畫作品中,舉凡南通明清之際較有才氣的書畫家,他幾乎都有收藏,并做好記錄和題跋,例如南通籍的包壯行,對于其畫作,張謇很是推崇。南通博物苑所藏的近十米的《墨梅屏》,張謇在畫作右端下側以行書題跋:“此前明崇禎癸未進士包石圃壯行畫。《繪林伐材》稱壯行工鉤勒梅花、水墨竹石。顧鄉里之流傳絕少,似此巨幅尤為僅見。初得時前側之下猶存一包字,復為裱工剝棄,無可征信,后之人將不辦為何人稱作,可惜也。題而識之,赴博物館以存先輩名跡。”〔10〕這段題跋的時間為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二日,此時正值通州師范學校始建,育嬰堂建設逾一年,張謇的個人經濟生活不甚寬裕,實業壓力驟增。對于《墨梅屏》的題跋,張謇依然顯示出了精謹嚴肅的學術風范。這段文字首先明確該畫何人所作,收藏機緣也頗為有趣,包括詳細記錄這幅畫最開始得時只在前側存了一個“包”字,后來被裱畫工人剝棄,題跋原因是為了后輩知曉這幅畫的來向,“赴博物館以存先輩名跡”,可見對于家鄉先賢遺作保存的苦心。另張謇所藏并贈予南通博物苑包括李方膺、胡長齡、顧驄等南通地方籍畫家作品,為地方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可供研究和觀賞的大批資料,這些都歸功于張謇禮敬鄉賢之心。
(二)
《柳西草堂日記》可以推斷早期張謇對于書畫的收藏活動始于光緒八年(1882),處于為吳長慶做幕僚時期,最早的書畫藏品現存可查為隨慶軍于朝鮮所購的十二頁明代各書家書法扇面。《蓬萊閣感事》中題詩“金宮銀闕照東瀛,畫角朱旗漢將營。去日樓船通海市,歸來槲葉滿山城。中郎拜職勛資盛,上將籌邊畫諾輕。辛苦至尊憂社稷,年年征調朔方兵”。此時的張謇對于書畫收藏的主觀意趣尚存于“私家之收輯”。張謇“處衰亂之世,只有敬以免禍。敬則神常斂,心常謹,潛龍之義也,故《小旻》《小宛》末章皆以‘戰戰兢兢’終之”〔11〕。雖然囊中羞澀,但是作為士人業余愛好的書畫收藏,張謇也會購置數件“以自慰其場屋辛苦”。
《邊葦間畫冊跋》中,對于曾經賞玩題款過的畫冊,重又遇到,雖知“國體既變,甲寅北行”,最終將此畫購回南通“示世世子孫知余與是冊有如是因緣”。深受傳統書畫熏染的張謇,無論是時代風氣還是身份歸屬來說顯示出了對于文人書畫的偏愛。陳師曾先生對于文人畫定義為“曠觀古今文人之畫,其格局何等謹嚴,意匠何等精密,下筆何等矜慎,立意何等幽微,學養何等深淳,豈粗心浮氣輕妄之輩所能望其肩背哉!但文人畫首重精神,不費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優美者,仍不失為文人畫”〔12〕。對于梅蘭竹菊等文人題材,張謇多有贊譽;對于山水畫作,筆墨儒雅高意所投射的畫品,張謇也會詳細記錄畫家品性之高潔。因為早年游走于朝鮮、日本等地,張謇也得以很多機會觀摩古代繪畫名作,養成了不俗的鑒賞品味,且除了筆墨上的關注外,對于畫后的“助教化”功能尤為看重,有著典型中國文人儒家思想的指向。書畫創作、收藏和鑒定遵循的是“鑒是前提,藏為手段,賞才是目的”〔13〕,張謇從一定角度上,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書畫鑒藏家,其中對于書畫的來源和時間做出明確記錄。在《張謇全集》中,書畫題記有65篇之多,且多數作長篇題跋,力求嚴謹,同時對于書畫風格和內容做出極高的技術分析,增加了畫面趣味性。《張謇題潘思牧嵩岳長松圖》選自《畫譜》題跋“郭熙嘗作連山一望松為文潞公壽,以二尺余小絹作一老人倚杖巖前一大松下,此后作無數松,大小相亞,轉嶺下澗幾千百松不斷,故一望云爾。他如雙松、三松、五松、六松、喬松,皆此例也。此巨幅故尤可貴”〔14〕,顯示出張謇不俗的鑒賞力。
(三)
相比于吳湖帆、趙伯駒等近代收藏大家,張謇雖然不及前者收藏之豐,但是對于觀音題材的收藏卻是獨樹一幟,專收觀音像近百余件,并編輯《歷朝名畫觀音寶相》,對于觀音主題書畫的收藏“與他晚年得子有關”〔15〕。《狼山觀音巖觀音造像記》開頭即題:“江淮男子張謇,昔年四十未有嗣胤。先室徐夫人既為置簉,又師古禖祀,歲二三月必齋祓禱于狼山之觀音巖。祈必有報命,祝若曰:報佛恩者寫經造像。”〔16〕據傳在觀音收藏中,有唐吳道子(傳),宋賈師古、牧溪,元錢選、趙孟頫、管道昇,明仇英、徐渭、丁云鵬,清陳洪綬、張照金等,另有玉雕、石刻、鎏金等古董,《歷朝名畫觀音寶相》共計154件,序、跋皆請大德高僧佛門弟子為之。南通博物苑收藏的觀音像主要來自浙江杭州的辯利院,乾隆年間刊印過的院志中詳細著錄了辯利苑所藏觀音畫像。這批畫像已有名氣,后來不斷有新的觀音畫像錄入,清末時已達160余幅,后因浙江一帶時局混亂,院寺瀕臨毀亡,住持僧靜法委托友人張子騫尋求外界保護以存文物,張子騫遂將觀音畫作全部寄給張謇。張謇在《狼山觀音院后記》做了明確記載,“若宗廟法物之不敢妄置,若對越尊嚴之不敢褻視,苑不能藏也”〔17〕,后轉藏于狼山觀音院,并委托鎮江金山寺靜圓和尚主持。后幾經磨難,直到1951年,觀音像重新入藏南通博物苑。
張謇對于觀音題材的收藏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時代使然。辛亥革命以后,社會道德文化系統混亂,傳統知識分子力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求慰藉和挽救之道。早年的張謇排詆佛教提倡廟產興學〔18〕,將南通師范選址于大佛寺,隨后“立初等小學十所,各就其他不再祀典之廟營之”這些大膽的舉動使得南通地方之人“危疑震撼”〔19〕。隨著舊有社會秩序、道德規范等陸續出現問題,張謇逐漸意識到人心的歸屬,“即佛教也不是那么保守,信仰佛教也可以近代化,佛教原來與西學頗有相通之處”的觀念在趨新士大夫中盛行〔20〕,張謇也逐漸改變對于佛教的看法。同時伴隨著釋太虛在佛教中加入世間性的色彩,佛教不再僅僅被認為是“非以徒厭世間獨求解脫也”,規范人事也符合了知識分子挽救人心和社會道德的愿望,這樣的歷史機緣為張謇收藏大量觀音主題繪畫提供了更多的空間。
其中書畫類觀音造像大多精美莊嚴且不乏名家之作,元代畫家趙孟頫的《半身觀音圖》,絹本,設色,縱42厘米,橫36厘米,分為兩個部分,上端是明代畫家文徵明的小楷《心經》全文,左下朱文方印“文徵明印”“悟言室印”,右下方印“徵仲父印”,字體溫純精絕。下端為趙孟頫所繪半身觀音,觀音眉眼純秀,慈悲莊嚴,頗有古風。
明清畫家項醇《千手觀音》,紙本,縱94厘米,橫54厘米,畫面上方為“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下鈐朱文方印“臣周易印”。畫心左下方署款“嘉慶乙亥二月歙邑弟子項醇齋沐敬寫”,并加蓋“盧峰侍者”“項醇”“項承醇字泗舸號云谷”三方白印,朱文收藏印“摩松堂供養”,畫心右下有“仁和弟子胡燮敬奉辯利禪院”,畫中觀音端坐蓮座之上,線條細勁,賦色厚重,為南通博物苑千手觀音精品。
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金農《墨筆白衣觀音》,紙本,縱96厘米,橫39厘米,畫心右側題款“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相。杭郡金農圖畫。農”,左下角“南通狼山觀音院供奉”“芬陀利華”“辯利院供養”收藏印三枚,右下角“邁孫眼福”朱文印。畫中書法自立格調,具金石氣,白衣觀音焦墨勾邊,筆意自由古拙,反映了作者不落俗套的藝術視角。
“揚州八怪”之一羅聘《德王觀音圖》,設色紙本,縱131厘米,橫57厘米,乾隆四十二年(1777)繪制,左右各作《心經》及《七佛偈》。這幅觀音圖體現了羅聘“畫無不工”以及“羅兩峰聘筆情古逸,思致淵雅,深得冬心翁神髓,墨梅蘭竹,均極超妙,古趣盎然,人物佛像,尤奇而不詭于正,真高流逸墨,非尋常畫史所能窺其涯涘者也”(清秦祖永《桐蔭論畫》)。《德王觀音圖》延續了羅聘一貫德繪畫風格,衣紋線條淺淡卻不失堅勁有力,觀音面目慈悲仿若鄰家長者,頗具人性色彩。
三
張謇一生事業卓著,卻也歷盡人間坎坷。他生活的時代,國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的憂患意識始終縈繞于心。“夫人莫哀于心死,事莫痛于亡國。”〔21〕棄仕從商后,張謇大力發展家鄉教育文化事業。1922年,全南通僅公私立小學達347所。為了發展家鄉事業,張謇多次登報賣字籌錢,“仆字本不鬻錢,有時借逃人役則鬻,有時營實業乏旅資則亦鬻,年來鮮暇,不復為。今發起通州新育嬰堂,自三十二年九月開堂,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初,收嬰逾千數。原有經費僅銀元四千,而用逾二萬”。“仆不自盡其力,無以對凡應募之人,而確為之所自盡者,唯有鬻字。”〔22〕雖賣字換錢中常遭遇不快,但為了家鄉的人文建設事業,依然不辭辛苦,將南通發展為全國模范縣,一求“為天下之表率”。
張謇推行地方自治,在引進人才,促進文化傳播方面使得南通一改往日寂寥閉塞的文化環境,張謇首倡并出資成立南通金石書畫會,書畫會成立之初,全國便有280多人申請入會,其中“國內著名畫家、書畫家吳昌碩、王一亭、張謇、田桐、朱屺嶦、徐悲鴻、錢化佛、金拱北、朱石其等,均是該會的會員”〔23〕。書畫會出版會刊《藝林》,出版了《中國名人金石書畫集》和《俞吟秋珍藏名人書畫集》,同時在出版事業上因興師范學校,創辦中國近代頗有影響力的翰墨林印書局,張謇引入諸宗元、李苦李、金澤榮等文人。印書局一方面兼營書畫交易和裝裱,促進南通書畫界交流,另一方面編印了很多字帖供學生研習,使得翰墨林成為文人雅士書畫交流的平臺。正如張謇為大生紗廠題寫的那副楹聯“為大眾利益事,去一切嗔恨心”,成為張謇一系列慈善行為的最好詮釋。注釋:
〔1〕張謇:《張謇全集》第4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頁。
〔2〕《通州博物館敬征通屬先輩詩文集書畫及所藏金石古器啟》,《張謇全集》第5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頁。
〔3〕張謇:《張謇全集》第5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4〕同〔3〕,第22頁。
〔5〕錢榮貴、楊天奇:《張謇書法的“師古”與“通變”》,《中國書法》2020年第11期,第154—156頁。
〔6〕《文衡山小字長卷跋》,《張謇全集》第4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7〕張謇:《張謇全集》第6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頁。
〔8〕《題懷素帖》,《張謇全集》第6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頁。
〔9〕《博物中館匾并題語》,《張謇全集》第6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257頁。
〔10〕南通博物苑編:《張謇收藏書畫選》,1995年版,第16頁。
〔11〕《柳西草堂日記》,《張謇全集》第6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185頁。
〔12〕陳師曾:《中國繪畫史》,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52頁。
〔13〕梁江:《中國美術鑒藏史稿》,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14〕同〔10〕,第63頁。
〔15〕沈啟鵬:《張謇與美術》,《美術》2003年第4期,第114頁。
〔16〕《狼山觀音巖觀音造像記》,《張謇全集》第6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頁。
〔17〕《狼山觀音院后記》《,張謇全集》第6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頁。
〔18〕徐躍:《從排詆佛教到提倡佛教—從清末民初張謇為主的討論》,《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65頁。
〔19〕《論創辦地方實業教育致端撫函》,《張謇全集》第4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
〔20〕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53頁。
〔21〕《為時事致徐世昌函》,《張謇全集》第1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頁。
〔22〕《南通新育嬰堂募捐啟》,《張謇全集》第5卷,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115頁。
〔23〕許志浩:《中國美術期刊過眼錄(1911—1949)》,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頁。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藝術學院)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