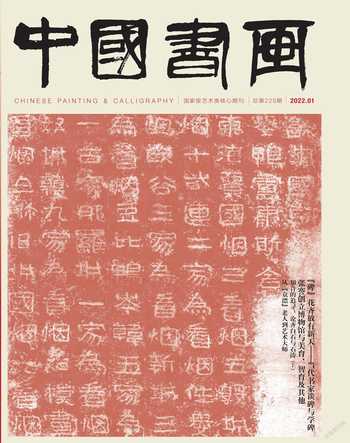一曲曲悠揚唯美的輕音樂
范迪安等


編者按: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美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繼承、改造、創新貫穿其中。我們在關注書法與傳統中國畫創作的同時,也需要關注諸如版畫、油畫、新水墨等以反映中國意境、國家大事、人民生活、時代氣息為主題的創作,這些創作在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氣質方面也發揮了各自的長項。有鑒于此,本刊特推出“新視域”欄目,為讀者呈現傳統書畫以外的美術力量。
我和偉冬是美術教育和美術史論研究領域的同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擔任南京藝術學院院長期間,堅持立德樹人根本方向,以學科建設為引領,以創作科研新成果服務社會,使學校的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影響俱增,受到同行們的高度贊譽。多年來,他在美術歷史和理論研究領域辛勤耕耘,視野開闊,學殖深厚,思鋒勁健,文采粲然,做出了突出貢獻。現在他從校長崗位上退下來了,又拾起畫筆,有時間從事美術創作,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他有思維開闊的管理經驗,又有閱畫無數的視覺積累,“雙管齊下”便有藝理相通的暢快。落筆之際,抒發性靈,尋求一種新的路徑和方式去表達觀點、見解和情感,也傳達出一種具有深厚學者情懷的格調與意境。
—范迪安(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
古語有言: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劉偉冬以退休之年習畫、展畫,在引領學校發展大業、立德立功之后,退而繪畫立心、修辭立誠,此大智也!偉冬的畫,研習已有時日,如是研習,正是要在藝中求真情流露,此即是仁心。
—許江(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劉偉冬校長獨特的學術和管理理念,使南京藝術學院成為中國藝術院校的標桿。他從校長崗位上退下來以后開始畫畫,我以為以他的智慧和熱情一定能在繪畫領域有所收獲!
—李勁堃(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廣州美術學院院長)
早聞劉偉冬院長也畫油畫,但一直未能有機會見識。我們熟知的偉冬先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院長、學者、理論家、國家藝術門類美術學學科委員會召集人。由于長期從事大量管理工作和學術活動,而少于看到他的油畫作品公開露面。近日,終于從圖片上看到了偉冬先生的油畫作品,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看來并非是預想的那樣只是玩玩而已,而是有長期偷偷磨煉之嫌!因為從技法上看,他已經相當嫻熟,不僅有深厚的形色修養,而且還蘊含有融匯東西、貫通物我之氣韻。在用筆和肌理的節奏上都凸顯了瀟灑和輕松的氣質,我們不禁要感嘆:一位理性者的感性神游在步入花甲之年剛剛開始!
—龐茂琨(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四川美術學院院長)
讀劉偉冬的繪畫,我感受最為強烈的是他對于生活的日常感和自然靈性的表達。這是一對矛盾的主題,他卻能得其生趣以意求之。偉冬將繪畫的視覺經驗轉化為內心理想審美的營造,畫面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充盈著一種傳統文人獨有的詩意。以物觀物是偉冬繪畫的特點。以小見大的主題是寫景也是抒情。偉冬將自身的感悟、經驗融入物象之中,草草數筆但意蘊深遠。無論是對內容的取舍,還是畫面的置陳布勢,他沒有囿于對象形態的束縛,而是深入挖掘物象的內在精神。這種對于日常的禮贊與對藝術本源的觀照,是他作品打動人心的力量源泉。偉冬畫了很多園林,但又超越園林本身。園林是古代文人的思想寓所和精神空間,從方圓土地養身心的三維空間,到寸尺紙絹抒胸懷的二維世界,白墻黑瓦間的移步換景,是他心中無限遼闊的萬里山河。他的畫面滲透著一種由來已久的時空觀念,對時間、空間、畫者、觀者的思索,讓他的作品具有一種現代性。偉冬筆下的色彩清潤尚雅、沉穩內斂。他在客觀寫實和主觀象征中找到一種平衡,畫面的光感柔和,輪廓消散,飽和微妙富有層次變化,流露出一種純凈的詩意。這種溫文爾雅的從容含蓄正是江南文人特有的精神氣質。毫無疑問,江南獨特的地理環境、人文積淀和學術傳統,給予了偉冬許多養分。但偉冬的身份是多重的,他繪畫中的厚重與深思,更多地源自對藝術的思考與探索,源自他在美學、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修養。他將傳統文人繪畫所具有的文學性、哲學性和詩意抒情集于畫面之中,這是古典文化精神的現代回歸,對很多當代藝術家都具有啟示性的意義。
—曾成鋼(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美術學院院長)
偉冬兄有才,文章好,能作詩,能書法,很多年前,我偶爾看到他畫的幾張中國畫,有模有樣的。后來,偉冬兄又開始畫油畫了,有靜物,有江南園林,還有殘荷池塘雪景。他的油畫作品意境青澀淳靜,色彩簡潔清朗,頗有些寫意的韻味,其內心包含著的文雅、聰慧、隨性、敏思等諸項素養在此間匯成起伏陳誦的樂符,向我們播送出一曲曲悠揚唯美的輕音樂。
—周京新(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偉冬兄的油畫富有寫意精神,有意境,有極強的表現性。20世紀中國油畫一直在追尋一條油畫民族化的道路。南藝劉海粟先生從印象派之后的現代主義探索表現主義與中國寫意之風相結合的藝術,蘇天賜先生承林風眠之風,以詩情與寫意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油畫風格,富有江南神韻。偉冬兄于這樣的傳統中,深得滋養。遺風再傳,以立新意。愿新的審美氣象為他的不斷創造賦予蓬勃的生命樂章。
—吳為山(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美術館館長)
這些小品畫作初看略似林風眠一路中西結合之彩墨畫,其所畫題材粗看貌不驚人,多取大畫家們不屑剪裁之情景,或者說這個急死忙活的時代的匆匆過客們視而不見的去處,而一旦被他攝取入畫,便每幀都凝聚了一種不解的情調和恍如隔世的情懷。這些被遺忘的角落,以及盛開過,或許已經脫水干枯卻依然展示著的不鮮的花朵,記憶著以往或現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或者某些人曾經的某些事情,或許清楚,或許已記不清的過往,或許什么也不曾發生也未可知。畫面章法嚴謹,取景平實以墨為主,使我以為是彩墨自是當然,而仔細看來確實是油畫材料,我便有理由堅信一種看法,那就是中國人畫的都是中國畫,無論你是什么方法材料,即便觀念、思想,其精神與審美都是中國的。因此,油畫傳入中國時叫作“西畫”,而現今多稱“中國油畫”,說的是材料,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偉冬以他對繪畫的真情投入所作油畫材料的中國畫,一如他的為人,嚴謹謙遜,含蓄中充滿感受背后深邃的情感。耐看的畫面、不露痕跡的筆觸透出的豐富和莫名的人格的真誠,其所傾訴和流露的情緒,自是我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神秘去處。或許,這種不可名狀的不知所是,正是這些畫的可貴之處。
—楊曉陽(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會長)
責任編輯: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