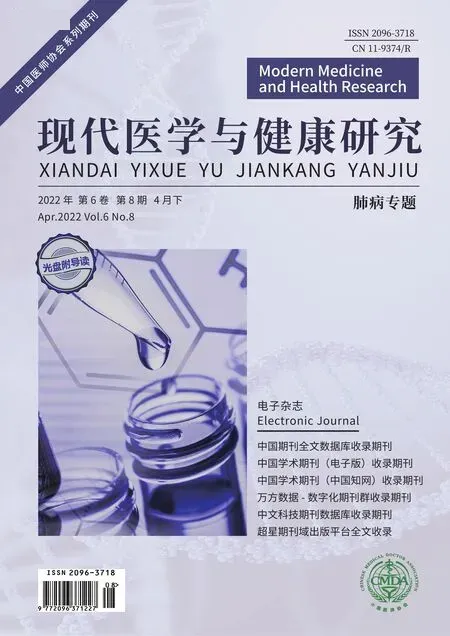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影響因素及血壓節律、血壓變異性變化
田關源,鄭 玲,鐘曉澤,吳義強,吳武忠
(揭陽市人民醫院風濕腎內科,廣東 揭陽 522095)
維持性血液透析是終末期腎病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案之一,而血管通路是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線,動靜脈內瘺與其他通路相比,因具有壽命長、創傷小、并發癥少、干預少、費用低等特點,已成為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公認的首選血管通路[1]。但動靜脈內瘺因成熟不良致內瘺失功的發生率較高,且血管通路失功仍是透析患者住院的首要原因[2]。長期臨床實踐證明,自體動靜脈內瘺也存在一定的早期功能失功現象,一旦自體動靜脈內瘺失功將會嚴重影響患者治療效果與生活質量[3]。血流動力學因素與透析通路相關,尤其是血壓可能會成為影響動靜脈內瘺失功的因素,而目前相關報道觀點尚未統一。動態血壓監測能更全面、客觀地反映血壓水平和血壓晝夜節律變化[4]。基于此開展本研究,旨在探討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影響因素及血壓節律、血壓變異性變化,現將研究結果作如下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7月至11月揭陽市人民醫院收治的122例進行維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開展前瞻性研究。所有患者中男性59例,女性63例;年齡39~78歲,平均(64.23±7.66)歲;其中糖尿病腎病40例,原發性腎小球腎炎35例,免疫球蛋白A(IgA)腎病23例,高血壓性腎病14例,狼瘡性腎炎6例,梗阻性腎病4例;合并癥:糖尿病66例,高血壓88例。納入標準:符合《腎臟病學(第3版)》[5]中的相關診斷標準,進行維持性血液透析的終末期腎病患者;年齡20~80歲者;實施上肢腕部動靜脈內瘺術(頭靜脈與橈動脈端側吻合)者等。排除標準:術側艾倫(Allen)試驗陽性者;術側橈動脈狹窄或閉塞者;術側頭靜脈近端有狹窄或血栓者;四肢近端靜脈或中心靜脈狹窄、血栓或因毗鄰病變阻礙靜脈回流者;預計存活時間短于3個月者;術側鎖骨下靜脈留置心臟起搏器者;有動靜脈內瘺手術禁忌證(如凝血功能障礙、感染及不能配合手術等)者等。本研究經揭陽市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1.2.1 動靜脈內瘺通暢性評估 動靜脈內瘺失功判斷標準:內瘺充盈不良,上方不能觸及震顫,血管雜音微弱,或未能聞及,血流量<200 mL/min,血流量過少或者血流終止,不能達到血液透析的最低血流量要求;內瘺通暢判定標準:內瘺充盈良好,上方觸及震顫,可聞及響亮血管雜音,血流量≥ 200 mL/min[6]。以是否動靜脈內瘺術后早期失功分為初級通暢組(102例)與早期失功組(20例)。其中內瘺早期失功的判定標準:術后內瘺成熟不良或開始透析后3個月內透析血流量不足以維持透析[7]。
1.2.2 一般資料 ①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身高、體質量。②臨床資料:合并癥、血小板計數、總膽固醇、C‐反應蛋白、血鈣、血磷、全段甲狀旁腺激素等,采集所有患者空腹靜脈血5 mL,一部分血樣采用全自動血氣分析儀檢測血小板計數;另一部分血樣進行離心(3 000 r/min,10 min)取血清,采用化學發光法檢測血磷水平,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總膽固醇水平,采用酶聯免疫吸附實驗法檢測血清C‐反應蛋白、全段甲狀旁腺激素水平。
1.2.3 動態血壓監測 日常活動下,于術前24 h采用攜帶式動態血壓監測儀器(德國IEM公司,型號:Mobil‐O‐Graph)監測動態血壓,日間于6∶00至22∶00進行監測,30 min/次,夜間于22∶00至次日6∶00進行監測,夜間睡眠時間<6 h或日間睡眠>10 h則數據無效。血壓節律參數包括:24 h平均收縮壓(24 h SBP)、24 h平均舒張壓(24 h DBP)、夜間SBP及DBP下降率。血壓變異性指標包括:24 h收縮壓標準差(24 h SBP SD)、24 h舒張壓標準差(24 h DBP SD)及變異系數(CV),CV=標準差/平均數;夜間血壓均值比白天血壓均值下降率≥ 10%稱杓型血壓,<10%稱非杓型血壓[8]。
1.2.4 多普勒超聲檢查 于術前24 h采用便攜式彩色多普勒超聲儀器(美國索諾聲公司,型號:M‐Turbo)進行檢測。掃查肱動脈、橈動脈、尺動脈及頭靜脈,觀察其是否存在狹窄或閉塞,在上臂近肘部止血帶束臂并囑患者握拳以測量加壓擴張后頭靜脈直徑,開啟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測定血流量。
1.3 觀察指標 ①統計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術后早期失功的發生情況。②比較初級通暢組和早期失功組患者一般情況、臨床指標及術前內瘺彩超參數。③比較兩組患者動態血壓監測參數。④采用K‐M生存曲線分析術后1年患者內瘺通暢率。⑤采用多變量Cox回歸分析法分析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術后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影響因素。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s)表示,行t檢驗;計數資料用以[例(%)]表示,行χ2檢驗;應用K‐M法對患者術后1年內瘺通暢曲線進行繪制,并采用log‐rank檢驗進行比較;采用多變量Cox回歸分析法分析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危險因素。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動靜脈內瘺術后早期失功情況及初級通暢組和早期失功組患者一般情況、臨床指標及術前內瘺彩超參數 122例患者中,早期失功20例,占比為16.39%,初級通暢102例,占比為83.61%。早期失功組患者年齡、糖尿病患者占比、血小板計數、血清C‐反應蛋白、總膽固醇、血磷、全段甲狀旁腺激素均顯著高于初級通暢組,頭靜脈直徑、橈動脈血流量、頭靜脈血流量、束臂后頭靜脈直徑及束臂后頭靜脈血流量顯著低于初級通暢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初級通暢組和早期失功組患者一般情況、臨床指標及術前內瘺彩超參數比較(±s)

表1 初級通暢組和早期失功組患者一般情況、臨床指標及術前內瘺彩超參數比較(±s)
項目 初級通暢組(102例)早期失功組(20例 ) t/χ2值 P值年齡 (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歲 ) 58.62±9.51 68.02±11.71 3.886 <0.05女性[例(%)] 54(52.94) 9(45.00) 0.422 >0.05糖尿病[例(%)] 48(47.06) 18(90.00) 12.417 <0.05高血壓病[例(%)] 71(69.61) 17(85.00) 1.971>0.05血小板計數(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109/L)187.00±51.00 216.00±69.00 2.186 <0.05血清 C‐反應蛋白(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g/L) 2.38±0.06 10.31±4.60 17.708 <0.05總膽固醇 (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mol/L) 4.04±1.26 4.89±0.96 2.855 <0.05血磷 (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mol/L) 1.61±0.41 1.94±0.42 3.278 <0.05血清全段甲狀旁腺激素(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pg/L) 414.51±87.89 507.02±102.09 4.190 <0.05橈動脈直徑 (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m) 2.29±0.78 2.38±0.66 0.483 >0.05橈動脈血流量(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L/min) 301.88±57.99 119.33±57.67 12.884 <0.05頭靜脈直徑 (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m) 2.37±0.89 1.90±0.78 2.200 <0.05頭靜脈血流量(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L/min) 145.23±38.23 107.76±27.09 4.176 <0.05束臂后頭靜脈直徑(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m) 3.02±0.99 2.11±0.39 4.039 <0.05束臂后頭靜脈血流量(images/BZ_9_1464_935_1486_966.png±s, mL/min) 235.23±32.43 167.89±31.12 8.545 <0.05
2.2 初級通暢組和早期失功組患者動態血壓監測參數 與初級通暢組比,早期失功組患者24 h SBP、24 h SBP SD、24 h SBP CV、非杓型血壓患者占比均顯著升高,而夜間SBP、DBP下降率均顯著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 2。

表2 初級通暢組和早期失功組患者動態血壓監測參數比較
2.3 術后1年內瘺通暢率 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術后通過電話、微信及門診復診方式定期隨訪1年,應用K‐M法繪制術后1年內瘺通暢率曲線,采用log‐rank檢驗進行比較,早期失功組1年內累積通暢率為0,初級通暢組1年內累積通暢率為85.29%,初級通暢組1年內通暢率顯著高于早期失功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3.67,P<0.05);122例患者中,3個月內初級通暢率為83.61%,1年內通暢率為71.31%,見圖1。20例早期失功組患者,其中2例腦血管意外死亡,2例心肌梗死死亡,2例急性心力衰竭死亡,5例血栓形成,4例內瘺吻合口狹窄,5例流出道狹窄。

圖1 術后1年內瘺通暢率曲線
2.4 血透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影響因素 以內瘺早期失功為因變量,以年齡、糖尿病、血小板、血清C‐反應蛋白、總膽固醇、血磷、iPTH等為自變量,進行多變量Cox回歸分析,結果顯示,C‐反應蛋白水平升高、術前頭靜脈直徑降低、非杓型血壓、24 h SBP SD升高均為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危險因素,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RR= 2.245、3.334、3.567、3.412,均P<0.05),見表 3。

表3 影響血透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多變量Cox回歸分析
3 討論
目前,動靜脈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率仍較高,血液透析患者治療的重點仍然是保護自體動靜脈內瘺的功能及延長其使用壽命[9]。相關研究顯示,動靜脈內瘺術后3個月、半年及1年內瘺通暢率逐漸下降,與本研究結果基本相符[10]。動靜脈內瘺形成術后,由于氧化應激、組織缺氧、血流動力學紊亂、內皮細胞損傷等的影響,從而引起血管重塑(血管向外擴張和/或靜脈動脈化)失敗是早期失功的主要原因。
相關臨床研究顯示,動態血壓監測可較為準確和全面地評估慢性腎臟病患者的血壓狀態,預測患者心腎的不良預后[11]。血壓變異性是高血壓患者靶器官損害的危險因素,而收縮壓變異性(SBP SD)、舒張壓變異性(DBP SD)是反映血壓變異性的主要指標。本研究中,與初級通暢組比,早期失功組患者24 h SBP、24 h SBP SD、24 h SBP CV、非杓型血壓患者占比均顯著升高,而夜間SBP、DBP下降率均顯著降低,提示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也受血壓影響,其原因可能在于,透析期間體質量增長率主要反映機體體液積聚情況,過多的水、鈉潴留可導致患者電解質代謝紊亂及體液失衡,從而使血壓變異性加重;SBP升高提示人體動脈內壓上升,從而導致內瘺靜脈同期內獲得較高的壓力沖擊,使患者靜脈微結構損傷加劇,不利于靜脈的緩慢性動脈轉化進程,影響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成熟,增加早期失功的風險[12]。
目前國內外研究認為,老年人(年齡>65歲)、吸煙、存在并發癥(糖尿病、冠心病)、貧血、低血清白蛋白、動脈硬化、透析中低血壓、透析后壓迫止血時間≥ 30 min、頭靜脈內徑<2 mm的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率較高[13‐14]。本研究中多變量Cox回歸分析結果顯示,C‐反應蛋白升高、術前頭靜脈直徑越小,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發生風險越高。其中,早期失功組患者頭靜脈直徑太小可直接影響內瘺血流量,繼而增加失功的風險[15]。同時多變量Cox回歸分析中,C‐反應蛋白水平升高為血透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影響因素,可能機制為血管壁炎癥狀態導致單核細胞及T淋巴細胞浸潤,引起內皮細胞損傷,繼而出現血管內膜不規則增生,導致內瘺狹窄[16]。因此,醫護人員應加強內瘺維護意識,定期監測相關實驗室指標,并及時調整用藥;同時,加強對患者及家屬健康宣教,提高其治療依從性。目前動態血壓監測相關研究表明,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壓晝夜節律改變,夜間血壓增高,大多呈非杓型血壓[17]。臨床研究顯示,非杓型血壓是終末期腎病患者靶器官損傷、心血管事件的危險因素[18]。本研究結果顯示,非杓型血壓為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危險因素,可能與血壓晝夜節律紊亂,產生波動的剪切力,導致血管內膜平滑肌細胞增生有關[19],升高的短時血壓變異性可致左室增大、收縮功能受損,并增加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而長時血壓變異性為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20],但目前尚無研究表明收縮期血壓變異性與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關系,本研究提示24 h SBP SD為血透患者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影響因素,目前機制不明,血壓變異性升高可能通過血液透析時循環壓力波動出現組織缺氧,并造成器官損害,并引起血管損傷[21]。在臨床中應及時給予患者合理的降壓治療,尤其針對非杓型血壓患者,降低24 h SBP SD水平,可降低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發生風險。
綜上,C‐反應蛋白水平升高、術前頭靜脈直徑降低、非杓型血壓、24 h SBP SD升高均為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危險因素,改善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炎癥狀態,降低24 h SBP SD,可降低動靜脈內瘺早期失功的發生風險,同時臨床需密切觀察術前頭靜脈直徑,以預測內瘺是否成熟。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小樣本,隨訪時間短,需要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延長隨訪時間,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