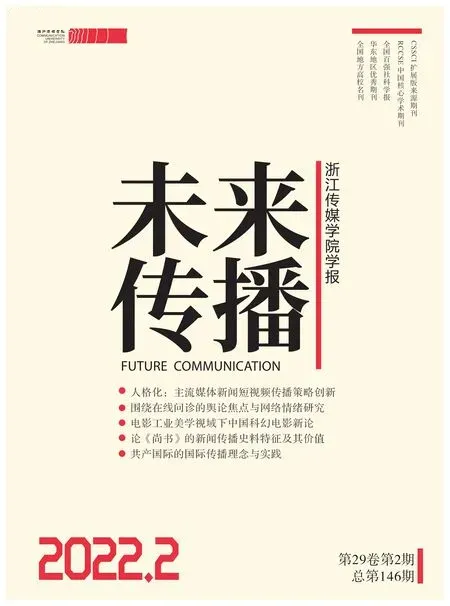主體、表征、交互:人類信息傳播的認知動力機制考察
李茂華
(成都大學中國-東盟藝術學院影視與動畫學院,四川成都610106)
20世紀中后期,認知科學興起并迅速成為顯學。認知科學是“關于智能實體與它們的環境相互作用的原理的研究”[1],其研究成果揭示了人腦及心智的工作機制。這為處于迷茫期的經典傳播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與切入點,促成了21世紀傳播學研究的認知轉向。
在經典傳播學研究中,“傳播”被賦予多重內涵,但其核心要素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傳播是觀念(意義或信息)的傳遞;傳播具有社會關系性;傳播借助“像”(符號)得到傳達;傳播是共享;傳播是說服;傳播是一種系統。傳播過程被概括為由傳播者、受傳者、訊息、媒介、反饋等要素構成的流程及相互關系的機制和系統。在認知科學興起之前,人腦及心智的工作機制無法得到理解與闡釋,傳播學研究偏向于“外視域”(即人與人、信息、媒介、環境等外部要素的關系域)的研究,而忽視“內視域”(即人腦、心智與各傳播要素交互影響的關系域)的研究,作為主體的“人”對傳播的影響無法得到透徹的理解。“認知傳播學以人為主體,以信息為工具,以傳播介質為橋梁,探究人的認知行為與傳播現象、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考察人的心智與大腦處理機制對信息傳播的影響,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地位在傳播學研究中得到突出。”[2]本文在認知傳播學的視野下,以認知哲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學、傳播學等研究成果為基礎,以認知為視角,在傳播關系域中,對傳播的核心要素——“主體”(包含傳播者與受傳者)、“表征”(信息的構成)、“關系”(傳播要素的關聯)等進行再審視,在“內視域”中探究人腦、身體與外部環境和信息生成之間的關系,以厘清人的認知機制與傳播之間的聯系。
一、認知主體:人類傳播活動的本質力量
在經典傳播學范式中,“傳播者”被視為傳播活動的起點,這起源于美國學者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拉斯韋爾是第一位提出傳播過程模式的學者,他的“5W”模式被認為開啟并引領了傳播學研究的五大領域。拉斯韋爾提出5W模式之時,傳播學尚未完成體系化工作,傳播學學科還未成立,拉斯韋爾的5W模式被認為厘清了人類傳播的構成要素與流程,成為傳播學過程研究的范式之一,并以之為基礎展開了控制分析、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和效果分析。拉斯韋爾模式所奠定的這一傳播過程模式,雖然抓住了人類傳播活動的幾大主要構成性要素,使人類傳播活動第一次得以系統化和動態化地呈現,但其中隱含的機械化方法論也帶來之后傳播學研究范式和框架的固化,即將傳播看成是從一端到另一端的線性的傳播過程,而沒有看到人的意識在傳播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人類傳播的本質力量被掩蓋。

圖1 拉斯韋爾的傳播過程模式
沿著拉斯韋爾的傳播過程模式,奧古斯德(Osdood)和施拉姆(Chramm)提出了循環模式,將傳者和受者都視為傳播主體,這無疑突破了拉斯韋爾的傳受主體二分化的藩籬,看到了傳播過程中傳播者和受傳者在對信息的接收、理解、再傳播過程中功能上的一致性。賴利(Riley)夫婦的系統傳播模式,則將人類傳播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大系統中進行觀察,看到個人與他人、群體、組織、環境等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此后,人類的傳播活動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中的運行得到多層面、多角度的深度闡發,人—訊息—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成為傳播學研究的重點。在此基礎上,傳播學者將人類傳播活動進一步分為并列的五大類型: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不同類型界分明晰,具有各自的內涵、外延與相應的研究范疇。這種劃分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質疑的主要焦點在于“人內傳播”是否能與其他傳播類型并列的問題。林之達認為:“這種劃分,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標準而犯了‘子項相容’的邏輯錯誤。”“因為,任何傳播都必須把傳播內容或者轉換成相應的聲音信號通過對象的聽覺器官作用于其大腦,或者轉換成光信號通過對象的視覺器官作用于其大腦,或者將表征傳播內容的詞的符號(文字)轉換成光信號通過對象的視覺器官作用于其大腦,或將傳播內容轉換成兩種以上的信號通過兩種以上的感覺器官作用于其大腦。因此,傳播科學從這四類傳播中揭示出的特點、規律,可被任何傳播活動者用來進行旨在提高傳播效果的策劃……”[3]
林之達“任何傳播內容都必須轉化為人的感官可感知的信號(表征)作用于人的大腦”的觀點揭示出人類傳播活動的認知本質,對之前傳播過程、傳播類型的研究有一個糾偏的作用。但在當時,盡管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人的心智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仍然是個未解之謎,其成果還不足以促成傳播學研究的認知轉向。林之達認為:“傳播學界當務之急還是集中力量研究社會傳播,……即使有必要研究‘內向傳播’,從研究策略上考慮,也宜先借鑒認知心理學家在人體內信息過程方面的研究成果。”[3]
認知心理學家試圖揭示人的心智工作之謎。1868年,荷蘭心理學家弗朗西斯科·唐德斯(Franciscus Donders)的系列實驗拉開了認知心理學研究的序幕。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于1890年出版了《心理學原理》。在這本書中,他提到了思維、意識、注意、記憶、感覺、想象和推理等與認知有關的觀點。1938年,美國學者愛德華·托曼(Edward Chace Tolman)在迷宮實驗中提出了“認知地圖”的概念。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同年召開了麻省理工學院信息理論研討會,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認知科學的誕生。1967年,烏爾里克·奈塞爾(Ulrich Neisser)出版了《認知心理學》一書,“強調利用信息加工的方法研究心智”,這標志著認知心理學的正式誕生。認知心理學經過系列實驗認為,心智構建并控制著個體的心理能力(如知覺、注意和記憶等),同時心智還能構建個體對世界的表征,使我們的人體機能得以運轉。[4]
19世紀,腦科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揭開了大腦的組織構成及其與心智產生的關聯。大腦中的神經元以及不同的腦區具有表征外部刺激并做出反應的功能,腦與身體共同構成了心智產生的物理基礎。當外部刺激引起人的感官注意,經感受器進入人體后,會被知覺系統加工,知覺加工受主體狀態(需要、動機、經驗、記憶、情緒等)的影響,在此階段會有知識的參與,經知覺加工后的刺激再輸出時具有新質特征。這一體內傳播過程,是提升人類傳播活動傳播效果的關鍵環節,是其他傳播活動的前提和基礎。
在當前的腦科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了人的心智對傳播效果的影響。首先,注意機制控制著傳播內容的到達性。我們處在一個信息極度發達的社會,而與此相對的是人的注意力的稀缺,如果我們生產的信息不能引起主體的注意,那么將無法進入體內感知系統進行認知加工,傳播活動即終止。而研究證明,“人體的信息視覺處理首先是從二維的圖像陣列中獲取最基本的圖像特征,如色彩、亮度、紋理和分布等。人體感官最容易對色彩鮮艷、高亮度、運動狀態等信息首先產生注意”。[2]這些研究成果給了我們提升注意力效果的啟示。其次,知覺加工影響傳播內容的接收與理解。知覺首先依據整體性原則對進入人體內部的信息進行識別,也就是說我們僅窺知信息的部分成分就能反應出該信息,但很多時候我們在識別信息時調動了經驗、情境以及反饋信號等。信息越符合我們的經驗,我們對其越容易識別;信息處于一定的情境中,我們更容易識別;我們的知識及期望的反饋信號會影響我們對信息的處理。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的傳播內容,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受眾的經驗以及知識結構的情況下,能夠獲得最大的傳播效果;在配合一定情境傳播的情況下,更容易被識別。由此,基于受眾的經驗不同、知識結構不同,我們可以更精準地設計分眾傳播策略,同時結合受眾感覺處理的特征,對傳播形式及內容進行優化;傳播內容的設計更多以情境傳播為主,避免空洞的說教。當然,知覺加工還受到個體需要、動機、情緒的影響。越是為受眾所需,其接收信息的動機就越強,進行知覺加工的效果就越好。在知覺加工過程中,正情緒的接受效果更好,負情緒反之。再次,記憶影響傳播效果。“記憶是指在初始信息不再呈現的情況下,保持、提取或使用這些信息的加工過程。”[4](148)記憶分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長時記憶包括情景記憶——有關特定經歷的記憶;語義記憶——對事實的記憶;以及程序性記憶——對于如何做事情的記憶。”[4](192)情景記憶會帶領我們以想象的方式重回過去某個場景,搭建現在和過去之間的聯結。語義記憶偏重于語詞、概念、命題等知識。程序記憶涉及技能。記憶對傳播效果無疑具有重大影響,當我們的傳播內容激起受眾某個記憶情景時,無疑會激發他的相關情緒情感,再次給予他對該信息的理解;知識類節目會激發受眾的語義記憶,越符合記憶內容,收到的傳播效果越好;程序記憶對傳播者的技能有影響。
心智對傳播效果的影響無疑是重要而有力的。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等其他傳播活動,都要以人內傳播為基礎,“人內傳播”與其他傳播類型并不構成并列,而是其他傳播活動的前提和基礎,它伴隨著這些傳播過程的始終。只有具有認知能力的主體(人),才是傳播活動的本質力量。
二、表征:人類傳播活動的認知中介
傳播從本質上說,是具有認知功能的個體在與外部環境不斷地互動、交流過程中出現的信息的流動,它既包括個體的自我傳播,也包括個體與外在環境互涉的體外傳播。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傳播,表征都是傳播得以進行的中介。
大腦具有對世界進行表征的能力。認知心理學認為:“個體所覺察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在大腦中被表征的。”[4](46)比如我們能夠看到一棵樹,是因為這棵樹的反射光線進入了我們的視覺器官,并使樹的影像會聚在我們的視網膜上,而這棵會聚在我們視網膜上的“樹”并不是樹的本身,而是“樹”的表征。也就是說,我們所認識的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經由我們的感知覺系統,在我們大腦中形成的“表征”,而并非這個世界本身。由此,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所有認知,都建立在對“表征”的認知和處理上。
格拉斯(Snodgrass)將“表征”看作是“信息記載或表達的方式”“表征代表著相應的信息。”[5]鑒于表征在人體內部和外部“記載與表達信息方式”的不一致,我們分體內系統和體外系統兩個部分來分析“表征”。
在體內傳播系統,表征是外部世界的信息經由人體感官系統在人腦中的映射,這種映射借助神經元活動得到實現。當外部刺激進入感官,會激活特定的神經元(通常是一群神經元),這些神經元通過放電實現對該刺激的表征。如“樹”的表征,是借助了視覺神經元——視網膜而得以實現。當人在客觀環境中遭遇不同的信息刺激,就會激活不同的神經元放電,從而引起人們對這些信息刺激作出反應。因此,表征是人與這個世界建立認知聯系的中介,是人的認識產生的來源之一,它依附于人腦這個器官,并指導人從事信息實踐活動。
在體內傳播系統中,表征一方面作為外部世界信息(可能是客觀的,也可能是主觀的)在頭腦中的映射,另一方面也是大腦對其進行知覺加工的客體。當外部信息進入人的感官閾限后,經過感知覺形成表征,這些表征會在知覺過程中遭遇編碼、轉換等加工處理,部分表征會以多種形式儲存在知識結構塊中,形成記憶,當新的信息進入人腦,表征會被提取以和新信息進行比對,從而完成對新信息的認知加工,還有部分表征會以新信息的方式通過人的感官系統并借助語言等符號輸出人體。
表征的形成源自人的實踐。人通過勞動、學習、交往、思考等多種實踐活動,在不斷地接觸新信息與交流新信息的過程中,建立起心智對世界的表征系統,這套表征系統以記憶的方式被儲存,并在人的一切活動中起作用。以人類傳播活動而論,世界在人腦中建立了一套表征系統,形成人對世界的認知,為了便于人類傳播思想、促進發展,人類發明了語言、文字、圖片、影像等符號系統,以將認知客觀化與對象化,從而創設了一套體外表征系統。體外表征與體內表征并非一一對應,如“樹”,作為客觀存在物的“樹”在大腦中形成“樹”的表征,而人類為了表達對“樹”的認知,創設了多種表征形式:有視覺形式,如繪畫、照片中的“樹”;有概念形式,如詞典中“樹”的解釋;還有文字、聲音、影像等形式,無論哪一種表征形式,都會引起大腦內部相應區域的神經元放電,從而激活對“樹”的識別和闡釋。因此,傳播過程是世界(信息)以光、電、聲音等信號進入人體感知系統,在神經元活動的作用下,以表征形式進入體內傳播,在知覺系統加工下,一部分信息被拋棄,一部分被存儲為知識,一部分形成新的信息再經感官輸出體內系統,從而開啟體外傳播。體外傳播再借助人類創設的一套體外表征系統,將人對世界的認知(思想、知識等)通過體外表征系統進行傳播,促進人們思想的形成或改變,從而認識和改造世界。表征構成人類傳播活動的認知中介。
人類的體外表征系統豐富而復雜。馬爾(David Marr)在《視覺》一書中,把表征看成“一種能把某些實體或某類信息表達清楚的形式化系統,以及說明該系統如何行使其職能的若干規則。”[5](8)按照這種理解,表征具有兩種意義:一是描繪、說明對象,使之喚起人們頭腦中的印象;二是表征的方式,即用何種方式去喚起。前面提到的“樹”的表征,用圖片、用文字、用影像,分別是不同的表征方式,但是同樣能喚起人們對樹的印象或闡釋。實際上,體內表征,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存儲,有形象化的、有概念化的、有命題式的,還有其他抽象形式,在體外表征的詢喚下,其形象或意義才得以迅速彰顯。人類在歷史進程中,在不斷地交流、對話、實踐的過程中,其表征體系也在不斷地演進,先后形成完備的語言符號體系、文字符號體系、影像符號體系等,成為人類交流思想、認知世界的具有社會規約性的工具;同時,人類創造的繪畫、雕塑、建筑、園林、音樂等藝術,乃至人類實踐活動的其他對象物,都在自己的體系內,構成人類思想的某種表征。
發生認識學認為,心智的產生是腦—身體—環境三者耦合的動力系統的有機產物,表征作為心智產生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也是在這三者相互耦合的動力系統的作用力下產生的。我們對體內表征的考察,在某種程度上部分回應了“腦”“身體”在心智產生中的作用,部分回答了胡塞爾(Husserl)無法解釋的意識的產生及涌現問題,但環境對表征形成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察。
表征作為人類傳播活動的認知中介,是認知客體(對象)的代表和指示物,正因為如此,認知主體(人)才可以通過表征(符號)實現對客體的主觀化把握,從而實現客—主關系向主—主關系的轉換。比如“樹”,如果沒有表征的存在,認知主體與樹的關系,將表現為“身體”的認知主體與“樹”的客觀存在體之間的關系,主體必須面對客觀存在的“樹”才能產生認知;當“樹”的表征產生,主體對“樹”的把握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對脫離主體的身體活動與樹的“存在”,而在觀念中進行認知把握,正是這種觀念化的把握的可能,才產生了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大眾之間的思想交流,從而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對表征的理解,不能僅將其視為“客—主”關系結構中的存在,而應進入到“主—主”關系結構域中進行考察,表征無論是作為描述性的指示物或代表,還是作為喚起認知的方式與工具,它都是在多極主體中被建構的。表征的意義一旦在多極主體中形成通約性,就會以知識結構塊的方式儲存,并先在地支配認知主體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與實踐方式。當然,表征所包含的意義,也并非一成不變,它在主體的多極交往活動中,也呈現出流變的特征,這也是“主—主”關系域張力的表現之一,同時,也是人類傳播活動生生不息、動態發展的特征之一。
三、交互:人類傳播活動的認知動力機制
在經典傳播學研究視域中,“傳播”包含了以下內涵:傳播具有社會關系性;傳播是共享;傳播是說服;傳播是一種系統。這種“外視域”視角,更多是將人放在外部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而忽略了人的“認知”對傳播所起的作用。傳播者作為傳播的起點,他所傳播的“訊息”是如何涌現的?信息從接收到輸出體內的過程中,有無發生變化?不同的受傳者對信息的接受程度為何有區別,是什么在影響受傳者對信息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關于“心智的涌現”問題,早期哲學已經開始探討,最早可追溯到笛卡爾(Descartes)。笛卡爾認為:心靈與身體是兩種獨立的實體。他承認心靈與身體有交互作用,但堅持認為心靈實體不能還原為物質實體。現象學家胡塞爾(Husserl)將“存在看作是意識的相關項(Correlatum),看作是合乎意識的‘被意指之物’”“研究的方向必須朝向一種對意識的科學本質認識,朝向意識本身在其所有可區分的形態中按其本質之所‘是’的東西,但同時也朝向意識所‘意指’的東西,以及朝向那些各種不同的方式,意識便以這些方式,……意指著對象之物,并且有可能將它‘表明’為‘有效’‘現實’的存在之物。”[6]在胡塞爾看來,存在與意識相關,是意識的“意指之物”,研究應該朝向“意識”“意識的意指”以及二者的中介“這些方式”。胡塞爾的觀點后來在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實驗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證實,但“意識”存在在哪里,以何形態存在,“這些方式”又是什么,它如何使“意指對象”得到“表明”,也就是“意識”的存在及其涌現問題,胡塞爾也無法很好地解釋。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引入了“身體”概念,認為“我們認知結果的意義……與我們實現認知活動的基本的身體圖式、行為結構和生理神經結構有關。”[7]這成為具身認知論的哲學基礎。20世紀,建立在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基礎上的新物理主義肯定了“身體”對認識的介入。但也有知識論者認為物理方式無法解釋人類的獨特意識經驗。那么,人的意識及意識經驗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人的身體的物理結構和人的意識及意識經驗,又是否影響了,或者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在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
19世紀末期,一些心理學家開始嘗試研究心智,成為認知心理學的先驅。1868年,荷蘭心理學家唐德斯(Franciscus Donders)的“反應時”實驗,揭示了通過行為反應推測心智的方法。[4](5)1885年,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發表《論記憶》,認為“記憶”也可以用來描述心智的某種屬性——保持心智的能力。[3](8)之后,隨著認知心理學研究的推進,認知科學研究歷經了符號主義、聯結主義等發展階段后,第二代認知科學提出具身的認知觀。1991年,具身認知觀的代表人物瓦雷拉(Varela)、湯普森(E.Thompson)和羅施(E.Rosch)首次將“生成”(enactment,bringing forth)概念引入認知科學,“提出生成認知研究的三個主題:(1)具身性:人類的心智不是局限在頭腦中,而是擴展到整個生命機體和生命機體賴以生存的環境;(2)涌現:有機體的認知是腦—身體—環境互惠作用的動力自組織的涌現;(3)內我—他者的共同決定:個體的心智不是孤立地出現的,它不但嵌入在生物環境中,而且嵌入在人際的情境(interpersonalcontext)中。”[8]20世紀晚期,認知神經科學家們利用事件相關電位(ERP)、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高速計算機和強大的電子顯微鏡等高科技工具,對大腦內部的神經機制進行了掃描,大腦的功能及運作機制以及心智的產生原理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科學的闡發。認知神經科學經過實驗證實:構成大腦的物理結構與認知的產生密切相關。如基底神經元、丘腦底核、黑質以及皮質、丘腦協同合作,共同調節運動控制功能(包括軀體運動和眼球運動)以及某些認知功能。[9]下丘腦會參與到一些情緒過程中并控制與其底部相連的垂體。[9](70)
上述研究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智”產生的基本條件:腦、身體的物理性存在,以及腦—身體—環境三者耦合的動力系統,這個“動力系統”的存在,是人體信息攝入、加工、處理、傳播的奧秘所在。腦組織構成了信息攝入、加工、處理、傳播的物理基礎;身體作為豐富而真實的環境中的身體而介入認知系統;人的認知產生于環境與腦、身體的交互,并與人自身的生存、發展緊密相關。處于環境中的腦與身體的交互,使人產生了意識(基于物理系統的腦內世界模型[10]),而“意識”的涌現,才使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成為可能。
關于人類認知傳播的動力模式,如圖2所示。

圖2 人類認知傳播動力模式圖
由此再回到“人內傳播”的概念,“人內傳播”并非是一個封閉的自循環系統,而是作為生命有機體的人在與自身及外部環境不斷地互動、交流過程中實現的信息的傳播過程,它在生生不息地、動態地、不斷地自我創生著。這正是人類意識產生、生產信息、傳播,再作用于自身及社會的內在不竭的動力源泉。
四、余 論
20世紀末期,傳播學者對傳播學研究日益走向僵化的質疑,對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傳播”而暫緩研究“內在傳播”的呼吁,在認知科學已經發展到第二代具身—嵌入式認知、延展認知、生成認知的當下,在腦科學、人工智能、認知神經科學、認知哲學已取得諸多成果之時,可以進行重新的思考和論辯了。我們也看到,自2004年以來,中國的認知傳播研究已邁入理論自覺期,相關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以成都大學傳媒研究院歐陽宏生教授為代表所做的“認知傳播學學科體系建構”工作,和以北京師范大學喻國明教授為代表所開展的“認知神經傳播學”研究,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4年,中國認知傳播學研究會成立,并每年召開年會,共同就認知傳播相關問題展開研討,由此帶動一大批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投入認知傳播的研究,這是一個向好的趨勢。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當前的認知傳播研究還需要更深入、更寬廣地展開:一是認知傳播本質內涵的研究進展緩慢。當前的認知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雖部分揭示了大腦和心智的工作機制,但能對人類傳播活動構成理論和實驗支撐的成果還不多,認知傳播研究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方法論,利用先進的技術和相關工具,去開展人類傳播的認知研究,揭示主體的需要、動機、經驗、情緒、知識、記憶等心理狀態與身體狀態在傳播中的活動機制,揭示傳播的內在動力機制,以更好地實現傳播效果。二是認知傳播的外部關系研究可以更寬廣地展開。在跨學科的視野融合下,認知哲學與傳播學、認知符號學與傳播學、認知語言學與傳播學、影視學與認知傳播學等在學科跨界中將會開拓出一片新的學術藍海。本文對傳播內涵中的“主體”“表征”“交互”三個關鍵詞從認知視角進行再考察,揭示出人類信息傳播認知動力機制的三個要素(腦、身體;腦—身體—環境的交互;表征)。正是腦—身體—環境三者耦合的動力系統促使意識形成,進而使人類信息傳播得以開始,具有認知能力的主體(人),才是人類傳播活動的本質力量。這只是認知傳播本質內涵研究的一個小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