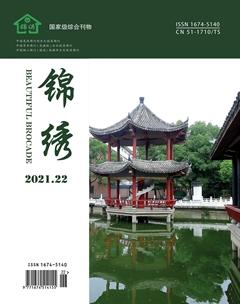核心素養視角下高中地理課堂教學提問策略探析
陳能
摘要:在教育領域,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各學段學生發展核心素養體系建設規劃,以此與當前的政治經濟發展相符合。而高中生地理課堂是高中生提升人地協調觀、綜合思維能力、區域認知能力以及地理實踐的能力的必經之路,同時是中學生地理學科綜合素養教學的主要陣地。本文將從核心素養相關的理論出發,結合初高中生的心智發展特征,對中學政治地理課堂提問的策略進行綜合分析。
關鍵詞:核心素養;中學;政治地理課堂;提問
引言
當前,廣大的高中生在此情形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的接受心理、學習習慣、知識經驗等方面的特征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傳統的灌輸式教育方式已經難以適應高中生對于地理課堂參與、互動的需求。而課堂提問是增強師生互動和活躍課堂氛圍的必經之路,也有利于是讓學生在提問的過程中增強培養發展人地協調觀、綜合思維、區域認知、地理實踐力的地理核心素養。
一、高中地理核心素養和課堂提問概述
地理核心素養是素質教育模式下的產物,是對學生全面發展與針對性培養的矛盾統一體,同時也是不同學科與素質教育目標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在高中地理學科教育中,地理核心素養在具備學科上述的一般性素養的基礎上之外,其還具其獨特性有自身獨有的素養,其中主要包含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三個方面的內容,具體而言就是人地協調觀、綜合思維、區域認知、地理實踐力這四個方面的內容。
廣義的課堂提問是在教育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之間提出的問題和回答,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雙向互動機制。其中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提問的主體是雙向的,回答的主題也是雙向的;第二層含義是課堂提問也包含學生之間的提問與相互討論和回答。從課堂提問的關系上而言,課堂提問是由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根據教學內容、教學目標,教師提問或者是引導學生提問的過程,其目的旨是在課堂提問的過程中提升學生的多方面素養。
二、核心素養視角下高中地理課堂教學提問策略
(一)重視深度地理課堂提問,提升高中生區域認知力
在具體的高中地理課堂中,教師要首先了解核地理心素養的具體內容與要求,根據不同內容的課堂進行不同提問方式與內容的設置,全面提升對政治地理課堂的提問的重視度。首先,作為高中地理課教師,將核心素養中發展學生的學科素養能力融入其中應將對學生地理核心素養的培養融入日常教學之中,在課堂開始前做好提問發生與提問內容的界定,所有的提問都要以促進學生的學科素養為出發點,循序漸進地提升問題的深度,讓學生在提問中提升區域認知的能力。比譬如,在高中地理課堂中,教師在提問某一位學生關于“溫帶大陸性氣候的分布特征”問題時,應根據學生的回答,教師循序漸進的提升問題的深度,將淺層問題引向對我國新疆、甘肅、內蒙古等區域的深入分析,將氣候與當地的生活環境、人物性格等方面延伸思考,增強學生對地理區域認知的分析能力。
(二)提升提問策略和技能水平,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地協調觀
作為一名高中地理課教師,要從多個角度提升自己課堂提問技能和水平,可以通過閱讀杜威、布魯納、皮亞杰、維果斯基、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的理論著作,不斷地從中吸取優秀成分,并將其運用與自身的課堂提問之中;其次,還可以廣泛的研究本班級內學生的接受特點,將針對集體的提問方式與針對個體的提問進行融合。比譬如,根據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高中生大多數已經處于形式運算階段,已經具備了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并綜合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教學理論,對于平常喜歡國際評論的同學而言,世界范圍內的環境保護、區域智力、人類活動等方面的國際新聞與地理課堂提問相聯系,積極引導學生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并在人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中樹立環保、低碳、愛護環境的價值觀,成為和諧世界的建設者,這有利于培養學生的人地協調觀。
(三)激發學生質疑與應答的勇氣,促進綜合思維能力發展
在具體提問過程中,教師要發揮引導功能,充分挖掘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全面激發學生質疑與應答的勇氣。比如,教師可以采用工作坊的教學方式,進行小組化的提問,以群體提問的方式提升部分學生的怯場行為,讓學生在討論中敢于發言的同時,樹立集體觀念,并通過具體的問題引向整體、全面、系統和動態的地理分析方法之中,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思維能力。比譬如,教師引導各個小組的同學對臨近的小組進行提問,分析水水土流失的高發區域以及原因時。,可以讓學生在集體提問中暢所欲言,并最終通過教師歸納引導,讓學生理了解水土流失與當地的植被分布、人類破壞、氣候、和地形、土壤性質等方面的有著深刻聯系,以系統、整體的方法進行分析,讓學生在自由大膽的提問中提升自己的綜合思維能力。
(四)加強學生對地理課堂的興趣,培養地理實踐力
在增強學生對政治地理課堂的興趣實踐中,核心素養中既有知識的學習,也有情感態度的參與,也有分析方法與邏輯思維的培養。而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提升學生主體參與課堂學習的必經之路。在具體的提問過程中,要以教材為以及教學大綱規范出發,要適當的豐富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引創設出多樣化的提問情境。比譬如,高中地理教學科研的開展可以與當地的規劃館、地質博物館進行的合作教學,讓學生走出教室,進行實地調查,在具體的情境中設置實踐性問題,提升學生的地理實踐時間能力。其次,也可以組織學生到實地進行考察,參與研學旅行活動等形式。,在具體的主題活動中,教師可以設置關于地理環境調查、戶外考察和實驗中的問題,以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同時,培養學生的地理實踐力。
三、結語
綜上所述,核心素養視角下的高中地理課堂提問是從教學到學習,從教師的主導與學生的主體的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價值觀、態度價值觀等多方面素養進行縱橫交錯的有機整體。高中地理課堂的提問是促進中學生核心素養發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具體的實踐中,只有將教師的提問策略以及學生主觀能動性相結合,重視深度地理課堂提問,提升高中生區域認知力;不斷地提升提問策略和技能水平,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地協調觀,在提問過程中激發學生質疑與應答的勇氣,促進綜合思維能力發展,;加強學生對地理課堂的興趣,培養地理實踐力等四個方面為核心,有利于最終為提升中學生的地理核心素養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熊平生,竇文濤. 高中地理教師課堂教學行為研究[J]. 教學與管理,2017(12):114-117.
[2]王琛. 基于地理核心素養的高中地理課堂教學提問研究[J]. 教育現代化,2017,4(31):149-150.
[3]王婉霞. 核心素養導向下問題驅動教學模式在高中地理課堂教學中的實踐[J]. 西部素質教育,2019,5(24):65-66.
[4]魏巍. 高中地理教學中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以“大氣的受熱過程”為例[J]. 科學咨詢(科技·管理),2020(09):3-4.
[5]劉衛. 高中地理課堂檢測性提問研究與實施策略[J]. 地理教學,2016(08):25-27.
(寧波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文化學院 浙江省 寧波市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