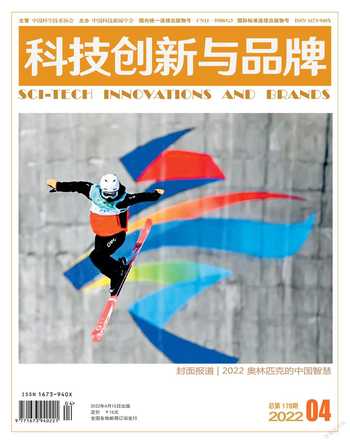葉國安:初心不忘馭核以和
高妍 喬占衛
“核能有些像馬戲團里的猛獸,聽話時讓人感到其樂無窮,而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設想。”瑞典核物理學家帕克金森曾如此比喻核能。作為人類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核能的發現和使用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人類欣喜核能帶來的超強能量,也畏懼核廢料可能導致的放射性災難。
面對優點與缺點同樣突出的核能,普通人大多關注其缺點,談核色變,唯恐避之不及,科學家卻更看中它的優點,并堅定的與核為伴。他們拆解、分離、研究核的每一個元素與功能,只為了在充分規避核能缺點的前提下最大化發揮它的優點。中核集團首席專家、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葉國安,就是這樣一位馭核人。
葉國安長期致力于錒系元素化學與后處理工藝技術研究,在镎、钚化學行為與后處理工藝過程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已獲得多項國家科技進步獎。
后處理,最難的分離過程之一
乏燃料即用過的核燃料,由核電站的核反應堆產生。乏燃料可不是常規概念中的核廢料,葉國安稱之為“富礦”。
葉國安解釋,用過的核燃料里既有大部分沒有用完的鈾,又形成了很多高價值的其他元素,是名副其實的資源。“核電站用過的核燃料僅僅消耗了原料鈾的4%~5%,絕大部分鈾沒有用完,如果棄之不用太浪費了。并且,消耗掉的鈾大部分會裂變成幾十種裂變產物元素,一小部分會吸收中子生成更高質量數的超鈾元素,如93號元素镎、94號元素钚,這是比鈾更好的核燃料。”這對于鈾資源并不豐富的我國來說正是雪中送炭,而后處理則是將這一“富礦”充分挖掘出來的有效手段。
核燃料后處理是分離鈾、钚以及镎、镅、鋦等錒系元素的復雜化學化工過程。通過后處理,可將乏燃料中的鈾和新生成的钚等元素回收并利用,不僅可以豐富我國鈾資源,確保我國核電進一步規模化、自持式發展,還可大大減少乏燃料放射性物量,降低其長期潛在危害。
在我國核燃料循環體系中,后處理是實現核燃料閉式循環的關鍵環節,是一項融合了高、精、尖的復雜技術,難度非常高。如何難?葉國安指出,后處理的難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難,化學分離難。
在周期表第7周期,錒系元素只占據其中一格。但僅這一格,就包括了15個化學性質非常相似的元素,“這些元素就像一個元素似的,因此分離純化相當困難”。葉國安介紹,“錒系元素分離的要點是其價態調節與控制,特別是镎、钚的價態調節與控制。因為镎、钚都是典型的變價元素,钚有III、IV、VI三種價態,镎有IV、V、VI三種價態,不同價態可以共存,在輻射場中精確調整并控制在某一個價態很困難。”此外,分離中還要考慮到輻射與試劑相互作用對分離的影響等。“說后處理是最難的一種分離過程,恐怕也不為過。”
第二難,實現設備高可靠性難。
后處理是把放射性元素“打開來”操作,放射性強,對關鍵設備要求很高,不僅要求高自動化水平,還需要高可靠性,最好免維修。這對于設備臺套數達到20余萬的后處理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三難,技術集成和穩定運行難。
后處理本身就是一個流程化工廠,物流組成復雜、各成分之間差別大、物流形態和放射性差別大,導致相應的處理工藝、操作手段、防護要求不一樣,所以它的設備很多。可以說,后處理是一個各種高端裝備、檢測與控制技術高密度集中使用的場所,如何集成匹配、優化運行至關重要。
這是開展后處理工作的難點,也是葉國安30多年攻關的重點。
葉國安學放射化學出身,1986年被分配到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一來就分到后處理室,叫做錒系元素化學與工藝研究室”。
上世紀80年代,軍工科研艱難,經費少,人員流失嚴重。好在有一批老同志兢兢業業的堅守,葉國安就是在王方定院士等老一輩科學家帶領下一步步入了后處理的門。
在葉國安從新兵成長為老將的30多年里,我國的后處理水平也逐步提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研究條件有了改善,建成了核燃料后處理放射化學實驗平臺;建成了核電站乏燃料后處理中試廠 ,從軍用后處理轉到核電站乏燃料后處理,放射性提高兩個數量級、鈾钚分離凈化指標也相應有很大提高,技術有了很大改進;分析檢測技術取得了很大進步,安全監管要求也比過去更加嚴格”。
這其中,有一項與葉國安領導的團隊密切相關,那就是核燃料后處理放射化學實驗平臺CRARL的建設。
CRARL平臺,一座開啟未來的方舟
2021年11月3日,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核燃料后處理放化實驗平臺設計建造關鍵技術及應用”項目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項目第一完成人葉國安代表團隊領獎。
核燃料后處理放化實驗平臺,即CRARL,是為適應我國核能進一步發展與核燃料循環體系建設打造的一個綜合性科研平臺,可用于開展后處理熱實驗及放射化學研究等。
CRARL的建成令人振奮,“可以做熱實驗了,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葉國安介紹,“后處理工藝技術研究有一個規律,先做分離的小實驗,一般稱為試管實驗,研究基本分離機理、分離條件;然后把很多元素加在一起,類似于乏燃料的組成,但是不加放射性的核素,做分離工藝研究,每個工藝段都這樣做;最后再把全部工藝段連接集成起來,用真實的乏燃料做熱實驗驗證和改進。”
此前雖有可以開展后處理工藝研究的實驗室——46-戊工號,但它輻射防護等級不夠,設備老化嚴重,無法開展核電站乏燃料后處理的化學與工藝熱實驗。因此在CRARL建成之前,相關研究只能做前兩個階段,最后一個階段的熱實驗始終無法開展。
但是,全流程熱實驗又是驗證工藝研究真實性的關鍵步驟,必不可少。“當時印度都可以做,出去開會他們的研究報告水平比我們的要高出一大截。法國、美國、日本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建有非常完備的實驗設施,功能非常多,我們羨慕得不得了。”葉國安說,他們一直想建一個真正的后處理研究設施。
2003年11月,CRARL立項,此時的葉國安已經擔任放化所所長。在2000—2001年擔任室主任期間,他帶隊完成了“全流程集成及其臺架溫實驗”任務,積累了豐富經驗,滿腔熱情亟待揮灑。
這一干就是11年,CRARL平臺在2014年建成,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建筑面積近一萬平方米,熱室、工作箱增加很多,功能也比原來的多、各類實驗都可以做了,操作放射性物料強度比原來高出很多,對工作人員的保護和維修水平等也都上了一個臺階,可謂實現了后處理化學與工藝研究手段的跨越發展。”葉國安滿是自豪,“有了這個平臺,情況就改觀了”。
葉國安介紹,在這個平臺上,可以處理各類高燃耗乏燃料和輻照靶件;可以研究不同后處理方法和工藝;分離的元素不再限于鈾、钚,還可以提取多種元素或核素如镎、镅、鋦、鍶90、钚238等;還可以開展高溫熔鹽化學與干法后處理工藝研究;分析方法和放射性廢物處理方法的研究范圍也大大拓展。這是一扇門,我國先進核燃料循環后端技術的進一步研究從這里開始。
自2015年9月開始首次熱試驗,CRARL迄今已開展多次工藝熱實驗,取得了一系列原創性成果,先后完成多項重點研究任務,“其使用大大超出了原來的預期,為我國相關項目的設計解了燃眉之急,提供了急需的設計輸入”,取得了巨大的綜合效益。
現階段,開展任務型研發工作的同時,他們還在圍繞CRARL平臺開展深入研究,比如新后處理分離方法研究,進一步提高分離效率、縮短工藝流程,減少廢物量、提高后處理經濟性等;進一步分離多種有價值元素,如次錒系元素镎镅鋦和鍶90等;此外還進行后處理分析方法改進、廢物處理技術特別是冷坩堝玻璃固化研究等。
同時,葉國安領導團隊按照我國核能“熱堆-快堆-聚變堆”三步走戰略,“結合快堆開發新一代干法后處理技術,在快堆-干法后處理核燃料循環中實現循環時間更短,縮短提高鈾資源利用率的時間,為我國核能盡快實現更大規模發展提供技術保障。”
“兩條辮子三個攤子”搭建的組織力
后處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通力協作是開展這項工作的前提。以熱實驗為例,不提前期的基礎和分段研究,僅最后的集成實驗就是一項“大工程”。
實驗前要做好準備,包括乏燃料、設備、試劑和分析檢測方法的準備,安全方面的準備;實驗開始,需要整個工號高效運行,各方面配合,上千個分析樣品取樣、密封、遠距離傳輸,容不得半點差錯;實驗完成后,1600多個樣品要分析,取得工藝數據;最后還要廢物處理整備,“完成整個工作要大半年的時間,往往需要幾百人協同作戰”。每到這個時候,也是考驗葉國安這個領頭人組織能力的時候。
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葉國安總結出了“兩條辮子三個攤子”的管理方法。“辮子就是工藝和分析,攤子就是設備、設施、安全,分別指定負責人和助手各管一攤,再把老先生組織起來討論、把關。”這些經驗還是在“全流程集成及其臺架溫實驗”任務時積累下來的,后來不斷完善沿用至今。
同樣沿用下來的,還有錒系元素化學與后處理工藝研究團隊以技術需求為牽引的成長原則。“一個團隊要不斷有需求牽引,才有前進的動力。牽引我們這個團隊前進的,就是國家后處理事業的發展。”葉國安介紹,自“九五”至今,錒系元素化學與工藝研究一直都有技術研發需求作牽引,國家的需要就是團隊前進的目標。
在各級部門的支持下,團隊以任務帶學科,再以學科培養人才,逐步壯大至今。如今的原子能院錒系元素化學與后處理工藝研究團隊,已經成長為以首席專家和學科帶頭人為核心的200余人大團隊。基于CRARL平臺,團隊能夠開展大多數錒系元素的基礎研究、分離工藝與分析測量方法研究,以及放射性廢物處理技術研究等,在國內核燃料后處理領域獨一無二。
團隊成長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團隊的內部管理。錒系團隊注重學術氛圍培育,是一支以技術說話的團隊,以技術水平、技術能力優先,技術上不搞花架子,干工作實事求是、腳踏實地。
錒系元素化學與后處理工藝研究團隊還注重外部交流,包括國際交流。后處理是個應用性很強的大專業,從應用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工作讓葉國安獲益良多。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就帶領大家到工廠 、設計院、高校、科學院等單位交流,“接受他們挑毛病”。同時,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核燃料循環技術工作組專家,葉國安已參加多次專家年度會議,也帶領國內同行多次參加大型國際溶劑萃取、后處理、放射化學等方面的會議,積極參加中法后處理、中俄核燃料循環等方面的合作會談。“通過這些交流看看國際水平是怎么回事,對我們工作很有幫助”。
針對人們對核的恐懼、對后處理廠建設的“鄰避效應”心理,葉國安直言:“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后處理雖然是把放射性‘打開來’操作,但卻是相當安全的,現在的工程技術手段完全可以把放射性屏蔽起來并密封住,可以做到對操作人員、環境和生物圈沒有影響。而后處理廠 ,也會在技術上采取多種安全措施防止核臨界事故和其他事故。最重要的,后處理操作的核材料與爆炸裝置不一樣,它們不是緊緊篐縮在一起的,而是散裝或流動的,所以不會爆炸,也絕不會發生像原子彈甚至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那樣的核臨界爆炸事故。”
葉國安一再強調,后處理是一項切實有益于國家能源與經濟發展的技術,應該得到正確的認知與理解,而自己的團隊將會為這項技術的更長遠發展砥礪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