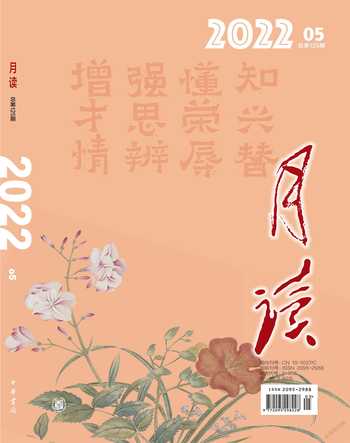敬姜論勞逸a
《國語·魯語下》
公父文伯退朝b,朝其母c,其母方績d。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e。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f?居,吾語女g。昔圣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h,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i,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j。少采夕月k,與大史、師載糾虔天刑l。日入,監九御m,使潔奉禘、郊之粢
盛n,而后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o,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p,而后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q,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r。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s,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t,蒸而
獻功u,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注釋:
a 敬姜:姜姓,齊國莒(今山東莒縣)人,齊侯庶出之女。據記載,敬姜嫁給魯國大夫公父穆伯為妻,生下公父文伯。她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之過,教以法理。
b 公父文伯:即公父歜,魯國大夫,公父穆伯之子。
c 朝:古時見君王曰朝,謁見尊敬的人也可以叫朝。 母:即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
d 績:紡麻。
e 干:冒犯。 季孫:即季康子,當時擔任主持魯國朝政的正卿。季氏是魯國的大族,敬姜是季康子的叔祖母,所以文伯這樣說。
f 僮子:即童子。 備官:做官。
g 女:通“汝”,你。
h 大采:五彩的禮服。 朝日:天子每年春分時節祭祀太陽的儀式。
i 祖:熟習。 識:知。 地德:古人認為土地能生長萬物、養育百姓,這便是地之德,也可以理解為土地的習性。
j 師尹:大夫官。 惟:表并列,與,和。 旅:眾士。
牧:州牧。 相:國相。 宣序:全面安排。
k 少采:三彩禮服。 夕月:天子每年秋分之夜祭祀月亮的儀式。
l 大史:即太史,掌管史書及星歷的官員。 師載:掌管天文的官員。 天刑:天體運行的法則。
m 九御:九嬪,天子宮中的各種女官。
n 禘:天子祭祀祖先的大祭。 郊:天子在國都外舉行的祭祀典禮。 粢盛:祭祀用的谷物。
o 慆淫:懈怠,放蕩。
p 庇:治理。
q 玄紞:古代冠冕兩旁用來懸玉的黑色絲帶。
r 纮:古代冠冕系在頜下的帶子。 綖:蓋在冕上的布。
s 列士:士的總稱,周代分元士、中士、庶士三種。
t 社:春社,每年春分時祭祀土地神。
u 蒸:指冬天的祭祀,進獻五谷、布帛。
大意:
公父文伯退朝之后,去看望自己的母親,他的母親正在紡麻,文伯說:“以我這樣的家庭還要母親親自紡麻,恐怕會讓季孫惱怒。他會覺得我不能孝敬母親吧?”
公父文伯的母親嘆了一口氣說:“魯國就要滅亡了吧!讓你這樣幼稚無知的人做官,卻不告訴你為官之道嗎?坐下來,我講給你聽。過去圣賢的君主為百姓安置居所,選擇貧瘠之地讓百姓定居下來,使百姓勞作,發揮他們的才能,因此君主能夠長久地統治天下。老百姓只有勞作才會思考,只有思考才能找到改善生活的辦法;閑散安逸會導致人們過度享樂,人們過度享樂就會忘記美好的品行,忘記美好的品行就會產生邪念。居住在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才,是因為過度享樂啊。居住在貧瘠土地上的百姓,沒有不講道義的,是因為他們勤勞啊。因此,天子穿著五彩花紋的衣服隆重地祭祀太陽,讓三公九卿了解五谷生長的情況。到了日中的時候,考察國家政務,與百官中的政事、師尹和旅、牧、相等一起安排事務,使百姓得到治理。天子穿著三彩花紋的衣服祭祀月亮,和太史、師載詳細記錄天象,探究天體運行的規律。日落時便督促嬪妃,讓她們清潔并準備好禘祭、郊祭用的各種谷物及器皿,然后才去休息。諸侯們清早聽取天子布置的任務以及訓導,白天完成他們所負責的日常政務,傍晚則反復檢查典章和法規實施的情況,夜晚警告百官,告誡他們不要過度享樂,然后才去休息。卿大夫早晨統籌安排政務,白天與屬僚商量如何處理政務,傍晚梳理一遍當天的事務,夜晚處理他的家事,然后才去休息。士人早晨接受早課,白天講習所學的知識,傍晚復習,夜晚反省自己有無過錯,直到沒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才去休息。從平民以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一天懈怠。王后親自編織冠冕上用來系玉的黑色絲帶,公侯的夫人還要編織系于頜下的帽帶以及覆蓋帽子的布。卿的妻子做腰帶,大夫的妻子要親自做祭祀用的服裝,各種士人的妻子還要做朝服。自庶士以下都要給丈夫做衣服。春分祭祀土地,接著開始耕種;冬天祭祀時,獻上谷物和布帛,無論男女都要做出貢獻,有過失就會受到懲罰。這是自古傳下來的制度。為官者操心,百姓出力,這是先王的遺訓。自上而下,誰敢放蕩而不去努力呢?
“如今我守了寡,你又做官,早晚勤懇做事,尚且擔心丟棄了祖宗的基業。倘若懈怠懶惰,又怎么躲避得了罪責呢?我希望你早晚提醒我說:‘一定不要廢棄先人的傳統。你今天卻說:‘為什么不自圖安逸。以你這樣的態度承擔國君安排的職位,我恐怕你的父親穆伯要絕后了。”
孔子聽了這件事,說:“弟子們記住,季家的這位老婦人確實不圖安逸啊!”
【點評】
這是一位母親對孩子的教導,也是古代家風家教的典范。
公父文伯在朝為官,薪俸足以養活母親。他看到母親辛勤紡織,不免心生愧疚,于是提出讓母親頤養天年,不要再操勞。這本是人之常情,也是孝的表現,可是作為母親的敬姜卻講出了一番大道理。
敬姜這段近五百字的議論,首先分析了勤勞的益處和安逸的壞處。接著詳細敘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他們每天的工作雖各有不同,但都勤勉做事,“無日以怠”;婦女則上自皇后下至民女都做著分內之事。議論以“勞”字為主線,提出了“無一人之不勞,無一日之不勞,無一時之不勞”的理念。作為一位貴族婦女,敬姜提出了勞動的重要性,反對好逸惡勞,并把它提到國家興亡的高度,現在看來是十分可貴的。
古語有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敬姜的議論不僅是告誡自己的孩子,也是告誡后人要在忠于職守、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厲行勤儉,不可貪圖安逸,否則很可能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