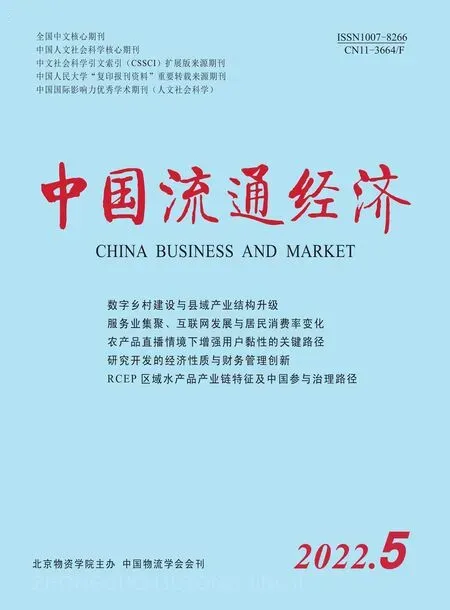服務業集聚、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率變化
——來自我國現代流通業的經驗證據
汪 洋,吳順利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市 100070)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而居民消費率卻呈現波動下滑的總體態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至2019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已由46.7%下降至38.8%。消費作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壓艙石”,居民消費疲軟勢必會掣肘國民經濟暢通循環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如何擴大內需,并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2020年9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指出,現代流通體系建設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載體,能夠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促進居民消費。2021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并重點指出,穩定和擴大消費應借助“互聯網+”優勢,推進線上線下更廣更深融合,推動新業態和新模式的發展。由此看出,“互聯網+流通”已成為驅動居民消費的戰略引擎。
作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現代流通服務業已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及先導性產業。過去受“重生產、輕流通”觀念桎梏,加之流通企業布局分散、規模小、集中度低,傳統流通業存在“渠道淤塞、低效能、高成本”[1]以及競爭力薄弱[2]等諸多短板和問題,不僅加劇了商品流通領域的市場分割現象,而且嚴重限制了流通在消費領域的關鍵作用。近年來,我國流通服務業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以及現代化趨勢加強,空間集聚特征愈發凸顯,為適應消費領域擴容提質和方式創新等變化提供了現實契機。此外,互聯網作為一種靈活高效的新型媒介,不僅驅動居民消費結構向個性化轉變,還從消費端拉動產業轉型升級[3],進而有效引導現代流通業發展模式和方向。2020年,我國互聯網普及率升至70.4%,全年完成電信業務量、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分別達到13.675 8萬億元和9.759 0 萬億元,較上年分別增長28.1%、14.8%①。既有研究指出,網絡購物非但不會擠占線下實體消費,反而具備一定的驅動作用[4]。互聯網具有顯著的網絡效應[5],消費者的網絡型服務需求正受到網絡效應的主導[6],以網絡購物、移動支付、云消費、元宇宙、智慧物流等為代表的新業態、新模式和新技術逐漸興起,并成為釋放我國內需潛力的中堅力量。綜上,本文試圖探討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率三者間內在關聯,希冀為優化現代流通業空間布局、提升現代流通體系與互聯網的適配性以及解決國內居民消費不足問題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馬歇爾(Marshall)[7]率先詳細闡述了產業的空間集聚現象以及導致集聚外部性形成的三大經典動因:知識溢出、中間投入品共享以及勞動力蓄水池。杜蘭頓(Duranton)等[8]進一步將集聚經濟的三大微觀機制歸納為學習、共享和匹配。此外,還有大量的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產業集聚形成機制[9-10]以及外部性理論[11-12]展開了細致的探討。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逐漸側重于對產業集聚外部性的經濟社會效益進行深層次解析,且主要圍繞以下主題:一是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13];二是產業集聚與知識、技術創新溢出[14-15];三是產業集聚與要素流動[16]、資源配置[17]以及勞動生產率[18];四是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19]。總體來說,這類研究現已較為系統和完善。
值得深思的是,產業集聚的外部性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但其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尚不明確。目前,學術界側重于以制造業或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研究對象來考察產業集聚的消費效應[20-21],而專門探討現代流通業集聚消費效應的文獻相對較少。丁寧[22]認為,商業組織在商圈內形成集聚能通過直接和間接網絡外部性更好地滿足消費者多元、個性化需求,但隨著區域內流通業集聚的加深,會加劇行業內競爭。豪斯曼(Hausman)等[23]的研究發現,流通行業內部競爭程度的提升會驅使各類新產品、服務以及品牌流入,反而會消減顧客的購物支出。此外,羅福周等[24]基于中國2000—2017年省級面板數據,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發現流通業集聚能通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中介機制來降低農村居民消費。而朱保芹[25]認為,流通業集聚僅對城市居民消費具有促進作用,對農村消費作用不明顯。綜上,當前學界關于現代流通業集聚消費效應的研究尚不完善,且存有顯著爭議,亟待對其做進一步挖掘和補充。
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間關系的探討逐漸引起學者們的濃厚興趣。諾瓦克(Novak)等[26]創新性地測算了消費者在互聯網環境下的消費體驗度;穆爾喬諾(Muljono)等[27]針對網絡購物過程中影響消費者持續購買意愿的關鍵因素展開了調查和分析。劉湖等[28]研究發現,互聯網發展能夠提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并推動消費升級。劉大為等[29]以2018年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為樣本,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實證發現,互聯網對家庭消費總支出有促進作用。此外,郭崇等[30]研究發現,我國商貿流通業借助“互聯網+”的資源優勢以及信息共享平臺的作用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但鮮有學者將互聯網納入對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間關系的探究。
綜上所述,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研究:一是以現代流通服務業為例,采用區位熵指標測算我國省域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二是基于產業集聚的外部性視角,從理論分析和經驗證據兩方面考察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三是將互聯網發展水平嵌入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機制邏輯框架,構建交互效應模型和門檻模型,探究互聯網發展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作用路徑間的調節作用和門檻效應。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
現代流通業集聚的規模經濟和外部性對居民消費率的變動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基于馬歇爾-阿羅-羅默(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性的理論基礎,分別從擠出效應、收入效應、輻射效應、示范效應、成本效應等五個方面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非線性關聯進行機理剖析。
一方面,當現代服務業集聚程度較低時,集聚負外部性率先凸顯,并抑制居民消費率提升。流通業與產銷雙方聯系緊密的行業特征,加之運輸過程中的“冰山成本”,驅使流通企業偏向選址于地理位置和要素稟賦優越、交通便捷、市場潛能大的城市中心[31],造成流通業顯著的“中心—外圍”分布特征。集聚外圍區在前期會受到強烈的路徑依賴和虹吸效應影響,不僅會破壞商品、要素自由調整的市場機制,出現渠道淤塞、低效能、高成本等問題,還將誘發資源搶奪、惡意競爭、尋租和串謀等低效行為,嚴重阻礙居民消費潛力釋放。而伴隨著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當中心區集聚程度提高至區域內要素配置、商品供給與居民消費能力嚴重脫鉤時,擁擠效應將超越集聚效應占據主導地位,所引發的要素擁塞、資源錯配、交通擁堵、公共基礎設施濫用、知識產權非法侵權等負外部性可能會對地區居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信心產生負向沖擊,而高昂的房租、裝修費用、廣告宣傳成本、競爭性創新投入會阻礙市場均衡價格的下降,加之勞動力過度地向中心區流入,將對工資水平產生負向沖擊[32],降低居民消費絕對能力,從而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
另一方面,當區域內現代服務業集聚達到較高程度后,集聚正外部性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并開始對居民消費產生促進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收入效應。與制造業集聚不同,服務業集聚能顯著增加勞動者工資水平[33]。現代流通服務業集聚的規模效應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流通企業降本增效以及增加利潤,從而提升勞動者工資收入。同時,現代流通業在區域內大規模集中還會產生知識溢出效應,增進勞動者間的學習和共享,提升和強化勞動者創新能力、人力資本水平和技能差異,促進地區工資增長。二是輻射效應。主要呈現為“中心集聚—范圍輻射—外圍擴散—多極化均衡”的空間演化路徑。流通企業傾向于將投資目標靶向消費者渴望安居樂業的區域,而這些區域多為城市中心[31]。因此,各類現代流通企業將率先“扎堆”城市中心,不斷豐富城市居民的商品和服務供給種類,促進產品質量升級。隨后,集聚中心區通過輻射效應向周邊居民或單位擴散正外部效益,進而擴展和強化外圍區的商品流通渠道和效率,擴大交易范圍,更好地滿足消費者多元需求。三是示范效應。隨著流通業集聚程度的加深,區域內大規模的同質化產品或服務,將驅動流通服務業創新和轉型。為搶占市場份額,各類創新型業態、技術、模式和區域品牌將在集聚區內形成示范效應,不斷推動區域創新意識培養、營商環境優化以及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升,并在消費的示范效應和攀比效應作用下,潛移默化地推動居民消費觀念和習慣轉變、消費擴容升級。四是成本節約效應。首先,現代流通業集聚可以節約消費者商品、價格搜尋過程中所耗費的金錢和時間成本,并避免市場信息不對稱所引致的信息成本損耗;其次,弱化生產者—消費者間的時空約束,削減冗雜流通環節,可以節約市場交易和流通成本;最后,匹配機制還有助于流通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精確匹配勞動供給者,降低勞動力供求雙方的搜尋成本[34]。鑒于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可能存在先抑制后促進的作用機理,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存在U型曲線關系。
(二)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率
互聯網發展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幾條途徑實現:首先,互聯網普及與應用有利于勞動者通過在線教育、數字技能培養以及知識溢出等方式提升自身專業素養和創新能力,擴大地區就業規模和老年就業參與[35-36],促進城鄉居民增收[37],進而增強居民消費絕對能力;其次,互聯網交易平臺的數字賦能可極大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時空距離,壓縮流通成本,削減交易成本,“互聯網+”消費的新模式不斷驅動新舊動能轉換,突破傳統購物方式的時空約束,增強消費的便捷性,節約時間成本和鞋底成本[38];再次,互聯網的網絡效應不僅有助于調節供需兩側的理性均衡,優化供給體系對居民需求的適配性,還能有效地弱化城市行政壁壘,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進程,擴大商品供給范圍和市場規模,最終促進居民消費;最后,互聯網金融以及網絡借貸平臺有助于便捷消費信貸,增加家庭信貸需求,降低家庭信貸約束的概率[39],從而緩解居民消費過程中的流動性約束,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互聯網發展對居民消費率產生正向驅動作用。
(三)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率
進入21世紀以來,以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元宇宙以及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的互聯網虛擬平臺與實體流通服務業深度融合所衍生出的各類新業態、新技術和新模式,成為拓寬消費領域、挖掘消費潛力、加速消費升級的核心動力源。
區域信息要素的優化配置在流通企業區位選擇、投資決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在互聯網發展水平較低、新型基礎設施尚未完善時,流通業與互聯網融合成本較高,難度亦相對較大,這導致互聯網服務開發與推廣初期的流通企業收益和消費者效用相對較低,此時的互聯網發展還可能擠占對實體流通業態的市場需求,故而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關系的調節效應為負。但是,當互聯網發展達到較高標準且跨越一定門檻后,流通業與互聯網的協調與融合程度會不斷加深。流通企業借助互聯網技術搭建信息共享平臺,及時獲取消費信息和顧客評價,適時調整產銷策略,推動流通企業降本增效。新經濟地理學認為,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流通成本節約能顯著增強區域產業集聚能力[40],不斷吸引流通企業在空間上集聚,并在流通業集聚進程中憑借互聯網時空壓縮效應,弱化商品流通的市場分割現象,推動流通業一體化發展[41]。在此階段,互聯網發展通過信息共享、交易成本節約以及服務范圍擴張等諸多渠道來削弱甚至扭轉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的不利影響,從而正向調節流通服務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的關系。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互聯網發展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二者間關系具有U型調節效應。
H4:互聯網發展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具有門檻效應。
四、模型構建、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一)計量模型構建
1.基準模型的構建
為了初步判定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率的線性關系,構建基準模型1:

其中,Cit為地區i在年份t的居民消費率,aggit為地區i在年份t的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interit為地區i在年份t的互聯網發展指數,∑Controlit表示其他控制變量集合,δi為地區效應,γt為年份效應,μit為隨機擾動項,θ為常數項,α、β為回歸系數。
為了檢驗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在模型1基礎上引入現代流通業集聚的平方項,得到模型2:

其中,為地區i在年份t的現代流通業集聚的平方項。
2.面板分位數模型的構建
我國省域間居民消費率差距較大,而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估計的目標函數易受異常值影響,故本文利用科恩克(Koenker)[42]提出的分位數回歸方法來有效減少異常值影響偏誤,并揭示居民消費率條件分布的全貌。基于此,本文進一步采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方法考察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對不同居民消費率水平的影響效應。根據模型2,構建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3:

其中,Qτ(Cit)為居民消費率的τ分位數,α1τ、α2τ、α3τ為現代流通業集聚及其平方項和互聯網發展的τ分位數回歸系數,βiτ為控制變量的τ分位數回歸系數。
3.交互效應模型的構建
進一步,為檢驗互聯網發展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調節效應,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現代流通業集聚及其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的交互項(aggit×interit、×interit),得到交互效應模型4:

其中,aggit×interit、×interit分別為現代流通業集聚及其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的交互項。
4.面板門檻模型的構建
本文借鑒漢森(Hansen)[43]提出的面板門檻模型,以各地區的互聯網發展指數作為門檻變量,將現代流通業集聚設定為區制變量。進一步,為了驗證現代流通業集聚在不同互聯網發展水平下對居民消費率影響的門檻效應,構建面板門檻回歸模型5:

其中,interit作為門檻變量,aggit為模型的區制變量,I(·)為指示函數,若指標函數為真則取值為1,反之為0,∑Controlit為控制變量集合,χ為常數項,ρ、λi為系數估計值,εit為隨機擾動項,γ為門檻值。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居民消費率(C):用各地區居民消費支出總額與GDP 的比重衡量,其中,居民消費支出總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城鎮人口+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農村人口;城鎮居民消費率(UC):用各地區城鎮居民消費總支出與GDP 的比重衡量;農村居民消費率(RC):用各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總支出與GDP的比重衡量。
2.解釋變量
現代流通業集聚(agg):目前,學術界對現代流通業的概念和產業邊界尚未形成明晰和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現代流通業是中高級批發市場、連鎖經營零售業、現代服務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和物流業等行業的集合[44],但其中的一些細分行業無法用專門的統計指標來測度。本文借鑒孫金秀[45]的界定方式,用現代流通業主體部分,即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三大細分行業的集合來衡量現代流通業。此外,考慮到我國現代流通業集聚的中心在城鎮地區,而農村流通領域主要是以集市貿易式、練攤式為主的私營企業或個體戶,規模小,組織化及現代化水平滯后。因此,為區別于傳統流通業,主要參照國家標準《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T4754—2017),用各省份流通三大細分行業的城鎮單位就業人數和城鎮私營企業與個體戶就業人數總和來測度現代流通業的就業規模,并借助區位熵指標對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進行測度,區位熵指指標的數值大小代表著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的高低。區位熵計算公式為:

其中,eij(t)為t年份省份i在j產業的就業人數,為t年份在省份i所有產業就業人數和,為t年份j產業的全國總就業人數,為t年份所有產業全國的總就業人數。
本文測算了2005—2019年中國省域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但限于篇幅,具體測算結果不在此贅述。表1表明,我國現代流通業在空間上的集聚程度具有顯著非平衡特征。東部地區的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②。其中,北京、上海、廣東、遼寧等東部省市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相對較高,而西部地區除重慶外,其余省份的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整體偏低;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集聚程度在30 個省市區中排名靠后,與西部省份差異較小。總體來看,我國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呈現出顯著的東高西低空間特征。

表1 2005—2019年我國省域現代流通業集聚指數均值
表2描述了我國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隨時間變化的趨勢。結果顯示,從全國層面看,我國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隨時序的增加總體呈現下降的態勢。分地區看,東部地區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逐漸下降,中部地區的集聚程度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西部地區的集聚程度上升趨勢明顯。截至2019年,東部地區的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始終高于中西部地區,但隨著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間差距逐漸縮小。此外,2014年之后,西部地區的集聚程度開始超越中部,呈現出中部塌陷的空間格局。

表2 2005—2019年全國及分地區的現代流通業集聚指數時序變化
3.調節/門檻變量
互聯網發展(inter):互聯網發展的概念涉及內容頗深,學術界對其的衡量方法也存有差異。較多學者采用網民規模、寬帶接入端口數、移動電話用戶、電信業務量、CN 域名數、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等指標衡量[3,46]。本文借鑒白雪潔等[47]的做法,主要從互聯網應用和互聯網基礎設施兩大視角構建互聯網發展指標體系(見表3)。其中,互聯網應用以互聯網普及率、電信業務總量/GDP衡量;互聯網基礎設施水平用每萬人域名數、每萬人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衡量。最后,利用熵權法將四個指標合并成為互聯網發展的代理指標。

表3 互聯網發展指標體系
4.控制變量
為減少模型中存在的遺漏變量偏誤,本文參考現有相關文獻,在模型中控制以下變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各省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測度,并進行對數化處理;居民收入水平(inc),用各省份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衡量,并取自然對數,其中,居民人均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村人口)/總人口;政府支出(gov),用各省份政府財政支出與GDP 比值來衡量地方政府部門對經濟、民生的干預和投入力度;對外開放(open),用各省份美元兌換人民幣匯率平均價折算后的進出口總額占地區GDP比重測度;城鎮化率(urban),用各省份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升級(indus),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出增加值的比值衡量。
(三)數據來源
文中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統計報告、各省市統計年鑒以及EPS全球統計數據庫,并對數據做如下處理:為保證數據的可得性與完整性,本文對數據缺失嚴重的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和西藏地區予以剔除,最終選用中國其余30 個省區市2005—2019年度的面板數據作為觀察樣本;為了使數據更具可比性,對部分統計口徑不一致的變量予以調整后合并,同時對所有貨幣價值數據以2005年的不變價計算。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4。

表4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樣本量=450)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模型在估計階段的偽回歸現象,需要檢驗各變量的平穩性。本文選擇HT、IPS、ADFfisher 三種檢驗法,檢驗結果見表5。檢驗結果顯示,除agg、inter、agg2三個變量的原始數據在兩種及以上檢驗方式下具備高度平穩性外,其余各變量的檢驗結果均接受了原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此外,原序列一階差分后均是平穩的,即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二)協整檢驗
根據表5可知,模型中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需進行協整檢驗,以驗證各變量間長期關系的存在與否。本文采用面板協整考(Kao)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協整關系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各統計值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即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關系,可采用原序列進行后續實證分析。

表5 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三)基準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5.0 軟件進行后續實證估計。在模型估計方法選擇上,豪斯曼檢驗的p值結果在1%顯著水平上拒絕混合、隨機效應(RE)的原假設,故選擇固定效應(FE)模型更為科學。此外,考慮到各變量的個體和時間差異,選擇時空雙重固定效應模型。本文將FE、RE的回歸結果匯總至表7,以便對結果進行對比和分析。
表7第2—5 列顯示,基準模型1 依次引入現代流通業集聚(agg)及其平方項(agg2)和互聯網發展(inter)后,擬合優度R2不斷提升。第5 列中現代流通業集聚(agg)回歸系數為-0.045 7,且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而其平方項(agg2)的回歸系數為0.012 0,同樣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表明,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并非存在直接的線性關聯,而是存在U型曲線關系,根據拐點公式計算得出U型曲線的拐點值約為1.904。這意味著,當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較低時,會抑制居民消費,只有當集聚程度跨過臨界點1.904 后,才會正向促進居民消費,故H1 通過檢驗。同時,表7的第5 列結果還顯示,互聯網發展(inter)的回歸系數在5%顯著水平下為0.096 7,因此,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和應用水平的提升,將對居民消費產生正向促進作用,故H2成立。這一結果也與蔡海亞等[48]的研究結論一致。
在控制變量方面,經濟發展水平(lnpgdp)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一結果同我國當下居民消費增長速度滯后于經濟增速的國情相符。居民收入水平(lninc)系數顯著為正,該結果與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觀點一致,居民收入水平決定消費的絕對能力,是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決定性因素。財政支出(gov)系數為正,政府部門對企業和居民給予的經濟補貼和保障能顯著提升居民消費率。城鎮化率(urban)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我國城鎮地區作為人口和產業集聚的中心,擁有更優越和發達的基礎設施條件和商品流通體系,且消費習慣、渠道和模式更加開放、多元以及便捷,勞動者工資也普遍高于農村,因此城鎮化率提升會促進居民消費。對外開放(open)系數為負,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由于我國2015年以前的外貿依存度明顯偏高,導致內外需結構嚴重失衡[49],但隨著國內大市場主體地位的逐步確立,國內市場需求日益攀升,對外開放對居民消費的作用不斷減弱。產業結構升級(indus)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是因為我國服務業發展質量有待提升,技術創新動能不足,導致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比值提升對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作用不夠明顯。

表6 面板協整檢驗結果
(四)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為了清晰地展示現代服務業集聚及其平方項和互聯網發展回歸系數隨分位數變化的情形,進一步選取五個具有代表性的分位數:10%、25%、50%、75%、90%,考察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對不同居民消費率水平的影響程度(見表8)。
表8列(1)至列(5)表明,現代流通業集聚在10%、25%、50%、75%、90%五個分位數上都表現出與居民消費率間的U 型關系,且拐點分別為1.886、1.890、1.916、1.928、1.942。總體來看,隨著居民消費率的提升,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U型曲線的拐點存在右移趨勢,而互聯網發展只在50%、75%兩個分位數上與居民消費率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加顯著。分析結果不僅佐證了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U 型曲線關系(H1),說明了互聯網發展對居民消費率的正向促進作用(H2),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對不同居民消費率水平影響程度的差異。隨著居民消費率的提高,居民的需求層次不斷提升,逐漸由生存型向發展和享受型升級,由物質需求向精神需求轉變,此時現代流通業發展和布局的標準更“嚴苛”,其對居民消費率產生正向作用的難度逐漸增加。網絡時代,居民消費潛力不斷增加,而互聯網作為消費者滿足精神需求的重要平臺和載體,將隨著居民消費率的提升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此外,表8中的各控制變量在五個分位數下的回歸系數方向和顯著性與表7結果高度一致。

表7 基準回歸結果

表8 面板分位數回歸結果
(五)調節效應檢驗的回歸結果與分析
為了驗證H3,在基準模型1 中進一步引入現代流通業集聚及其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的交互項(agg×inter、agg2×inter),得到交互效應模型,檢驗互聯網發展在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影響路徑中的調節效應(見表9)。
表9第2、3列表明,在分別控制了現代流通業集聚及其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的交互項之后,agg、agg2的回歸系數較表8結果無顯著變化,即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依舊存在U 型曲線關系。而由第2列可知,互聯網發展與現代流通業集聚交互項(agg×inter)的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互聯網發展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二者間的調節效應并非簡單的線性作用。另外,第3列顯示,現代流通業集聚與互聯網發展交互項(agg×inter)的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負,而現代流通業集聚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交互項(agg2×inter)的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這一結果表明,互聯網發展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具有U型調節作用,當互聯網發展水平較低時,其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即隨著互聯網發展水平的提升,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負效應得到進一步強化;當互聯網發展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時,其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隨著互聯網發展水平的提升,現代流通業能有效借助互聯網發展的網絡優勢,緩解甚至扭轉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作用,促進區域居民消費率的提升。因此,H3通過檢驗。

表9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六)內生性處理和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處理
本文模型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問題。此外,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還可能與居民消費率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造成內生性偏誤。本文選取agg、agg2、inter的一、二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一步采用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IV)的廣義矩估計(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方法、兩階段最小二乘(Two Stage Least Square M,2SLS)法對模型內生性問題進行處理。同時,本文借助不可識別、弱工具變量以及過度識別三種檢驗法判別工具變量的合理及有效性(見表10)。
表10 結果表明,克萊伯根-帕普秩(Kleibergen-Paap rk)LM統計量在1%顯著水平下強烈拒絕不可識別工具變量的原假設,克萊格-唐納德·伍爾德(Cragg-Donald Wald)F統計量均大于10%水平的臨界值,故強烈拒絕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過度識別檢驗中的漢森J統計量均無法拒絕所有解釋變量均為外生的原假設,故所有工具變量均為外生且有效。表10的回歸結果與表7和表9的結果高度吻合,即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依舊具有U型影響(佐證H1);互聯網發展對居民消費率具有正向作用(佐證H2);交互項agg×inter系數顯著為負,而agg2×inter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互聯網發展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的關系具有U型調節效應(佐證H3)。因此,本文在考慮了模型內生性問題后,上述結論依舊成立。

表10 內生性處理結果
2.穩健性檢驗
為增強上文主要結論的可信度,下面將繼續對H1—H3進行穩健性檢驗。
(1)動態性考量。考慮到居民消費具有慣性特征,即本期居民消費率會受到上期影響,因此,有必要將模型的動態性納入考量范圍。本文在原靜態面板模型4 中引入居民消費率滯后項(Ci,t-1),構建動態面板交互效應模型7:

其中,Ci,t-1為省份i在t-1年份的居民消費率,φ為居民消費率滯后一期的系數值。
動態面板模型常用系統GMM 方法估計,本文利用系統GMM方法估計得到表11 第2 列。首先,需要對表11 第2 列的工具變量有效性進行判斷。模型殘差序列相關性檢驗AR(1)的p值結果表明存在一階自相關,AR(2)的p值為0.143,故誤差項均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性,薩爾甘過度識別檢驗的p值為0.975,無法在10%顯著水平下拒絕所有解釋變量均為外生的原假設,故所有工具變量均為外生且有效。
(2)剔除異常值。本文利用1%雙側縮尾法分別剔除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交互項以及居民消費率的極大和極小值,并重新進行回歸估計,以盡可能地消除極端值給結果帶來的偏誤,得到表11第3列。
(3)刪除年份。將2005年和2019年這兩端的時間樣本剔除,從而將研究樣本期間縮短為2006—2018年,結果見表11第4列。
(4)主要變量替換。本文分別對被解釋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替換以驗證結論的穩健性。其中,居民消費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 的比重替換,得到表11第5列;互聯網發展用各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即網民規模占總人口的比重替換,得到表11的第6列。
由表10、表11 的內生性處理和穩健性檢驗結果可知,各變量系數估計值與表7和表9結果無較大差異,故H1-H3再次得到印證,表明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具備較高的穩健性和可靠性。

表11 穩健性檢驗結果
(七)異質性檢驗
1.消費群體異質性檢驗
鑒于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在消費能力、觀念、習慣以及模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本文還將基于整體視角的消費群體分解為城鎮和農村居民,探討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對城鄉居民消費率的異質性影響(見表12)。
表12 第2、3 列的結果顯示,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城鄉居民消費率的影響均具有U型特征,不同的是,互聯網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但對城鎮居民的正向作用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相對于城鎮,我國農村地區的商品選擇性和流通渠道單一,消費信息較匱乏,存在諸多抑制農村居民消費活力的因素。而互聯網發展可以通過信息共享平臺獲取農村居民需求信息,擴大有效供給,并借助線上消費模式削減產銷間的時空壁壘,故互聯網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率的提升作用更為突出。此外,表12 第2 列結果表明互聯網發展對流通業集聚與城鎮居民消費率間的關系具有顯著U 型調節作用;而第3 列結果則顯示,互聯網發展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農村居民消費率間關系不具有非線性調節效應。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有限,且消費觀念和習慣相對滯固,在有限的市場需求下,互聯網發展的調節作用很難有效發揮出來。
2.地區異質性檢驗
考慮到我國存在著顯著的地區差異,本文進一步分東、中、西三大地區考察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檢驗是否存在地區異質性,具體結果如表12 第4-6 列所示。其中,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關系在東部地區樣本下具有顯著U 型特征,在中部、西部地區樣本下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在于,我國東部地區作為經濟和人口集聚的中心,各類流通企業爭相駐扎,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在前期脫離市場需求的匹配范圍,限制了要素自由調整,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因此,隨著流通業集聚程度的提升,擁擠效應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作用率先凸顯;但當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超過一定水平后,要素得到充分調整,消費潛力進一步被挖掘,集聚效應得以充分發揮。而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水平、流通體系建設等方面相對滯后,且居民消費能力有限,極大地阻礙了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提升作用。
互聯網發展(inter)系數在東部地區不顯著,但在中西部地區顯著為正,而現代流通業集聚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交互項(agg2×inter)的系數在東部地區顯著為正,在中西部地區不顯著。因此,東部地區能間接地依靠互聯網發展對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二者間關系的U 型調節效應,而中西部地區主要利用互聯網的直接效應促進居民消費。但由于中西部地區流通產業的發展和布局受路徑依賴效應掣制,嚴重阻礙互聯網向流通業的滲透和融合,加之滯固的消費觀念使互聯網的時空壓縮效應難以形成,從而無法有效地發揮其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3.行業異質性檢驗
本文進一步對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三大細分行業的區位熵進行測算,分別檢驗其對居民消費率影響的行業異質性,具體結果見表12第7-9列。

表12 異質性檢驗結果
總體來看,現代流通業各細分行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均存在一定的U 型非線性關系。但從U 型曲線的拐點值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U 型曲線關系的拐點值最大。一個可能原因是,相較于另外兩大行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更加關注對運輸成本的節約,它不僅要密切聯系上游生產廠商,而且要重點關注地區市場規模,這驅使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企業向交通便利、市場規模大的城市中心集聚。這種特殊的行業特征造就了其顯著的路徑依賴性,極大地降低了要素調整與配置的效率與合理性,也相應地增加了該行業集聚效應形成的難度,進而延緩了其對居民消費率的正向促進作用。
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集聚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交互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集聚平方項與互聯網發展交互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作為商貿流通服務業中與消費者聯系最緊密最直接的行業,近年來其與互聯網的融合程度不斷加深,以新零售、云訂餐、外賣配送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新業態新模式不斷興起,線上服務、線下體驗與現代物流有機結合,有利于發揮互聯網發展對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的U 型調節作用;而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依賴與制造業的垂直關聯和協同定位,這種特殊的行業特征在互聯網發展水平低于一定程度時,有助于促進互聯網與現代物流業的融合發展,進而正向調節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關系;但當互聯網發展水平超過一定程度后,會產生線上需求與線下實體配送脫節以及物流成本提升等負外部性,進而負向調節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關系。
(八)門檻效應分析
為了驗證H4,本文參考劉建民等[50]的方法,進一步檢驗探究互聯網發展在產生調節效應時,是否同時存在門檻效應,檢驗結果如表13所示。

表13 門檻值估計結果
利用門檻自舉法(Bootstrap),通過500 次抽樣進行門檻效應檢驗發現,互聯網發展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的單一門檻檢驗,但未通過10%顯著性水平的雙重門檻檢驗,故選擇單一門檻模型,門檻值為0.095 3,根據門檻值將互聯網發展指數劃分為inter≤0.0953和inter>0.0953兩個階段。
由表14可知,當互聯網發展指數不大于0.095 3 時,現代流通業集聚回歸系數為-0.020,且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此時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當互聯網發展指數跨越門檻值0.095 3 時,現代流通業集聚回歸系數變為-0.009,且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此時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仍具有抑制作用,但抑制作用逐漸減弱。這意味著,當互聯網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削弱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作用,這一研究結果與前文理論分析相符,即互聯網發展水平達到一定標準后,將通過信息共享、時空壓縮以及服務范圍擴張等諸多渠道來削弱集聚負外部性對居民消費的不利影響,故H4成立。

表14 門檻效應的回歸結果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1.我國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呈現U 型曲線特征。隨著現代流通業集聚程度的提升,居民消費率呈現先升后降的變化趨勢。2.互聯網發展與居民消費率正相關,互聯網發展對區域居民消費率具有顯著的正向驅動效應。3.互聯網發展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具有U型調節效應,并存在門檻效應。互聯網發展水平跨越拐點會削弱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作用。4.現代流通業集聚、互聯網發展對不同居民消費率水平的影響效果存在差異。現代流通業集聚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率的影響均具有U型特征。不同的是,互聯網發展對城鎮居民消費率的直接作用不明顯,但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城鎮居民消費率間具有U型調節作用;互聯網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率的正向作用顯著,但不具有非線性調節效應。在東部地區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U型曲線關系顯著,而在中西部地區不顯著,只有在東部地區互聯網發展對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關系才具有調節作用。現代流通各細分行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均呈現U 型曲線關系,但互聯網發展對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關系的U 型調節效應顯著,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倒U型關系調節效應顯著。
(二)政策建議
1.科學引導現代流通業集聚化、規模化、高效化發展
各地區應轉變“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觀念以及流通服務業分散化、碎片化、低效化的滯后模式,合理引導現代流通業集聚化發展,通過規模經濟推動流通服務業降本增效,提升流通企業和品牌競爭力,最終促進居民消費潛力釋放。各地還應統籌平衡現代流通業集聚度與市場需求、行業獨特性的關系,適時引導商品、要素的流動方向以及產業集聚的適宜范圍,避免受到路徑依賴和擠出效應的掣肘,從而降低居民消費率。
2.堅定推進“寬帶中國”戰略,推動區域互聯網發展
加強先進網絡信息技術的投入和研發,推進新型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進而提升區域互聯網普及率和應用水平;加強對貧困地區、農村以及中老年群體的互聯網教育和推廣,改變傳統的、滯固的消費觀念和模式,將互聯網作為促進居民消費的新動能。
3.推進“互聯網+流通”計劃的實施,深化互聯網與現代流通業的深度融合
各地應積極推動傳統流通業向現代化、數字化、信息化及智能化流通業轉型升級,促進流通業與互聯網虛擬平臺的跨界整合和深度融合,構建全渠道、全方位、標準化現代流通體系,催生一批高效、穩定、智能、綠色、便捷的新業態、新技術和新模式,有效發揮互聯網在現代流通業集聚與居民消費率間的調節效應。
注釋:
①互聯網普及率、電信業務量和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②本研究中的東部地區包含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以及遼寧共11省市,中部地區包含山西、內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黑龍江和吉林9 省區,西部地區包含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以及新疆10 省市區。受數據可得性與完整性限制,我國香港、澳門、臺灣、西藏地區數據未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