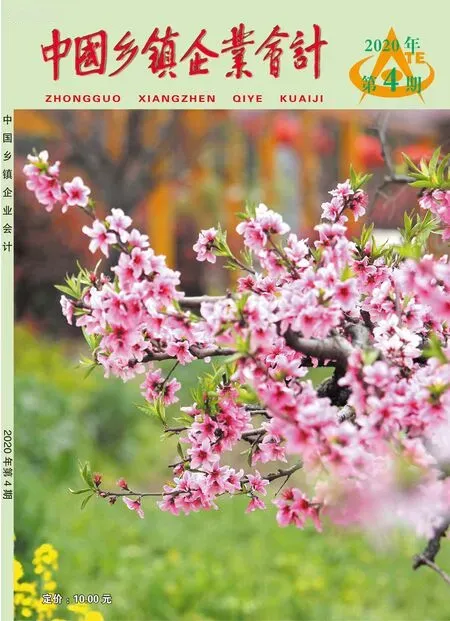新冠疫情沖擊、財務柔性儲備與企業投資行為
梁 娟 柴藝琿
一、引言
2019 年末爆發的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企業面臨生存壓力。朱武祥等(2020)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研究發現,疫情期間現金能維持三個月以上的企業占比不到15%。疫情使得經濟陷入系統性停滯,企業陷入財務危機,不得不放棄原有投資計劃。Campello et al.(2010)以金融危機為契機,以美國、歐洲、亞洲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研究發現,超過50%以上的企業由于缺乏資金取消了原有的投資計劃。同時,財務柔性充足的企業抓住了有價值的投資機會,收購兼并瀕臨破產的企業。財務柔性的差異是否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
財務柔性指企業及時獲取財務資源,預防不確定性事件,把握有價值的投資機遇,實現價值最大化的能力(Graham and Harvey,2001)。理論上,財務柔性企業或是通過較低的負債率保留了未來舉債的能力,或是通過較高的現金儲備及時把握有力的投資機遇,或是通過二者的結合提高企業應對未來不確定性事件的能力(Billett et al.,2007;Almeida et al.,2004;Bates et al.,2009)。新冠疫情沖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檢驗事前財務柔性儲備能否增強企業抵御不利沖擊的有利機遇。本文借助新冠疫情沖擊,探討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發生前與疫情期間投資行為的差異。以2017-2020 年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雙重差分的方法研究發現,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期間投資增幅更大。進一步的檢驗發現,上述關系在民營企業更顯著。本文有助于更好的認識新冠疫情的經濟后果與影響微觀企業的傳遞機制,從而為企業財務管理決策提供借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新冠疫情爆發后,經濟活動系統性停擺,企業面臨生存壓力。一方面,疫情防控需要使得企業大面積停工停產,失去了收入來源。供應商未及時復工,防疫成本高,客戶取消訂單、交通管制等使得企業復工困難。此外,由于疫情持續時間不確定,復工后企業收入并未呈現出報復性反彈。另一方面,企業的流動性壓力巨大,除需要按時償還貸款、支付利息、租金外,還需要支付員工工資和“五險一金”。疫情大幅降低了企業的盈利,短期內增加了企業的流動性壓力,提高了企業因資金斷裂而破產的風險。但危機又與機遇相伴而生,疫情期間資產價格大幅下降,為資金充裕的企業提供了國內擴張的良好機遇(Mitton,2002)。我們預期,疫情期間,財務柔性企業不僅能更好的抵御經濟的負面沖擊,也能把握沖擊帶來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遇(Gamba and Triantis,2008)。由此,提出假設1。
假設1: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新冠疫情沖擊時期投資增幅更大。
新冠疫情對資本市場產生了強烈的沖擊,金融機構為規避風險不愿向民營企業貸款。即使政府推出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體系的新增貸款仍主要流向國有企業和政府支持的項目,民營企業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十分有限。當民營企業難以從外部資本市場為好的項目融資,或者外部融資成本高于內部融資成本時,企業可能從內部融資。因此,民營企業有更強的動機通過儲備財務柔性為投資活動提供資金。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財務柔性與投資增幅之間的相關關系在民營企業更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7 年至2020 年的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基礎,探討財務柔性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我們執行以下篩選程序:1.剔除金融行業的樣本;2.剔除出現ST 的樣本;3.剔除出現PT 的樣本;4.剔除同時發行A 股和B 股的上市公司;5.剔除研究數據缺失或存在異常值的樣本。經過上述處理,我們總共獲得2162家企業的8648 個觀測。其中:負債柔性企業461 家共1844 個觀測,對照組1701 家共6804 個觀測;現金柔性企業336 家共1344 個觀測,對照組1826 家共7304 個觀測;用綜合指標衡量財務柔性企業135 家共540 個觀測,對照組2027 家共8108 個觀測。研究所需財務數據來自于CSMAR 數據庫,產權性質來源于CCER 數據庫。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定義
借鑒Vogt(1994)、曾愛民等(2013),構建如下模型(1)驗證假設1,變量定義見表1,具體闡述如下:

1.因變量
因變量INVchg 為上市公司的新增投資。借鑒曾愛民等(2013),如表1 所示,INV 等于企業的資本性支出除以上期資產總額。
2.自變量
由于我們選用雙重差分的方法衡量疫情沖擊前與疫情時期,不同財務柔性企業的投資行為差異。所以自變量為Dummy*POST,下面,我們分別闡述Dummy 和POST。本文研究的樣本期間共4 年:新冠疫情爆發前3年,即2017-2019 年;新冠疫情爆發時期,即2020 年。Post 為虛擬變量,疫情發生前年度2017-2019 年,為0;疫情爆發年度2020 年為1。
我們采用單指標判斷法和多指標結合法來定義財務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除了選用負債柔性和現金柔性作為單指標判斷的標準外,我們還將兩者綜合來判斷財務柔性企業。Dummy 為衡量財務柔性的啞變量,借鑒曾愛民等(2013),我們采用三種方法衡量財務柔性:(1)負債柔性(DFF);(2)現金柔性(CF);(3)負債柔性與現金柔性相結合(CDF)。由于企業保持保守的財務策略是一種持續的財務決策行為,因此,若某一企業在2017-2019 年三個連續的會計年度資產負債率位于樣本最低的30%之列,則被定義為負債柔性企業,DFF 賦值為1,其余企業作為對照組(1),DFF 賦值為0。若某一企業在2017-2019 年三個連續的會計年度現金持有水平位于樣本最高的30%之列,則被定義為現金柔性企業,CF 賦值為1,其余企業作為對照組(2),CF 賦值為0。若某一企業在2017-2019 年連續三年資產負債率位于樣本最低的30%,且現金持有水平位于最高的30%,則被定義為財務柔性企業,CDF 賦值為1,其余企業作為對照組(3),CDF 賦值為0。
3.控制變量
我們還在模型(1)中控制了投資、經營活動現金流、TQ、企業規模、現金持有水平、產權性質、資產負債率、是否發放現金股利等可能對新增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具體見表1。此外,我們還控制了年度、行業固定效應。我們主要關心模型(1)中Dummy*POST 的系數α1。如果α1顯著為正,則表明與非財務柔性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新冠疫情期間投資增幅更大。

表1 變量定義表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為了考察財務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投資行為的差異,我們分別在表2 中報告了財務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在新冠疫情前與新冠疫情發生期間主要特征變量的均值,并采用t 檢驗判斷了財務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的均值差異的顯著性。
首先,從表2 可以看出,無論按照負債柔性、現金柔性的劃分標準,還是按照負債柔性和現金柔性的綜合劃分標準,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具有較小的規模、較好的成長機會、較低的投資,但是,財務柔性企業具有相對較高的經營活動現金流,保持較高的現金持有水平和較低的資產負債率,這些差異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這些發現和已有文獻一致(趙蒲和孫愛英,2004;曾愛民,2011)。
我們從表2 的結果考察財務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疫情前與疫情時期投資增量和投資規模的跨期變動情況。無論采用負債柔性(DFF)、現金柔性(CF)還是綜合指標(CDF)衡量財務柔性企業時,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疫情時期投資增幅(INVchg)更大。具體表現為,對照組企業的跨期投資增幅均為負,財務柔性企業的跨期投資增幅均為正,且跨期增幅差異顯著。當采用負債柔性(DFF)衡量財務柔性時,財務柔性企業投資跨期增幅為171.43%,對照組企業為-36%,且跨期增幅差異顯著。另一方面,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的跨期投資規模(INV)增幅更大,或減幅更小。當我們采用現金柔性(CF)衡量財務柔性時,財務柔性組的跨期投資規模減幅為0.37%,對照組跨期投資規模減幅為1.42%,但差異不顯著。

表2 樣本變量均值及差異顯著性檢驗
(二)回歸分析
從本文表3 的第列(1)至第列(3)可以看出,DFF*POST、CF*POST、CDF*POST 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置信水平顯著為正。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1,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期間投資的增幅更大。

表3 投資增量與投資規模的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的結果來看,企業的新增投資與上期的投資水平(INVi,t-1)呈顯著正相關,說明上期投資水平越高,本期投資增量越大,說明本期的投資政策是上期的延續。企業的新增投資與經營活動現金流(CFlowi,t)呈顯著正相關,說明本期經營活動現金流能為新增投資提供資金。企業的新增投資與規模(sizei,t)呈顯著正相關,可能是因為規模較大的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較輕,更容易為投資募集到資金,所以,規模越大,新增投資越大。企業的新增投資與資產負債率(LEVi,t)呈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會通過舉債為新增投資籌資。企業的新增投資與現金股利啞變量(DIVi,t)呈顯著正相關,那些內部資金充裕的企業才會發放現金股利,所以,與不發放現金股利的企業相比,發放現金股利的企業的新增投資較多。
從本文表3 的第列(4)、第列(6) 可以看出,DFF*POST、CDF*POST 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顯著為正。上述回歸結果說明,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期間投資規模的增幅更大。但是,列(5)CF*POST 的系數不顯著,現金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的投資規模在疫情期間和疫情前的差異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疫情并沒有結束,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仍存在不確定性,現金柔性企業仍需在保持適度的財務柔性和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二者之間權衡。這也與單變量的統計結果一致,即現金柔性企業與對照組企業的投資規模在疫情前和疫情期間的降幅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三)進一步分析
表3 的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我們采用負債柔性、現金柔性還是綜合指標衡量財務柔性,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期間的投資增量更多。那么,這一結果是否會因為企業的不同特征而有所變化呢?這一部分是按照產權性質分組的結果。通過表4 可以看出,DFF*POST、CF*POST、CDF*POST 的回歸系數均在民營企業組在1%的置信水平顯著為正。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2,與對照組企業相比,民營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期間的投資增量更大。

表4 財務柔性對投資增量的影響(按產權性質分組)
五、研究結論
新冠疫情帶來的全面經濟衰退使企業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歷程,但也提供了一次檢驗財務柔性儲備如何抵御不利沖擊的良好機會。本文以2019 年12 月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為背景,探討不同財務柔性儲備的企業在疫情發生前與疫情時期投資行為的差異。研究發現:無論采用負債柔性、現金柔性還是綜合指標衡量財務柔性,與對照組企業相比,財務柔性企業在疫情期間新增投資更多。進一步的檢驗發現,上述關系在民營企業更顯著。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國經濟面臨周期性衰退,企業面臨巨大的流動性風險。對于企業來說,保持適度的財務柔性,不僅能提高企業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更能使企業及時把握有力的投資機遇,更好的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