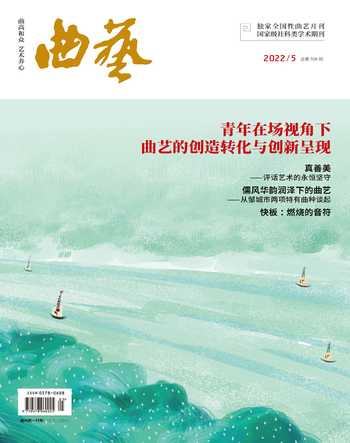評書不老 感恩傳承
關永超
當我第一次手捧著全國高等院校曲藝本科系列教材中的《評書表演藝術》,急急忙忙翻看目錄時,作為一名評書教員,我的心情是驚喜并澎湃的。仔細閱讀了田連元先生和他的女公子田潔老師共同完成的這部評書表演理論后,我體會到了填補空白的辛苦,很自然想起了說書藝人們的傳承之路,從口傳心授到學院教育的傳藝歷史,更多的是引起了我對跟隨田連元先生學習評書的少年時代泉涌般的回憶。那時候我們多么渴望有系統的理論教材啊。
說書,是關于說話的藝術。學習說書,如同嬰兒學話一般從頭來過,一步一步達到理解內涵、安排結構、組織語言,娓娓道來的表演境界,談何容易。為何要學習說書藝術呢?
幼時喜愛聽書,那是機緣巧合吧,電臺里播放著劉蘭芳先生的《岳飛傳》、單田芳先生的《隋唐演義》、袁闊成先生的《三國演義》,這是聽覺喚起的奇幻世界,一直到電視評書藝術的出現,我才第一次領略到了視覺中的說書人風采,真是“狀文狀武我自己,好似一臺大戲”。電視中的說書人是“本溪歌舞團田連元”。播講的故事是《楊家將》,田先生塑造的寇準,幽默而正義,讓我印象最深。
隨著中國北方曲藝學校的建立,說書藝術終于有了專業的學習殿堂。1990年,我從西安考到了天津,坐到了中國北方曲藝學校長篇書專業的教室里。國慶節剛過,入校一個月的我們聽到了從遼寧請來名家授課的喜訊,據說就是電視機里說書的田連元,和同學們一樣,心中萬分驚喜。教室的門輕輕推開了,田老師輕盈走入,暗灰色西裝,頭戴一頂灰色禮帽,平易近人,他摘下帽子,微笑著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田連元。”然后忙跟李慶良先生欠身致敬:“慶良叔,您一向都好吧。”專業負責人王文玉老師連忙正式介紹,我們的掌聲隨即響起,田先生再次起身微微鞠躬示意……熒屏上生龍活虎的田連元先生在生活中竟然如此儒雅謙和,我們的心靈是震撼的。
田先生的教學是嚴格而溫和的,原則不退讓,耐心而平和。在講述中的形體動作是我們學習的難點重點,立體評書不是復讀機,說演并重,尋求統一,往往讓我們詞句斷續,手足無措。初學表演,田先生反復告誡我們要撕下表演的這一層“僵皮”,勇敢些,思考清晰些,逐步規范之。這些教學實踐規律在這本《評書表演藝術》中都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評論,是評書藝術中靈魂所在,僅有講述的精彩遠遠不夠,畫龍點睛的點評才是最見功夫的。田先生用“說演評博”4個字概括了要義,開闊了思路。我們學藝時的評論是按照老師給出的腳本背誦的,若按照對全部故事的升華理解的高標準要求則相差萬里,為了學透徹,需要老師一遍遍分析講解人物的處境與心態。學說《楊志賣刀》時,對楊志的心情,從出身名門講起,用大量的書外書勾勒了人物的性格成因線索,這才讓十六七歲的我們對賣刀這一情節帶給楊志的恥辱感有逐步深刻的理解。
講述得精彩是田連元先生的藝術特色之一,體驗人物的心理,才能表達出靈魂深處的情感,南北名家大多有此功力,但那是從廣播里聽出來的,我在現場看到田先生演說人物時眼中的淚光閃動,《包公案》李后的自述,寇珠的慘死,經田先生演述出來,說者動容,聽者傷情。求教于前卻難以把握,而今在教材中,從理解、節奏、模仿、虛擬多個角度展開了論述。
關于創作能力的培養,田先生在教學中一再強調。無論長篇還是短制,他的作品都有很強的“田氏風格”,僅從文字上就可以閱讀感知。小時候很難看到或者聽到那么多田先生的評書,有一大部分是在出版發行文字里感受到田先生風采。他整理過的很多評書讀著讀著就笑了,那是在學校的閱覽室里。
突破傳統題材的局限,田先生的創作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從《鏡花緣》改編到《遼沈戰役》《為信仰而奮斗的人們》等。這一種創作方向,是從《追車回電》《九枚硬幣》那個時代就開始逐步突破并取得成功的。
我們從田先生口中聽到了評書評話大師們的不同風采,袁闊成、金聲伯、吳君玉、單田芳、唐耿良、陳青遠先生等,尤其是天津評書前輩,陳士和的《聊齋志異》、于樞海的《大刀王五》、顧存德的《水滸》《聊齋》等,他的講述不保守,不偏見,客觀公允的授課給我們這些學生娃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當時長篇書專業組的教師團隊中,三位教師有兩名來自天津,一位李慶良先生,一位王文玉先生,田連元先生高度自覺地配合學校總體安排,沒有一點名家的架子,真是難能可貴了。
一晃30年,田先生一生的說書心得盡在此書中,評書傳承不僅需要作品表現,更需要理論支撐,說書藝術之所以能與時俱進,傳承久遠,就是因為有了田連元先生這樣優秀的師長。
兩年學藝時間太短,畢業后還能繼續學習嗎?我上學時,田老師說他是不收徒的,文玉老師同樣不收,慶良先生輩分太高,不宜收徒。1992年,田先生辭去教學任務返回東北時,依然是我隨車相送。在天津站進站口,我與老師揮手作別,那時想,做個評書專業的畢業生也可以繼續自學說書啊。畢竟藝諺有云,修行在個人呢。
1993年,我留校任教,之后我們師生間的溝通就全靠文字書信,再后來有了固定電話了,都是老師打過來,那時一個小時的長途電話費都是老師負擔著。2004年,在崔凱老師和遼寧曲協同事們的勸說下,田老師打電話通知我:最近要收兩個徒弟,其中有你。那天我自己喝得暈乎乎的,到沈陽拜師時,也是酒醉酣眠半夜渴醒了。拜師田連元先生那一年我30歲。
看著這本《評書表演藝術》,我的思緒如潮,從學生時代的課堂學藝,到后來田先生定居北京后的登門問藝,又有20年光陰了吧。祝賀教材出版的同時,再次祝福老師健康長壽,藝術常青。
(作者:中國曲協評書藝術委員會委員、天津藝術職業學院曲藝系評書表演專業教師)(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