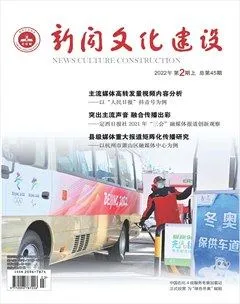媒介變更下的“名人”符號價值
張雨馨
摘要:符號是一種可感知的對象,通過媒介使其實現價值意義,網絡時代的到來,打破了過去以主流媒介壟斷的格局,擁有新渠道的群眾利用自媒體成為當下信息輸出的主要力量。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改變了符號的價值呈現,而名人符號亦是最敏感的地帶,本文將以符號中的名人符號(中國)為切口,分析其在不同時代背景下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并討論當下自媒體時代,媒介與名人符號價值中存在的矛盾沖突及原因。
關鍵詞:符號;名人符號價值;媒介
一、符號與媒介
符號作為濃縮表意的存在,可以任何形式包括且不限于象形圖像、文字、聲音或是某種精神象征來呈現。在現代符號學的體系中,結構主義創始人索緒爾提出了“能指—所指”符號二元說與德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所闡釋的“再現體—對象—解釋項”三元理論對其作出了基本定義。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這也是索緒爾提出的符號第一原則,這種任意性在現實中是約定俗成、不可論證的。[1]
符號的價值是無形的,它產生與實現的基礎是為了表意及滿足心理需求,同時,一個符號能形成可感知功能并實現其價值,需要媒介作為載體,起到儲存及傳播作用。葉爾姆斯列夫認為媒介即符號系統的“表達形式”,“媒介”的英文翻譯為medium,有著中介含義,[2]與媒體不同,更準確地說兩者是包含關系,媒體是媒介中的一部分,媒介與符號載體的區別在于:載體承載符號,而媒介讓這個感知得到傳送,傳播學中往往把媒介稱為“傳送器”。[3]而符號在傳輸過程中,“人與人”這個部分也是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同時空下的符號,它的生成、傳播、象征意義、價值都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過程并與當下的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人類思維等因素有著莫大關系,同時,媒介不僅僅作為一個渠道,在符號的表意過程中對內容具有一定影響。
二、“名人”符號及價值
大眾對符號的理解大多是一種象征性感知,通過某個符號能更便捷、更精準地指代生活中的某物,如看見紅燈就意識到停下腳步,從某個簡單的表情包即能快速了解對方所表達的情感。在認知體系中,一些符號具有象形意義,而一些符號更多偏向于象征意義。皮爾斯將符號劃分成三類:象似符號、指示符號、規約符號。[4]“名人”這一符號不具備象似性,不能使接受者有直觀快速的聯想反應,是一種較為抽象的存在。
(一)“名人”符號的表意
“名人”符號主要指向為象征意識層面,它所表達的內容需要進行二次解讀才能上升到具象形態,如因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們》而再次出現在大眾視野的演員寧靜,最直接的首層聯想是一個瘦瘦的、有著民族特色的女性形象,在進行第二層聯想后,又會與中性、時尚獨立等關鍵詞進行關聯,這就構成了更深一層的意指空間。名人符號的價值體現需要雙向呼應,如一個信號,首先需要發送信號的一方,其次要有接收的一方,當兩個步驟均完成時,此信號的意義才得以實現。“名人”符號的接收方需要得到“信號”并通過二次闡釋意義才算完整地執行了流程,同時,接收方要對該符號有一定的熟悉度,能作為進行聯想的前提,并且觸發移情效應,這三個階段是層層遞增的,針對接收者而言,還需對此名人符號的主體產生心理認同,其中包括對該符號的群體認同及社會文化認同。
符號的意義在于表意,但輸出的意義卻不是亙古不變的,在符號的表意范疇中,語境的不同也決定了“意”的不同。“語境”一詞由波蘭人類學學家馬里諾斯基提出,在語言學的范疇里大致可譯為“使用某種語言的當下環境”,馬里諾斯基將之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或稱“語言性語境”與“社會性語境”。語言語境指的是上下文,前言后語及段落篇章搭配組合等語言的自身環境;社會性語境則指語言發生的具體場合、文化背景、交流方式及目的等非語言性因素[5],將語境這一概念用至符號學中,可以理解為符號文本自帶的內容含義及其外界影響的衍生。語境順應著社會文化發展進行時效性變化,不同的時代背景會因當下不同的社會屬性、特征產出適配的時代符號,同時,某一典型符號也會因為語境的改變,而對其認知形成差異,“名人”符號即是如此。
(二)“名人”符號價值
“名人”符號寄寓了古代人民對生活美好的希冀,也記錄了人類征服自然、尊重自然、自我實現的心路歷程。作為源于生活卻突出于群眾的這一群體,神話中的名人符號代表著主流意識形態,傳達了一套較為完善社會道德觀念體系,具有社會性及榜樣性。
到了大眾傳媒時代與當下的符號消費時代,名人符號依然延續神話時期的兩種屬性,也順應主流認可的往符號價值越高的定律發展著,并且體現出新的價值屬性——商業性。
作為普通群體,個人行為舉止、形象大多只限于生存活動范圍里,但作為“名人”,其形象將會受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引起大范圍的輿論或模仿,他們需要比普通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因此,在大眾意識中,“名人”理所應當需要比普通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名人”應該是一個符合社會道德倫理并有著積極影響的符號。
大眾對“名人”長期的看法,也正是“名人”符號價值的體現。“名人”除了在各自領域中展示較高個人業務能力之外,德藝雙馨也是極為重要的。時尚芭莎每年舉辦的慈善晚會,邀請各領域名人,不僅自身參與捐款,也能帶動大眾關注公益事業。在每一個語境下,“名人”符號都起到了示范作用,是當下主流意識形態的濃縮,他們代表著所謂正統的價值觀、道德的標桿、社會的規則,也是群眾所模仿及追求的目標。但是,需要明確一個觀點,脫離出“名人”符號下的光環的這類群體,也是社會中的普通一員,生活中無法做到毫無瑕疵,這就需要在大眾視野下定制一副“人設”面具。瑞士心理學家容格在《心理類型》中提出的“人格面具”這一觀點十分適配名人這一群體,“他戴上了一個面具,并且只打造這個面具與他的意識意圖保持一致,同時,該面具也與社會的要求相契合,順應社會的輿論”。[6]可見,“名人”的人設問題,最大的發力點來自于外界,是社會、文化、經濟等多個因素共同打造的,“名人”符號可說是通過媒介創造的“神”的形象,進入符號消費時代,人設的打造與資本相互滲透,逐漸使“名人”符號衍生出商業價值。
三、媒介發展與“名人”符號
“名”需要媒介的傳播,普通群眾在日常中很少能真實接觸到名人本體,對于“名人”的認知主要來源于媒介的信息積累。媒介的內容生產和意義表達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媒介再現,它包含了復雜的媒介內容選擇、加工和社會文化符碼的植入,媒介內容隱含了特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其動機在于為了獲取權力或者其他利益。[7]
(一)古代的“名人”符號
提及“名人”符號,最早可追溯到古代神話時期,夸父追日、女媧造人等神話故事人物,那個時期的“名人”含義約等于英雄,他們高于民眾,能滿足大眾的訴求,同時,因符號生存環境較為純粹,媒介多依靠口口相傳,神的真實性亦淡化。
到了封建時期,人們的基本生存問題得到了保障。封建主義時期的“名人”構成基本上是文人,除了大眾的口頭相傳,最主流的媒介就是能抒發、表達自我的文字形式。此時符號傳播的媒介渠道還是較為單一,人類活動呈現出圈地形式,信息的傳播多發于某一集體內部,這導致集體與集體之間的溝通少,固定集體中的意識形態相對統一,表達的情感及內容同質化,因此對于“名人”符號的解讀,大眾不會產生過多標出性的觀念,這也為當時統治階層利用“名人”符號輸出社會價值觀提供了有利的環境。
(二)新中國成立后的“名人”符號
進入近代歷史時期,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上下全力投入生產建設當中,“名人”符號的構成多為革命英雄與勞模代表,各大報紙、書刊印滿了大慶油田工人王進喜、除“三害”的焦裕祿等勞動楷模,廣播里歌頌助人為樂的雷鋒事跡,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需要此類“名人”符號配合大眾傳媒來宣傳主流的意識形態,樹立榜樣性。
1978年,中國開始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飛速發展,大眾物質生活質量得以提升,開始追求精神滿足是“名人”符號價值的轉折點,大街小巷散發出生活氣息,鄧麗君即是那個時代的典型“名人”符號,一段婉轉而悠長的歌聲,是當時大眾心理需求的寄托。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電視這一媒介登上歷史舞臺,大眾認為電視等于“名人”,雖然依舊處于主流媒體壟斷時期,但信息量的增加以及信息之間的流通更為便捷后,大眾漸漸擁有了主觀選擇權,打破了原有固態的生活圈,對外界的渴望萌生出自我實現的意識,“名人”也成為大眾對自我價值實現的宿主。回想21世紀初,飯后之余人們談論的周杰倫、張韶涵等人,均以個性標簽出圈,關注名人業務及作品,誠然,其價值經歷了之前幾個時期的延續沉淀后,逐漸顯現出與其所匹配的新特征——輕松怡然的氣息徐徐散開。
以上的“名人”符號都是在各個時期社會經濟文化下形成的產物,發聲者仍是大眾媒體,渠道限制性較強,雖然有部分自我意識覺醒但輸出口徑還是相對統一,而真正產生巨變是之后的自媒體時代,自媒體的興起徹底打破了定式。
四、自媒體時代“名人”符號價值與范化
馬斯洛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8]在滿足了前4項后,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尋求更高一步的精神輸出。自網絡媒介登上歷史舞臺后,信息體量暴增,傳播渠道也呈現多元化發展,使得各界急劇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個較為健全的虛擬世界,大眾在這個時空中可完成現實時空有能力或無能力完成的個人動作,從而實現他們精神上的自我輸出,隨著長期慣性操作,現實與虛擬的界限逐漸模糊,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大眾的社交模式及價值體系。
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人們當下對于精神生活的執著,類似于神話體系中夸父對光明的追逐,是人類生命與生俱來的反應。也因如此,對于意義的執著,加速了符號泛化,瓦解了主流媒介掌控話語權的局面,過去口口相傳的群眾媒介與網絡空間高度融合后,成為這個時代中的體量最大的部分,微信、微博、抖音等各大網絡平臺,都是大眾展現自我、發表言論的渠道。名人符號最為典型,它不僅具有普通表意特質,還具有引導的附加意義,在符號泛化的大背景,名人泛化即是最大重音,具體的顯現特征為去精英化及娛樂化。
口頭相傳的時代,因媒介的自限性,導致傳播速度慢、范圍小,“名人”的數量也相對較少。雖然當今依然不乏像屠呦呦、鐘南山這類能在歷史上留下驚鴻一瞥的名人,他們的“名人”符號價值不能以經濟價值去衡量,但數量極少并且在大眾的熟知度、追尋度不高,相反,擁有大量追尋者的是那些與大眾距離較近的娛樂化名人群體。
微博平臺是當下縮小大眾與名人距離范圍的有效平臺之一,從平臺熱搜內容比例中,文藝類名人相關內容占比在50%以上。可見,在大眾視野里,文藝類名人即是當下“名人”符號的代表,但恰好文藝類名人在“名人”符號這個大環境中屬于精神文明領域,他們的社會貢獻無法實質化,符號價值更為抽象。籠統地說,即是這類人群在大眾認知里沒有做出某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使其轉化為傳統價值觀中具體貢獻,但又擁有“名人”符號的某些屬性,如關注度。所謂“亂世出英雄”,在過去生存問題、物質條件都還沒有保障的情況下,能改變生存環境,提高物質水平的名人當然是大眾高度統一認可的,回到當下的社會背景,生存物質基礎都較為完善,精神追求成為新的需求,再以傳統的“名人”符號價值來評判文藝類名人群體是不合適的。當下,“名人”符號價值的評判標準之一是流量,所謂“成也流量、敗也流量”,一個普通人可以通過自媒體展現自己的某種才能讓大眾熟知,此時此人確實具有了“名人”符號價值里的社會性,也就是所謂的網紅,然而,流量之所以稱為流量,“流”即說明它不具備長期以往名人符號的沉淀原則,可以發現,上個月還風風火火的網紅,近日就銷聲匿跡的常態現象,在流量時期,大眾通常只儲存當下記憶,與此同時,大量的造星計劃、選秀綜藝批量“生產”同質化名人,行為等同于在流量大波中淘金子,生產“快銷品”,僅以商業價值來衡量名人符號價值,忽視“名人”符號的榜樣性(貢獻與引導作用)。近年來,因私德“翻車”的明星不計其數,本質在于明星自身無法認識作為公眾人物的基本屬性,卻享受了“名人”符號所帶來的便利,這一點亦加重了大眾對“名人”符號價值的誤解。
在自媒體時代,接收方和媒介的融合程度加深,群眾依靠網絡平臺不僅擔任了接收方的角色,也成了當下媒介的主要輸出力量,在媒介構成比例改變后,主流媒介主導性仍然不變,但輸出的信息量明顯降低,無法達到過去統一的壟斷作用,形成了在媒介傳播的素質門檻低、大眾出現標出性觀念的現象。在這一循環中,“名人”符號的傳統價值、當下名人流量、群眾的仰望意識、對平等性追逐以及媒介結構的重組等眾多原因,使“名人”符號價值認知產生矛盾。
五、結語
名人的不斷涌現過程,是一種符號意義累積的結果,當上升到約定俗成的程度時,完成其象征化的意義,也是“名人”符號價值產生的重要表現,隨著媒介形式及構成的變化,“名人”符號也延伸出更多的意義。當今的“名人”符號在外界因素加碼后,呈現出去精英化及娛樂化的時代特征,如何使“名人”符號價值適配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僅需要名人提高各自專業能力,發揮榜樣作用,媒介輸出方也應有所意識,積極提升自我素養,多方共同完善。
參考文獻:
[1] 馮月季.符號、文本、受眾:媒介素養研究的符號學路徑[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3(4):95-99.
[2]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104.
[3] 趙毅衡.“媒介”與“媒體”:一個符號學辨析[J].當代文壇,2012(5):31-34.
[4] 閆文君.名人:傳播符號學研究[M].趙毅衡,唐小林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
[5] 同[4].
[6] 容格.心理類型[M].吳康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394.
[7] 同[1].
[8] 馬斯洛.人的動機理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