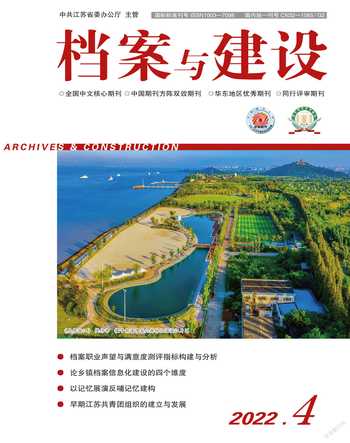憶江陰要塞策反工作(上)
仇英 唐大津 朱芳芳

我的愛人唐堅華(1924—1986),1939年在中學讀書時,就隨其堂叔(中學教師、中共地下黨員)開展地下黨工作。1940年在新四軍一支隊蘇北抗日軍政學校和抗大五分校學習。194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畢業之后任新四軍連隊指導員。1945年調到地方之后,歷任區、縣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他在解放戰爭中擔任策反江陰要塞的政治交通員,參與創建了江陰要塞的地下黨組織。
1947年春,唐堅華在上岡任副區長。中共建陽(今江蘇建湖)縣委書記樹海派他到江南去從事地下工作,說:“上級黨指示,要積極開展打入敵區工作。根據縣里掌握的情報,唐君照的弟弟、你的叔叔唐秉琳在偽江陰要塞,他手里有兵權,派你去做他的工作。通過你的父親(唐碧澄)找唐秉琳同你接上關系。”樹海問唐堅華有什么困難,唐堅華考慮到自己是上岡的區長,面目是“紅”的,如果被逃亡分子認識了,會有損于黨的工作。樹海說:“將全家搬到江南去,佯稱是逃亡地主,以掩護你的工作。如果有人認識,就說是逃亡出來的。”并寫了一封密信交唐堅華帶給他的父親,并囑咐要絕對保守秘密。唐碧澄原任鹽阜地區副參議長,于1946年秋天由曹荻秋和江華同志派往江南,執行黨交給的任務——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統戰上層人士、待命而動。唐堅華回家做我的工作,要我接受樹海對全家的派遣,明確提出要我沿途為他的工作打掩護。當時我在建陽縣邊區永豐區文教股工作。時值國民黨瘋狂進攻解放區,天天下鄉“掃蕩”,形勢十分緊張。我們配合武工隊、縣總隊在邊區打游擊,搞宣傳活動,穩定群眾情緒。我們常常到封鎖線附近貼標語,主要是墻頭標語,揭露蔣介石破壞談判協定、打內戰和蔣軍的罪惡行為,宣傳國民黨不長久、共產黨必勝,以及組織群眾跑反,組織兒童團站崗放哨,等等。唐堅華認為,我作沿途掩護,一是可以模糊敵人的視線,二是多一個人,可以多注意發現敵人的監視和盯梢,三是沿途買車船票、生活起居、吃住等都可以由我處理,他可以極少露面,少暴露。唐堅華還一再囑咐,要絕對保守秘密,不要同任何人講,他的母親、弟妹也不行。唐堅華母親長期在解放區,多次見過陳毅、黃克誠、曹荻秋、樹海以及其他中共黨政領導干部,聽過不少革命道理,也是有一定政治覺悟的。不對她講,只是要保密而已。既已定局,我服從革命大局,由樹海向政府文教科長孫達伍直接調動。唐堅華的母親、弟妹隨后也搬往江陰,全家一起站在了對敵斗爭最前線。建陽縣副縣長陸逵和糧食局長閑平批準辦理了一萬斤小麥,作為干部津貼和安家費。自此,策反江陰要塞起義的工作開始了。
唐堅華與唐秉琳接上關系之后,建陽縣委考慮策動要塞兵變責任重大,決定上交蘇北區黨委。建陽縣設宴為唐堅華送行,參加的有縣委書記王大林(樹海已調出),正副縣長楊兆熊、陸逵,社會部長蘇平,組織部長楊以希等。為了給唐堅華轉黨組織關系,鹽阜地委的社會部長高峰在飯桌上寫了個條子介紹他去蘇北區黨委社會部偵察科長江華處報到。后江華帶唐堅華去見了曹荻秋、陳一誠、宋學武等人。曹荻秋一見到唐堅華,就笑著說:“碧老的大公子來了。”
唐堅華匯報了同唐秉琳見面以及他父親的情況。曹荻秋、宋學武、江華都作了比較具體的指示:首先,要絕對保守秘密。區黨委由宋學武、江華領導唐堅華,唐堅華與唐秉琳單線聯系,不發生橫向關系。其次,抓兵權,抓實力,做好中下層的工作。拉攏下級軍官,團結可靠的人員,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待命而動。其三,如果有人認識,就說是逃亡出來做生意的。以逃亡地主、商人的面目出現,以“灰色”面目出現,堅守黨的秘密。宋學武還強調,必要的時候公開身份可以拋一點,絕不能泄露秘密。曹荻秋、陳一誠兩人各寫了一封信藏在香煙中交唐堅華帶給唐碧澄。從此這項工作由區黨委書記曹荻秋直接掌握,宋學武、江華具體領導。
唐堅華的工作,我從不過問,保證保密性。要做什么事,只做不問,如收藏密件、通行證、黃金等等。家人之間,和唐堅華的父母、唐秉琳等見了面,也只談家常。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連唐堅華十一二歲的小妹都知道注意周圍的動態,看到陌生人或第一次看見的人都要注意打聽這是什么人,房東家有什么人往來,有哪些人到唐秉琳家里去。每次往江南、回蘇北之前,唐堅華都要對我交代一番:“要絕對保守秘密,不要對任何人講,包括家里人。”“不管發生什么情況,寧可犧牲自己,絕不能泄露秘密。”
我們六下江南,在敵區來去共十一趟,四次到達,兩次受阻。
第一次是在1947年春,接受樹海的任務之后,我們帶了唐堅華母親到上海找唐碧澄。由唐碧澄到南京找來了唐秉琳,在一個姓高的人家里與唐秉琳見了面(姓高的不知道何事)。唐堅華告訴我說,“這次(與唐秉琳)相逢,遠遠勝過往日叔侄關系的舊情。我正面闡述了來意,他非常高興。這是同他正式接上了關系。我們還談了革命形勢,革命家常。劉少奇、陳毅、黃克誠、曹荻秋等同我們家庭都有過親密接觸,還談了唐秉琳的大哥唐君鄂在北撤山東時犧牲了,是烈士。二哥唐君照是鹽阜地委的組織副部長,三哥唐小石是射陽的縣委書記。我的三個弟弟都隨黃克誠部隊北上……這席談話更加堅定了唐秉琳的斗志和信心。這一次會見是可喜的,是有價值的,可謂揭開了策反起義工作的序幕。”
第二次是在1947年夏天。唐堅華和我在江陰唐秉琳家中,見到唐堅華的父親唐碧澄和他的弟弟唐明,他們也已從上海來江陰了。唐堅華告訴唐秉琳,這次工作已轉交到蘇北區黨委,并傳達了區黨委書記曹荻秋和陳一誠、宋學武、江華等人的指示。同時還研究了唐堅華全家遷往江陰的問題。這次唐秉琳提出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他講到“老五”(唐秉煜)也在這里(蔣軍中)。唐堅華很高興地說:“好啊!叫他們也來(我方),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并答應了回去向宋學武、江華匯報。唐堅華曾說過,他“力爭”“從速”解決他們的入黨問題。另外,唐堅華向唐碧澄轉交了曹荻秋、陳一誠的密信,唐碧澄也寫了復信交唐堅華帶回,仍藏在香煙中。從此江陰要塞地下工作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了。
第三次是在1947年秋天,唐堅華和我送唐堅華的母親、弟妹一家往江陰定居。他們住在青果巷一幢四進大住宅里。唐堅華家住第一進,唐秉琳住第三進,第二進是房東住,后進是廚房和勤雜人員居住。從此,這里就成了掩護唐堅華在江陰的聯絡點。

第四次是在1947年11月。華中工委成立后,蘇北區黨委相應撤銷,華中工委書記為陳丕顯、華中行政辦事處主任為曹荻秋、華中指揮部司令為管文蔚。仍然是宋學武、江華領導唐堅華工作。1948年1月,宋學武、江華通知唐堅華,經工委陳丕顯、曹荻秋、管文蔚、宋學武等領導研究決定:同意他的考察意見,批準他去吸收唐秉琳、唐秉煜、吳文廣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特別黨員,由唐堅華作介紹人。宋學武、江華決定帶五兩黃金(是金條斷開的四塊)給唐秉琳作治療關節炎費用。黃金藏在我特制的棉鞋里,左右各兩塊,穿在腳上。當時有一支部隊要過江,插進江南,宋學武、江華叫唐堅華的父親和唐秉琳準備火輪(輪船)夜間偷渡過江。后來唐堅華從工委回來說“不要了,部隊不過江了”,和我到了江陰他父母那里。他和唐秉琳談話后,叫我把五兩金子送給唐秉琳。我送去,唐秉琳叫我送給四媽(他的夫人)。一個隆冬的夜晚,在唐秉琳的家中,唐堅華帶領唐秉琳、唐秉煜舉行入黨宣誓。唐堅華對我說:“給他們(唐秉琳、唐秉煜)舉行一個簡單的宣誓,對他們是有教育意義的,時間不長。”我負責放哨,在一、二進來回巡視,黑夜伸手不見五指,天氣寒冷,幾乎被凍僵了。入黨儀式實際至少進行了兩個小時。
第五次在1948年春。宋學武、江華指示,“這次作較長時間地留在江南,至少半年,主要任務是有計劃地積極地進行發展工作,在有關部門安插和布置可靠人員,牢牢掌握住兵權。看樣子大軍快要渡江了。這次去的路線是從一分區過去,從東邊走旱路,由交通站護送過江。要長途步行,準備簡單的行李和換洗衣服。”我們從工委所在地射陽縣合德鎮出發到靖江,長途跋涉,通過重重封鎖線,十分艱難。行程約一個多星期。當我們抵達靖江時,敵人突然天天下鄉“掃蕩”,老百姓家家忙于逃命,交通站自動解散了。我們四處漂泊,心急如焚,吃住都成問題。更重要的是情況不明,無法到達目的地。我們在那里等待了一個星期,仍不見好轉,天天如此,只得又折回合德。
第六次,是回到合德之后,唐堅華向江華匯報之后,決定在合德裝一船棉花假裝商人從水路去江陰。此時已是1948年6月份了。途經泰州,被一些穿便衣戴袖章的敵人敲詐,抄出十幾兩黃金,扣押到一個警察所里。由于國民黨中統縣室插手,他們私吞了黃金,把唐堅華和我送到鎮江中統江蘇省室江照庵監獄坐牢半年。按照組織上指示的“以灰色面目出現”,我們始終堅持是“逃亡地主出來做生意的”,金子是祖上的遺產,拒不承認有任何政治活動。敵人沒有抓到證據,組織上多方營救,終于于1948年底交保獲釋。出獄后,我們繞道無錫回到了江陰,和唐堅華的父母弟妹一家人,以及地下黨的同志見了面。
我們往江南有兩條路可去,一是水路,從西面二分區乘船前往;一是旱路,從東邊一分區步行前往。
從西面去比較冒險,要“闖關”,要經過重重的敵據點、碉堡、哨所,還要防范出沒無常的自衛隊、還鄉團、穿便衣戴袖章的家伙等等。老百姓做生意的一般都從這里來去。西路是一路水鄉,有水蕩區,在蘆葦蕩里要通行兩三天。我們在那里行船是非常危險的,往往要好幾十條船一起“打幫”同行,趕到一個村莊住宿。大家互相傳話,“要跟上,不能落單”。十條船中可能就有八條會遭到水蕩中土匪搶劫殺害,在那里遭殺害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的。有人說有些小舟是來打腳(探子)的,不能同舟上的女子答話。幾十條船浩浩蕩蕩,似是一支水上大軍。只聽到撐船的水聲,沒有講話的聲音,大家配合默契,確有一派壯大的聲勢。每到一個村莊住宿,大家又緊張地互相叮囑“不準上岸,夜里要注意動靜”等等。進敵據點,首先要通過碉堡,戒備森嚴,有一種恐怖的氣氛。大家個個神情緊張,全神貫注地應對碉堡敵軍的盤查。輪到誰都要先送香煙,說好話,主動塞錢塞物,運氣好的查了證件放行。他們認為有油水可撈的,便三五個跳上船,揚言要搜查。這時要立即行賄,要送比較有分量的錢和物給頭頭,否則麻煩就大了。不僅人和物要扣押,甚至說你通“共匪”“替共產黨買物資”等等,貨物全部充公,人要坐牢。他們串通一氣分贓,發一筆橫財。每天都有一些船會受到如此遭遇。到各處車站碼頭都有哨所盤查看證件,住旅館也時常半夜來檢查證件。每次往江南回蘇北都要經過若干次的盤查。真是深入虎穴,深感莫測。站在對敵斗爭的最前線,無時無刻不在提防。
一次,唐堅華和我送他母親、弟妹往江陰,偽裝商人裝了一船大米,已到沙溝碼頭即將出售。突然來了五六個穿軍裝的要搜查,聲稱要查違禁品。看樣子是要大搜查了。他們拿著鐵釬在船頭船尾、大米中亂翻亂戳,沒有查到什么東西。但是一個頭頭腳上穿著皮靴,接過鐵釬,氣勢洶洶地要重查。唐堅華在船頭和他們周旋,我在船艙里看勢頭不對,分明是敲竹杠的。這個家伙來到船艙門口,我未等他進艙,立即拿了三塊銀元塞進他的皮靴里,結果他什么也未查,帶領幾個人到別處去查了。還有一次,唐堅華和我在興化的輪船上,突然來了十幾個憲兵,對船艙上下層都進行搜查,還要看證件。那種陰森恐怖狀態下,乘客緊張萬分。火車站就更復雜了。一次唐堅華和我去火車站,我們站在遠處隱蔽的地方環視了下,看到穿便衣的、穿制服的,腰間藏短槍、不三不四的人逛來逛去。還有一個女的穿一身美國式的黃軍衣,燙發很長,面色蒼白,可能抽白面子,逛來逛去,所有的人都避開她,就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也不敢靠近她。唐堅華說這個女人可能是軍統特務。看到這種情況,我們找了一家偏僻的小飯店,唐堅華在那里等,由我去買火車票。等火車快到站了,我們才進站,混在跑單幫的人群里,立即擠上車。以后我們不敢再坐火車了。長途汽車似乎要平靜一些。
從東邊去是一條長途步行的旱路。我們隨身只帶了一些簡單的行李和衣服。為了長途跋涉方便,又帶了一匹小白馬。我們輪流騎,交換休息,但我騎得多。唐堅華和我從工委所在地合德出發,途經龍王廟,在白茫茫的大路上前進。記得經過秋湖(同音)、雙樓(同音)、一倉、二倉、三倉、海門、紫石縣、靖江縣等,途中要經過幾道封鎖線。交通站只護送過封鎖線。沿途是無邊無際的荒草灘和鹽堿地,既無人煙,也無樹木,滿目荒涼。來往皆部隊同志,三五人、七八人,也有一二十人的,有少數的地方干部,沒有老百姓。沿途大家都主動互相打招呼:前面還有多遠?到什么地方?有人家可住宿?同志加油呀!這些地方荒涼有土匪,不能掉隊!等等。午飯之后,就互相招呼:同志,要趕快趕路!一定要在太陽落山之前趕到某地方!太陽落山之后,土匪就要上來了!等等。每到一個地方,基本要急行軍,才能趕到目的地。老百姓家里差不多都住了人,晚去的住宿往往比較困難,好的是大家都是同志,都主動招呼:“來!我們擠一擠”。沿途沒有水喝,更無用水,三餐都是咸水,海風、咸風吹得皮膚干裂,口腔干燥發炎,鼻子不斷出血。我當時有身孕,身體就更差了。皮膚、衣服、被子幾乎都是濕的,臉上生鹽霜。每到一處,老百姓都很熱情,幫助燒飯打地鋪。老百姓都很苦,雜糧也吃不飽,生活極其簡單,沒有家具可言,鍋蓋是玉米稈子做的。大麥枧子、玉米枧子、咸菜、醬就是很好的招待,沒有油,沒有鮮菜。他們還不好意思地說:“沒有好的給你們吃,你們也夠辛苦了。”麥草、玉米稈子打地鋪,大家累了,也睡得很香。第二天清晨,大家都主動打掃干凈,群眾紀律很好。早飯后向主人告別,我們多給些錢給老百姓,他們總是不肯多收。一次我們趕到一個地方,看到一家門口有幾個老百姓在吃飯。他們一家人很熱情地歡迎我們,幫我們拿行李、牽馬、喂飼料,為我們安排吃住。他們的生活很苦,除了一點不豐富的主食雜糧和草,別無其他。菜里幾乎沒有油,無葷無蔬菜,吃用水十分困難。
我們沿途到靖江要經過二三道封鎖線。封鎖線是敵人控制的一條交通線,有一條通行軍用車的大公路,以及與公路平行的一條大河。由交通站的武裝護送,約一個排的全副武裝。由這邊交通站護送過封鎖線,那邊交通站的武裝迎接護送到站。交通站護送必須在夜晚進行,在封鎖線兩邊必須各距離15里左右,行動才比較安全。一兩個小時前放前哨。等天黑了很久,才能行動。不準大聲講話,不準有任何聲音,腳步聲也極輕,不準吸煙,不準用照明器。緊要時傳話很輕。為了迅速過封鎖線,必須跑步前進約各10里,即20里左右。過河的船準備好等待,撐船沒有一點水聲。我們幾次通過都很順利。我是女同志,已有身孕,站里特別安排了兩個人照顧。在跑步前進的時候,基本是他們架著跑。一次一分區留守處干部科的李科長,特地前去交代交通站的同志要用擔架護送和派專人照顧。我一再推辭:“派人幫助就很好了,擔架就不用了。”交通站的生活既艱苦又緊張,吃的小米,常常飯不熟就催著開飯,一碗還未吃完就又出發了。好的是有一點青菜湯,當時青菜成了最需要的高級營養品。睡的是玉米稈子大通鋪,被子自帶。交通站離敵區都比較近。一次我們在三倉交通站,是個隆冬的深夜,突然槍聲響起,交通站的同志報警,還鄉團就在前面的莊子上,帶領我們在流彈狂飛、子彈嗚嗚聲中作了轉移。我們長途跋涉,來到了靖江縣,本應由交通站護送過江,很快就到江陰了。誰知敵人天天在黎明前就下鄉“掃蕩”,抓人搶東西,交通站就自動解散了。老百姓東躲西藏逃命都來不及,我們也無處安身,安全完全沒有保障。而且在那里幾乎言語不通。我們心急如焚,主要是為不能過江而焦急。我們在那里等待了一個星期,唐堅華天天奔跑找地方干部,最后地方干部說看樣子最近不會好轉,情況緊張,得不到情報,不知敵人是什么目的。因此我們只好又回到合德。
我們走的這條路線基本上是邊區,是一種游擊環境,群眾生活不安定,隨時要準備跑反。交通站也只是送過封鎖線,過了封鎖線各自前進。我們身上都有黃金、密件,主要機關又常常轉移,為了安全和保密工作,唐堅華往往要跑好多地方,才能找到主要領導機關和主要領導人,安排我們吃住和下一站的行程,一天吃一兩頓是經常的事情,半夜了才得以安排住宿。東路雖然危險性比西路小些,但也相當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