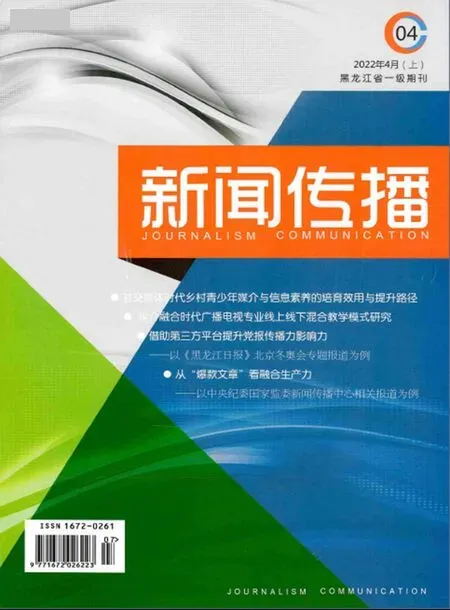融媒體時代新媒體的使用動機實證研究
——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
華婧楠 金香
(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吉林 133002)
一、研究背景
“媒體融合”是國際傳媒大整合之下的新型模式,是把傳統媒體(報紙、電視臺、廣播電臺)和新媒體的采編播作業有效結合起來,原始素材資源共享,信息集中整合,衍生出多種形式的融媒體產品,然后通過不同的平臺傳播給受眾。
隨著新媒體越來越向縱深發展,這種新型整合作業模式已逐漸成為國際傳媒業的新潮流。匡文波(2008)研究中提出新媒體概念,指出新媒體是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進行的傳播,區別與傳統媒體是互動性,已經不再是傳播者-受眾,新媒體使每個人不僅有聽取的機會,而且有說的條件。
我國有2800個縣級行政區,擁有全國大多數人口,在相對不發達的縣城,人民群眾需要通過媒體傾聽黨和國家的聲音,并希望自身的需求能在媒介使用過程中得到滿足(馬艷,2019)。截至2020年底,我國各大縣級城市建立融媒體中心,開展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融合發展,主要表現于開設專門網站、電臺APP、微信公眾號等。雖然融媒體中心對信息的傳達及互動為體現國家戰略而努力,但是目前我國的研究大量是傳統-新媒體轉型期的理論研究(柳竹葉,2015)。因此,本文以不同的研究視角為切入點充分了解新媒體用戶的使用需求是什么?能否用使用與滿足理論加以解釋?與傳統媒體的使用有何關系?帶著這樣的問題本文采用定量方法來深入揭示新媒體使用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的相關關系,為我國媒體融合事業快速發展帶來相關理論依據進而促進融媒體的可持續性發展。
二、文獻綜述
本文采用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該理論與大眾傳播效果理論不同,他是以用戶(傳播受眾)為對象,分析用戶對媒體的需求及動機,從而判斷傳播的內容或方式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Smock,2011)。
馬昀禹等(2019)依據使用與滿足理論初步判斷新媒體使用者動機因素主要包括:娛樂性動機、求知性動機、表達性動機、情感寄托性動機四類。陶程成、朱立冬對移動短視頻APP用戶持續使用意愿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發現,用戶的社交需求、認知需求和自我展示均積極影響用戶使用行為;用戶使用行為顯著影響滿足感,進而顯著影響用戶持續使用意愿,但是娛樂需求只顯著影響內容消費行為,對內容生產行為不產生顯著影響。
我們國家對融媒體的研究相比國外較晚,大多停留在宏觀微觀的理論研究層面,較少關注用戶的使用動機是否滿足現在的媒體使用實證分析。基于此,本研究運用定量方法,探討融媒體時代新媒體使用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的關系。具體以縣級新媒體用戶為研究對象,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進行問卷。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利用使用與滿足理論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用戶對媒體的需求及動機,從而判斷傳播的內容或方式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問卷調查是2020年10月15日到11月15日,對縣級新媒體使用用戶180人進行無規則抽樣進行問卷調查。其中,有效使用問卷是149份,收集的數據使用SPSS24.0進行技術統計、因子分析、交叉分析等進行檢驗。
(一)變量的測量
問卷使用Mee Eunkang(2000)驗證的問項,共26項,其中娛樂性動機9個、求知性動機6個、社會關系性動機11個,人事信息統計6項。
娛樂性動機是用戶通過使用新媒體獲取相關信息時從中感到心情愉悅舒暢,并在大腦深處產生進一步使用的欲望;具體的問項內容是“能帶給休閑娛樂”“為了轉換心情”“能帶給快樂”“為了解壓煩惱的心情”等9項。
求知性動機是用戶通過使用新媒體時,可以獲得相關專業知識拓展自身知識儲備量,從而產生繼續使用的欲望;具體的問項內容是“為了看地方新聞”“為了看全國新聞”“為了看國際新聞”“為了解決相關問題”等6項。
社會關系性動機:用戶使用新媒體時可以滿足其表達欲望,可以加強其在社會上與他人的互動和利用新媒體提供的方便窗口解決自身難題;“能使我感到不孤單”“為了和他人溝通”“為了體驗新的經驗”“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尋找便利”等11項。
(二)數據分析
表1說明在149份有效問卷中,從不使用新媒體的人數為13人(8.7%),偶爾使用新媒體的人數為49人(32.9%),經常使用的人數為87人(58.4%)。說明在被調查者中經常使用新媒體的人數遠遠大于不使用新媒體的人數。
問卷對象的人口統計學分析,男76人(51%)、女73人(49%),年齡分布18-19歲33人(22.1%)、30-39歲57人(38.3%)、40-49歲22人(14.8%)、50-59歲31人(20.8%)、60歲以上6人(4%),文化程度是初中12人(8.1%)、高中23人(15.4%)、專科37人(24.8%)、本科46人(30.9%)、碩士以上31人(20.8%),收入是3000以下45人(30.2%)、3000-5000是66人(44.3%)、5000-1萬是33人(22.1%),1萬以上是5人(3.4%),職業是學生14(9.4%)、生產人員34(22.9%)、辦公人員26(17.4%)、專職人員32(21.5%)、技術研發人員7(4.7%)、退休人員12(8.1%)、其他24(16.1%)。

表1:使用新媒體的頻率分析摘要表
(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相關性分析
為了證實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相關分析,本文運用了交叉分析法,對傳統媒體的使用程度如何影響新媒體的使用程度進行分析,并且證實兩者的關系。
表2表明,Pearson卡方的p值p<0.01有顯著性意義,因此傳統媒體的不同使用程度群體與新媒體的使用程度有所不同。結果表明不使用新媒體的人數有13人(8.7%),偶爾使用人數是49人(32.9%),經常使用人數有87人(58.4%)。數據可見,既不使用傳統媒體的人也不使用新媒體的人相對于其他兩項更多;偶爾使用傳統媒體的人更多也是經常使用新媒體的人;經常使用傳統媒體的人也會經常使用新媒體的人較多。這個結果和MeeEunKang(2000)的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相關關系有效性研究結果相同。

表2:使用傳統媒體和使用新媒體相關性分析
(四)新媒體使用動機分析結果(使用與滿足理論為中心)
為了證實新媒體使用動機的影響結果,首先對新媒體使用動機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時可觀測變量的特征、性質及內部的關聯性,揭示哪些主要的潛在因子可能影響這些觀察變量。
表3因子分析是最大似然方法,直接Oblimin方法旋轉,旋轉后成分矩陣刪除不顯著的題項3項。結果表明,KMO統計量為0.862,大于最低標準0.5,變量之間相關性較強。Bartlett球星檢驗p<0.001,拒絕單位相關陣的原假設,解釋的總方差累計69.686%,適合做因子分析。因此,得出觀測變量求知性動機(Cronbachɑ=0.847)、娛樂性動機(Cronbachɑ=0.850)、社會關系性動機(Cronbach ɑ=0.893)。

表3:因子分析
(五)影響新媒體使用的因素分析
為了證實新媒體的使用動機與新媒體的使用程度之間關系,進行交叉分析檢驗卡方的顯著性,進而驗證不同程度的新媒體的求知性使用動機如何影響新媒體的使用程度。
表4結果表明,Pearson卡方的p值>0.05,因此求知性動機需求的程度差異對新媒體的使用程度沒有產生顯著性相關關系。

表4:求知性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相關性分析
表5結果表明,Pearson卡方的p<0.05,有顯著性意義,因此娛樂性動機的高中低群體程度差異對新媒體的使用程度存在統計學顯著性差異。

表5:娛樂性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相關性分析
表6結果表明,Pearson卡方的p值>0.05,因此社會關系性動機對新媒體使用程度沒有顯著性差異。

表6:社會關系性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相關性分析
四、結果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融媒體時代新媒體使用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新媒體使用程度與傳統媒體使用程度有顯著性影響關系;傳統媒體的不同使用程度群體間對新媒體的使用程度有顯著性意義。這為新媒體是否可以代替傳統媒體的研究提供有效依據。
在求知性動機對新媒體使用程度的影響研究中發現不同程度的求知性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沒有顯著性意義;這說明求知性動機的程度與新媒體的使用程度沒有相關關系,這個結論可以探析新媒體所提供的知識信息是否滿足了用戶的需求。
在研究娛樂性動機對新媒體使用程度的影響過程中發現不同程度的娛樂性動機與新媒體使用有顯著性意義;這說明新媒體的娛樂性滿足了用戶欲望,也可以探討如何帶著娛樂風格且做好“新聞傳達者”。
在社會關系對新媒體使用程度的影響研究中發現不同程度的社會關系性動機與新媒體使用程度沒有顯著性意義;這說明目前縣級融媒體對外發布的相關內容滿足不了用戶的社會方便需要及通過窗口增強個人利益。
五、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樣本的抽樣存在局限性,建議今后相關研究者可以收集更多縣級新媒體使用用戶進行調查;本文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動機變量和尺度參考了國外文獻的已經驗證的問項,今后研究里我們可以自行開發符合我國國情的相關問項;最后,本文是采用橫向研究,今后可以進行縱向研究,從而更好地支持假設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