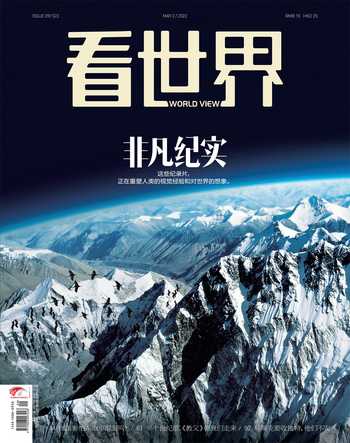我在長崎探尋中國歷史
樓學

長崎港口
長崎的地景由重重歷史地層堆疊而成,而在漫長的時光中,這些地層被一次次折疊。
作為一名來自中國的旅行者,我在這里旅行,仿佛在不同歷史間跳躍、穿梭。長崎保留著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史跡與街區,這趟異國旅程,最終與我所熟知的歷史片段聯結在一起。
我很少在日本看到如此具有中國風的城市。
長崎坐落在九州島的西岸,一直以來就是面向中國及朝鮮半島的重要口岸。從1633年以來,日本延續了兩個多世紀的閉關鎖國政策,而在這段歷史中,長崎一度是江戶幕府唯一開放的對外通商口岸—這樣的歷史地位,約略等同于廣州之于中國。也由此可以想見,在這樣畸形的外交及貿易政策下,長崎享用了幾個世紀的繁榮。
華人是最早來到長崎及外海的外國人群體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王直。
在東亞歷史上,王直有著截然不同的兩副面孔:對中國而言,他是明朝海禁政策的抵抗者,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倭寇;而對日本來說,他是書寫一代傳奇的“大明儒商”和“五峰船主”,也是他將葡萄牙商船帶到了種子島、平戶島,成為天主教傳入日本歷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
在王直之后的17世紀,日本最重要的兩大貿易國正是中國和葡萄牙。但江戶幕府對待兩國態度的差異耐人尋味:葡萄牙人被限制在遠離長崎城區的出島上居住, 而中國人只要不是信奉天主教,就不會被限制具體的居住地點。
唐人屋敷四周有城壕、柵欄圍合,只有通事、藝妓可自由出入。

唐人屋敷誘導門
這一政策直到明朝滅亡之后,隨著大量中國商船擁入長崎,長崎官方才在市區附近的丘陵地帶,另外劃定了專屬的“唐人屋敷”,算是“中國城”的1.0時代。
在當時,這片唐人屋敷可供兩三千人居住,算是一片特殊的“飛地”,四周有城壕、柵欄圍合,只有通事、藝妓可自由出入。
不過,大片密集的木屋總是暗藏火災隱患。歷史上,在最嚴重的幾次火災中,中國商船的倉庫曾被徹底焚毀。于是,華商不得不在附近的海岸線上填海造陸,作為新建倉庫的用地,后來的“新地”即由此得名。
1858年,在日本結束鎖國政策之后,許多華人就從原來的唐人屋敷搬往毗鄰的新地。如此算來,新地町的唐人街歷史其實不太久遠,可算是長崎“中國城”的2.0時代。
山坡丘陵上那命途多舛的唐人屋敷,如今勉強還有遺跡可循。在今天的館內町一帶,我們還能找到幾塊不起眼的古跡石碑,標記出昔日唐人屋敷的邊界。在日本開埠、唐人屋敷盡數廢棄之后,一些福建移民在昔日故址修建了福建會館,設立了處理工商事務的組織—如今的“館內町”一名,其實也與福建會館有關。
館內町與新地町比鄰而居,見證了華人進入長崎的早期歷史。如今,新地町的中華街號稱“日本三大唐人街”之一。
在一個不太起眼的路口,我找到了一座近年重建的“誘導門”,它通往已經湮滅的唐人屋敷。沿途的路牌上,偶爾閃現過“唐人坂”“館內町”的地名,頑強地保留著來自大海另一岸的古老記憶。
在新地町與館內町北面不遠,一條小河潺潺入海,日人喚之為“中島川”,它是長崎的母親河。

崇福寺山門以及第一峰門牌匾
在長崎,這條小河以河面上一組17世紀的古橋群聞名,這些早期石橋的修建者多來自中國。
其中最著名、最古老的一座就是“眼鏡橋”。這也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石拱橋之一。眼鏡橋很早就成為長崎的地標,與東京的日本橋、巖國的錦帶橋并稱“日本三大名橋”。
眼鏡橋其實是興福寺參道的一部分—中島川上的幾乎每一座石橋,都通往附近風頭山上的專屬寺院。
1624年,來自中國的僧人真圓在長崎開創興福寺,這是長崎最早的華人寺院;由于信眾多來自江南地區,寺院也常被稱為“南京寺”。
相傳當年有許多中國移民渡海而來,因隨身攜帶媽祖雕像,被日人以為是天主教中的圣母形象而頻遭刁難,因此最早的興福寺中其實供奉的就是媽祖。
直到十余年后,來自江西的高僧如定成為興福寺的第二代主持,寺院規模大大擴展后,才補齊了漢地伽藍格局。那座古老的眼鏡橋,也是在如定任上建成的。
日益增多的中國移民,使宗教禮拜的需求大大增加。在當時,長崎有四座名震一時的恢弘寺院,由于其創建史都與中國移民有關,合稱為“四大唐寺”,分別是江浙贛移民修建的興福寺、閩南移民修建的福濟寺、福州移民修建的崇福寺和廣東移民修建的圣福寺。
如今,四大唐寺中最有文物價值的當屬崇福寺。盡管其開創時間比興福寺略晚幾年,但崇福寺保留著長崎最好的明朝式樣建筑。1629年,福州僧人超然成為開山祖師,和興福寺類似,起初也是供奉媽祖的小殿,后來才慢慢整備為一座大型的寺院。
1646年,在明朝已經壽終正寢時,身處日本的福州移民為寺院增建第一峰門和大雄寶殿,當時連木材也是從中國遠道運來。這兩處增建的建筑還頑強保留了原真的明朝式樣,共同被列為日本的“國寶”。
除了列為“國寶”的第一峰門和大雄寶殿,護法堂內供奉著韋陀菩薩,在大梁上留著1731年修建的墨書題記。尤為難得的是,護法堂內的插拱、纏藤都有著鮮明的閩地特色,而山墻上的裝飾卻是日本風格—可見后期的崇福寺,已經逐漸融入了日本的本土文化。
寺院所屬的黃檗宗,在日本佛教史上聲名顯赫,是僅次于臨濟宗和曹洞宗的第三大禪宗流派。而黃檗宗的祖庭,就在福州府的福清縣。
1945年8月9日上午,美國人在長崎丟下一顆名為“胖子”的原子彈,在這次核爆中,四大唐寺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福濟寺、圣福寺被焚毀,崇福寺因遠離原爆點而幸運保存。崇福寺也是除京都、奈良以外文物建筑最多的寺院之一,甚至有“西日本第一寺院”的美譽。

長崎孔廟
要說長崎最著名的中國地標,恐怕不是唐寺或中華街,而是那座華麗龐大的孔子廟。
1878年,清朝在長崎設立了領事館,定居于此已有數百年的長崎華人終于有了來自母國的領事機構。1893年,領事館在清廷和華僑的共同支持下,主持修建了日本唯一一座中國式樣的孔子廟。它擁有完備的孔廟形制,儀門、泮池、大成殿、崇圣殿等一應俱全。
孔廟如今成為了中國歷代博物館,我到訪時恰好趕上介紹魯迅與新文化運動的臨時展覽,逛完一圈下來,再次對中日文化的千絲萬縷唏噓不已。
當年捐資修建孔廟的華僑群體中,最主要的仍是修建唐寺的幾大鄉幫。不過他們或許想不到,孔廟落成之時,甲午海戰已經一觸即發,東亞格局又要迎來一次劇變。
眼鏡橋很早就成為長崎的地標,與東京的日本橋、巖國的錦帶橋并稱“日本三大名橋”。
實際上,在甲午海戰爆發前近10年,長崎上空早已陰云密布,中日之間的硝煙味道,早就彌漫在孔廟不遠處的港口上。
1886年,當時號稱亞洲第一艦隊的北洋水師在丁汝昌的帶領下訪問長崎,卻有幾位清軍水師官兵在長崎違反軍紀、擅自上岸,最終導致水師官兵與長崎警民的嚴重沖突。頗為吊詭的是,一貫羸弱的清廷這次表現出罕見的強硬態度,竟然還取得了一次難得的外交勝利。
這一沖突雖以清廷的勝利告終,卻最終成為一條草蛇灰線。在此后不到10年,日本與清廷的海軍實力就發生了逆轉。不知道在甲午海戰時,當年曾親歷過“長崎事件”的官兵們,面對全軍覆滅的北洋水師,又要做何感想。
好在這處迎送過中國僧人、商船與水師的長崎港口,始終是與中國交流溝通的前線。1971年,長崎是最早喊出“只有一個中國”的日本城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長崎又派出了第一個訪華的日本地方自治團體。
盡管沒能趕上著名的新春燈會或中國盂蘭盆節,但在長崎的街巷、寺院和料理中,我仍然時不時尋見中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