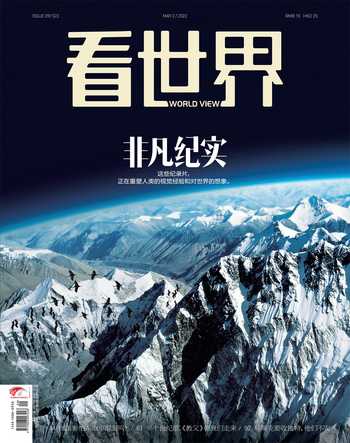《幽靈線:東京》為何難演《生化危機》輝煌?
馬點秋

《幽靈線:東京》游戲壁紙
大學剛畢業的你,收到了一家平平無奇公司的offer,開始了朝九晚五的社畜生活。漸漸地,你發現公司的員工越來越少。
起初,你并沒有太在意這件事。直到有一天晚上,結束加班的你準備回家時,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突然眼前一黑。再度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變為惡靈,并被告知,只有繼續去詛咒并殺死下一個人,自己的靈魂才能得到解脫……
這是近期發售的動作冒險類游戲大作《幽靈線:東京》中,一個支線任務的劇情。這款首次曝光于E3 2019游戲展上的游戲,在當時即引發了廣泛討論,不僅因為其具有游戲創意總監(中村育美)濃厚個人風格的、觀感極佳而又充滿懸念的游戲預告,更因為游戲獨有的、以“道法驅鬼”為核心的主題玩法。
游戲中最主要的攻擊模式,是用手指結印,施放咒術。
這樣的第一人稱射擊游戲,給人以極大的新鮮感;輔以日本都市傳說中常見的“裂口女”“幽靈線地鐵”等元素,以及“生化危機之父”三上真司Tango工作室出品的加持,不得不說在當時吊足了人們的胃口。

“生化危機之父”三上真司
然而,在發布會高調亮相的中村育美,在半年后即主動提出離職,游戲又在2021年7月宣布延期,至今才在《艾爾登法環》《小緹娜的魔幻之地》等大作頻發的情況下正式發售,可謂命途多舛。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一部被玩家戲稱為“林正英模擬器”的驅鬼游戲,以及日系恐怖游戲的未來。
趕工制作,抽離體驗
首先,就筆者通關這款游戲的感受而言,游戲的品質只能達到勉強及格的水平。
不得不承認,夜色下絢爛的東京夜景,在地標性的澀谷全向十字路口,被詮釋得淋漓盡致;霓虹燈在水面和大樓玻璃上的反射,在光線追蹤的加持下也栩栩如生;結合人口憑空消失神隱的背景,在游戲開篇給人一種強烈的孤獨感,與同樣類型的游戲《死亡擱淺》中,面對末世的孤獨和無力感相似,給人一種強烈的探究事實真相的驅動力。
雖然活人沒幾個了,但街道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妖魔鬼怪,相當熱鬧。
但優秀的游戲開場,幾乎是游戲唯一讓人感到驚喜的地方。開始游戲后,你會逐漸發現,雖然活人沒幾個了,但街道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妖魔鬼怪,相當熱鬧,讓開篇所營造的孤獨感蕩然無存。
而生澀的第一人稱跑動視角,讓人有一種“飄”著行走的感覺,主角使用的元素攻擊方式也只有風、火、水三種,區別只有攻擊范圍和頻次不同,并沒有之前玩家猜測的,屬性相克和技能連招搭配等日系游戲常見要素。
游戲中,敵人的種類也少得可憐。主線任務“跑路”成分過多,搭配那缺少動作捕捉的過場動畫演出,以及平淡無奇的劇情,更是讓人頻頻出戲。
這些“硬傷”和游戲大地圖上雜亂不堪的各類標志一起,處處透露著預算不足的趕工痕跡,以及對開放世界游戲理解的不到位。相比之下你甚至會覺得,育碧那飽受詬病的“流水線型”開放世界式游戲,都算精品。
而游戲中,升級所需的關鍵素材“靈魂”的獲取方式同樣離譜:靈魂散落在東京市區的各個角落,只能用主角手中數量有限的小紙人收集。

《幽靈線:東京》創意總監中村育美

《幽靈線:東京》以“道法驅鬼”為核心的主題玩法曾引發了廣泛討論,游戲中最主要的攻擊模式是用手指結印,施放咒術
但紙人的數量初期僅有十余個,一旦收集滿了,就要去電話亭“上傳”靈魂后才可繼續;一次上傳的靈魂數僅有千余個,但需要收集的靈魂總數有24萬個—靈魂收集系統,仿佛只是為了刻意延長玩家的游玩時間而制作。
支線任務的質量還算不錯,比如在文章開頭提到的任務中,玩家需要找到大樓中導演這一出惡作劇的最初怨靈,并將其封印超度,解除大樓的詛咒,解救被困于其中受盡折磨的靈魂。
但這仍舊無法拯救游玩過程中,始終存在的那種“抽離感”,仿佛玩家只是這一事件的旁觀者,不斷被游戲中蹩腳的設計,從沉浸式體驗中抽離開,并為自己錢包中失去的194元扼腕嘆息。
更換制作人,謎之操作
那么,《幽靈線:東京》究竟是如何從2019年的一鳴驚人淪落至此的?
個中原因,可能只有實際參與了游戲開發的人員才能說清楚。這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三個名字:三上真司、中村育美與B社。
《幽靈線:東京》是由知名游戲制作人三上真司創立的、位于日本東京的Tango Gameworks負責的游戲作品。而三上真司最出名的事跡,當屬在1996年發布了自己在Capcom(卡普空)的處女作《生化危機》,開創了在隨后的20余年間席卷全球的喪尸類游戲、電影、動畫熱潮。
但這一游戲系列的續作,實在歷經坎坷:二代推倒重來,三代倉皇上馬,四代更是在推翻的諸多企劃案中,衍生出了《鬼泣》這一游戲系列。
雖然《生化危機4》無疑是系列中最優秀的作品,但執意在當時機能更強的任天堂NGC主機獨占的三上真司,最終和老東家卡普空鬧得不歡而散。
隨后,這一傳奇游戲制作人和另外三位大神一起,創立了白金工作室,制作了評價頗高卻“叫好不叫座”、銷量平平的《絕對征服》,再之后獨自創立Tango Gameworks,以《惡靈附身》這款硬核恐怖冒險游戲一炮成名。
這也是三上至今為止親自參與制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其之后的精力放在了公司經營和培養新人上;“給年輕人更多機會”,成了他近年來最多談到的話題。
《惡靈附身2》交由1代的視效設計師John Johanas負責,而中村育美作為《惡靈附身》及其續作美術部分的負責人,同樣受到了三上真司的極大重視。據說《幽靈線:東京》最初的創意,便源自中村育美本人的構想。
在E3 2019展會上,當作品與玩家初次見面之時,三上真司更是讓中村育美站臺,為游戲進行宣傳,在推特上取得了十分熱烈的反響。可見,三上十分重視中村育美這一人才。

《惡靈附身2》游戲壁紙
他下一款親自監督的游戲,會是其職業生涯的最終作。
但中村育美卻在半年后,于Tango Gameworks主動離職,隨后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以接取各類游戲外包業務為生。《幽靈線:東京》的開發,繼續由《惡靈附身》的制作人木村雅人,以及導演木村憲司負責。這一系列的操作實在令人不解。
加入B社,動蕩不已
外界存在一種猜測,是B社(Bethesda)近年來的動蕩與壓力,讓《幽靈線:東京》團隊“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Tango Gameworks在2010年創立之初,便面臨資金人才匱乏的窘境,同年便被B社的母公司ZeniMax Media收購,成為了擁有《上古卷軸5》《輻射》《DOOM》等知名美系冒險大作IP的B社旗下的眾多游戲工作室之一。
然而加入了B社后,除了2014年發售的第一部作品《惡靈附身》好評如潮,Tango Gameworks與B社近年來的日子都不算好過。不但《惡靈附身2》口碑銷量不佳,B社向“服務化游戲”進軍的網游《輻射76》在發售之初,也因bug過多,而差評如潮。
之后,其對MOD社區官方化的嘗試,在玩家的反對聲浪中宣告失敗;企圖擺脫Steam搭建的自有游戲平臺,也即將在近期停止服務。
這一系列的操作,讓曾經光鮮的B社逐漸走向衰敗—或許這也是,最終導致B社和ZeniMax Media在2021年初,被微軟以75億美元收購的原因。
而2019年底開始暴發的新冠疫情,也讓許多游戲開發團隊遭遇了相當大的困難,以至于近年來的3A大作屢屢踩雷,佳作屈指可數。
總的來說,就和各大媒體7分左右的均分一樣,《幽靈線:東京》雖然為我們呈現了射擊類游戲的全新玩法,以及栩栩如生的澀谷夜景,但游戲存在的諸多問題,只能讓其成為一款相對平庸的作品。
即便如此,作為Tango Gameworks在非恐怖類型游戲領域的大膽嘗試,《幽靈線:東京》值得鼓勵。三上真司曾表示,他下一款親自監督的游戲,會是其職業生涯的最終作(《惡靈附身3》在玩家中的呼聲非常高)。希望Tango能夠越來越好,在恐怖游戲越來越不受待見的當下,挑起這份重擔,重現當年《生化危機》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