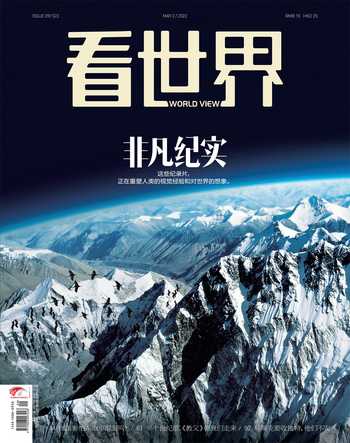盧旺達如何治愈集體狂熱?
鄧晨

“正常”與“瘋狂”如何判別?最常見的標準,往往是人的心智是否“脫離現實”,然而細究起來可沒那么簡單。
龐大的人群也可能會陷入集體狂熱,或追求難以實現的目標。這當中的每個個體會覺得,身邊的人有著同樣的認識,所以自己的想法再合理不過,是屬于最主流、最受支持的判斷,而不跟隨潮流者才是欠缺現實感的。
瘋狂只有在個體的精神疾病中,才顯得易于辨認:一般人憂慮感染癌癥是很普遍的想法,但如果辦公樓的某個員工沒來由地擔心廁所里藏著怪獸,這似乎就是很明顯地“脫離現實”“不正常”。
集體狂熱也屬于瘋狂的一種,而且當集體狂熱造成的災難消退之后,留下的可能是難以療愈的創傷及精神疾病。
1994年4月的盧旺達種族屠殺就是很切合的例子。災難過去28年后的今天,許多幸存者仍受到創傷后癥候群、抑郁癥,乃至精神分裂癥的折磨,難以找回平穩的生活節奏。
據估算,當年盧旺達的700萬人口中,有近80萬圖西族人及少部分的胡圖族人遭到屠殺。參與屠戮者可能超過100萬,遭受強暴凌辱的女性達50萬人。
當圖西族部隊控制局勢之后,有近200萬的胡圖族人逃至鄰國。這場災難使得所有幸存者的生活都扭曲破碎。世衛組織估計,盧旺達全國約有10%的人繼續承受精神癥狀的傷害,但是盧旺達的精神療愈體系卻十分孱弱。
按照一般人們所熟悉的現代精神醫學典范,典型的精神治療可能是昂貴的一對一心理諮商,或是依靠化學藥物去介入心理狀態。在大屠殺發生后,也有許多外國醫療人員前往當地支援。但很顯然,歐美的躺椅式精神諮商是不適用于當地情境的,盧旺達醫療體系必須發展出自己的方式。
其中,重要的就是社區化的團體康復治療。
盧旺達發展出來的模式,可被稱為“人我共愈”。這種模式將同個社區中的10—15位鄰里居民組成治療小團體,每個團體由兩名治療師引導定期聚會。驚人之處在于,這種團體刻意包含了加害者與幸存者,通過彼此開放地傾聽對話,重建彼此間的安全感、信任及尊重,再次建立起共同生活的基礎。
盧旺達在大屠殺結束后,約有12萬加害者被送入監獄,但是囚犯的數量讓監獄難以負荷,大部分囚犯終究會獲釋。在早期就發生過很多犯人出獄后再度被捕的情況,其中不少人為了湮滅犯罪證據甚至將受害者滅口,這讓社會上的幸存者人心惶惶;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加害者恐懼遭受被害人家屬的報復,渴望得到原諒、重新做人。
不論是什么樣的瘋狂行為,在當事人的心靈中必然產生過一套合理的推論,重返正常社會生活意味著必須建立新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舊的一切才得以消散或拋諸腦后;在一般的心理諮商中,這或許主要是個體的身心旅程,但在盧旺達的情境中,這必定需要居民之間相互的理解與確認。
很多陷入創傷與精神分裂癥的受害者,或許永遠無法康復。但對于許多民間社區居民來說,“人我共愈”這樣一種重新社會化的過程,為每個人再次提供了共同生活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