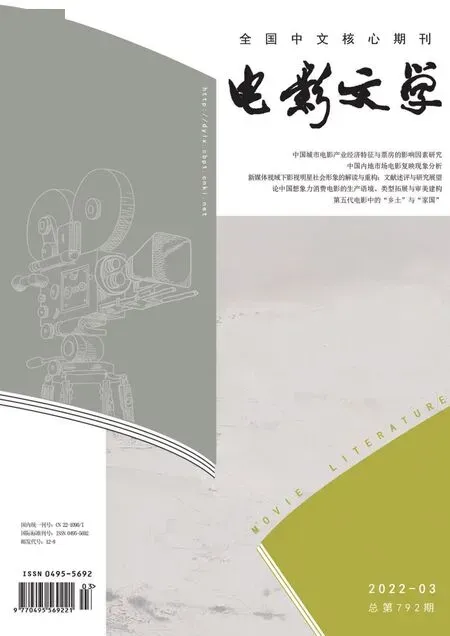第五代電影中的“鄉土”與“家國”
包 蕾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北京 100024)
20世紀80年代,自“五四”以來又一個具有文化啟蒙意義的人文復興高潮,在飽經了“文革”浩劫的人性泯滅、社會全面倒退后,以另一種“革命”方式——改革開放,令人們滿懷熱忱與期待、激進而狂喜地擁抱世界和現代化進程的華彩時段。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分子都充斥著對西方(彼時是社會先進文化與雄厚經濟實力的代名詞)的憧憬與追隨、對小康/幸福生活的渴望、對健全合理社會的期待、對“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覺醒、對“知識改變命運”的信仰……
一切事物都在經歷了傷痕、反思后,以一種全新的姿態脫穎而出,傳統與現代仿佛以水火不容的態勢代表著守舊與變革、愚昧與文明、落后與先進。在這種近代社會發展史從未曾出現的電光石火的作用下,第五代伴隨著家國命運破曉而出是必然的歷史機遇與宿命,早一刻或晚一刻,他們都會錯過加速前進的歷史巨輪,辜負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
第五代電影以“時間對空間、歷史對生命、造型對故事的勝利”,標志著一代人的崛起。在這種可以以電影手段隱去時代痕跡,凸顯導演敘事及美學構想的總體氛圍下,在絕大多數是由當代作家小說改編的文學腳本故事里,除了作者已經明確規定的情境(如《紅高粱》《霸王別姬》《金陵十三釵》等),時間可以被虛化挪移,地點可以被放在某一處極具地方傳統文化特色的人文場景或地域,人物的背景和個性可以進行再度創作,生活風俗可以設計出上不封頂的臆想片段,并以一種“偽文化”或“偽民俗”的面貌出現。在這種可以“篡改”的前提下,第五代在反思批判的同時,也在不自覺地踩出一條通往西方的“捷徑”,要想通過這條“捷徑”穿過“窄門”,“意味著他們必須認同于西方電影節評委們關于藝術電影的標準與尺度,認同于西方之于東方的文化期待視野,認同于以誤讀和索取為前提的西方人心目中的東方景觀”。
一、民俗傳統渲染下的儀式中國
電影中表現的儀式,是創作者表達內心情感最直接的宣泄和表達方式。
第五代導演一方面在“尋根”——發掘民族文化、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從而喚醒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則在啟蒙(他們亦是被啟蒙的一代人)——發掘民族文化中殘存的“劣根性”,批判并否定其中的封建糟粕(然而有些時候是以一種渲染集錦的方式),這不得不說是一重悖論。
正如陳捷在以“現代性”眼光來審視第五代的“傳統性”時所評價的:“在第五代的電影中,他們獨辟蹊徑地將民間文化與具有原始性與‘異域性’的少數民族文化視作他們認同的‘傳統’和要追尋的民族文化之‘根’,而他們所要批判的恰恰是一種以‘現代文化’面目出現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是現代中國以來的文化傳統,前者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而后者是沒有生命力的文化。”這其中“以‘現代文化’面目出現的‘傳統文化’”,是攝影機前的景觀,也是當代作家或編劇理解中的“傳統文化”,但其表現形式因為主題先行而被誤認為是正統,這也是電影能指與所指的特性所決定的。
儀式,從遠古時期的祭祀、圖騰崇拜開始,就在人類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義。儀式中所包含的民俗,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地區的居民/人民長久以來基于生產實踐活動而形成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審美情趣等文化現象,體現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文特點。民俗形態與社會形態、歷史背景和經濟狀況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內涵,也是第五代導演取之不盡的寶藏。無論是方言、地方戲、飲食、風俗等,絕大多數觀眾在想起第五代電影的經典場景時,第一反應除了那些深入人心的畫面外,都會對一些民俗片段記憶猶新。
民俗作為最基本的日常,涵蓋了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秋菊打官司》里秋菊地道的陜北方言,孩子滿月時做的“花饃”等令人目不暇接的各色面食,為這部以同期聲錄制的、強調紀實美學的影片營造了真實可信的場景氛圍與濃郁的西北氣質,幸而“社火”在其中只是出現了短短兩三個鏡頭,否則又會喧賓奪主讓觀眾感覺到一種人為刻意;《千里走單騎》的“百家宴”,令高倉健飾演的男主角感到震撼,并對一方水土孕育的深厚的鄉親之情有了深刻的理解和頓悟;《我的父親母親》中的民間手藝——“鋦碗”,用特寫鏡頭完整拍攝了巧手將原本不可能的已經破碎的碗重新用金屬給恢復“縫合”,這在現代社會是不可思議的手藝,但在那個物資匱乏的時代,這既是物盡其用的巧思,也體現了電影中母親對父親的深厚感情。民俗被挖掘也被再次創造,巧妙融入影片中,成為具有強烈表現力和人文感染力的有力細節。
張藝謀的《紅高粱》,是一曲禮贊生命與激情的電影詠嘆調,其中的“顛轎”“燒酒”“敬酒神”等,伴隨著迎風颯舞的高粱葉和如血殘陽,成為觀眾過目不忘的經典段落,也成為中國影史中非常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橋段。在有限的地域特色文化中尋找符合思想主題、人物性格和敘事需求的元素,民俗成為既可以具有鮮明外在張力和視覺效果的表現形式,又是能夠肩負承載傳統文化內在精神的最佳載體;同時,在導演進一步渲染打造和凸顯下,民俗又綻放出不一樣的時代風采,成為第五代電影迅速獲得國內外關注的關鍵因素。
針對這種文化現象,文化學者王一川曾經這樣評價張藝謀的“民俗”技法:“從中國審美——藝術文化的轉化角度看,張藝謀的作用也是重要的。在他之前,中國藝術的主潮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啟蒙文化,其基本任務被認為是對大眾實施詩意啟蒙,即用活生生的藝術形象感染大眾,向他們傳播理性。而張藝謀的橫空出世,打亂了這種詩意啟蒙節奏,顯示出‘娛樂’因素在藝術中的日漸增長及其重要性。張藝謀電影中那些讓人或贊美或指責的著名鏡頭,如顛轎、野合、酒誓、封閉的陳家大院等,在今天看來其實不過是藝術中不可缺少的新奇娛樂因素。張藝謀不過是較早地示范而已。”
可以看出,民俗成為第五代導演早期影片中具有娛樂效果的“作料”,點綴在故事線之間,成為頗具視覺沖擊力和地域文化色彩的有效手段,既有著文化痕跡和傳統意味,又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兼具表形和表意的功能。張藝謀先人一步的敏銳的藝術洞察力,為其個人的品牌打造提供了重要支撐,但也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逐漸形成定式的“民俗”呈現,逐漸失去了生機而淪為一種奇技淫巧。
陳凱歌《黃土地》中的腰鼓、祈雨、信天游等,同樣是這種以簡單敘事為主線,以激昂、振奮的民俗儀式/禮儀規矩作為全片華彩段落的路徑,對古老的農耕文明進行了愛恨交加的反思與展現。時至今日,觀眾可能已經記不太清電影中的故事情節,但是仍然會對那幾個極富爆發力和視覺沖擊力的場景記憶猶新,這可能也是藝術處理后的地方民俗帶給觀眾的獨一無二的精神烙印吧!
《霸王別姬》(1994)作為陳凱歌電影作品的巔峰之作,在無數觀眾心目中已經成為經典中的經典。在這部以京劇演員、人物為主線的影片中,梨園行、戲班子、天橋賣把式、堂會、服飾行頭、“同光十三絕”“牡丹亭”“貴妃醉酒”……數不盡的細節、曲目圍繞“國粹”——京劇鋪設繪就了舊時代的生活質感和氛圍,高度還原了一幅“北平”風情畫卷,為觀眾呈現出極具真實感和可信度的故事場景,同時也通過營造出流光溢彩的舞臺與兵荒馬亂的動蕩社會之間的強烈對比,烘托出了“下九流”人物不可自已的悲劇命運。
這種在編劇、導演可控范圍之內,以一種適度集成和全景展現的手法,將京劇文化/老北平人文,糅合在主人公程蝶衣“人戲不分”的劇情發展之中,成為有力助推劇情發展的核心因素,既為觀眾帶來了跨越時空的審美愉悅,又為劇中人物的命運走向提供了可信服的客觀依據。在這部影片里的傳統文化展現,尚在合理的尺度范圍之內,不僅沒有讓人覺得刻意虛假,反而為影片增添了華美而余韻未了的中國傳統文化魅力。
《菊豆》(1990)、《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作為張藝謀兩部具有一定爭議的影片,其中的敲腳、點燈滅燈、吊嗓、扎小人、染坊、宗祠等,多數已經成為影評界對其詬病的情節。兩部影片的象征意味尤其深厚,拋開陳家大院的“囚牢”意象、妻妾成群卻互相碾壓的殘忍“后宮”文化、染坊染池頗具視覺沖擊力的色彩所營造出的特定情境與封閉壓抑的影片整體基調,封建半封建時代對于女性的摧殘和吞噬仍然給觀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卻淪落進另一種以“偽民俗”為噱頭的怪圈中。
這種原著小說中并未涉及和描寫的內容,被導演“安插”進影片,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藝術“虛構”,但是這種脫離現實、嘩眾取寵的渲染手法,逾越了電影現實主義歷史控訴和文化批判的邊界,成為一種程式化、模式化的他者景觀令作者迷戀和展示,成為一種藝術創作心態與人物心理扭曲雙重疊加后的異化。很多學者目睹這一怪現象后,不無憂思——“作為精英的第五代實際上通過他們的影片放棄了對于民族文化和道德危機的思考,遠離了對現實民眾生存境遇的人文關懷,從而注定達不到精神信仰層面上的悲天憫人的終極關懷境界。”
彼時,第五代之前的中國電影,因為認識和視野的局限性,對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都市、工業化等西方社會具代表性的文明標志,還是存在一定抗拒、憂思甚至是恐慌的,回歸到鄉土中國才是“吾心安處”的所在,盡管他們深知這片土地存在的問題可能更加久遠而頑固。單方面的詩意已經無法將內在困境進行突破與化解,如果此時仍然沒有一種更為嘹亮而另類的聲音打破這種沉寂與失語,那么中國電影的走向只有顧影自憐這一條出路。
第五代的鄉土,與之前的刻板印象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它不再是第四代作品中單純意義上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寧靜淳樸傳統守舊的田園,也不再是站在現代工業化都市對立面的積貧積弱的代名詞,她成為一種包容混雜著欲望與活力、蠻荒與滯重,蘊含著壯美到秀美、熾烈與蒼涼,潛藏積蓄著黎明前即將噴薄而出的力量的宏大“母體”,即以一種亙古不變的姿態應對著社會動蕩與巨變的“空間對時間的勝利”(戴錦華語)。
這種“勝利”,飽含著種種無奈和絕望,直接體現在電影中,則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呼應著銀幕外轟轟烈烈的20世紀80年代思想文化的劇烈激蕩;也是從這一刻開始,鄉村與都市的二元對立,在改革開放的前提與氛圍下,成為需要共同面對被批判被重新審視境地的統一體,即鄉村所蘊藏凝聚的千百年來形成的地域文化同樣也孕育了一種生機勃勃的爆發力與可能性,而都市因為西方/現代化的沖擊也淪為人心、傳統的放逐之地和迷失之境。
二、“胡煥庸線”分割下的鄉土中國
鄉村,抑或鄉土的角色進行了延展與變遷,第五代偏愛“西部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們把很多原著小說里并未指明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安插”了進來——不僅取景在西北部地區(《一個和八個》從河北拍到了寧夏,《黃土地》在陜北高原,《孩子王》《盜馬賊》《獵場札撒》《邊走邊唱》《炮打雙燈》《秋菊打官司》《千里走單騎》《三槍拍案驚奇》等皆是以西部地區作為故事發生地),更是展現了一部原始蠻荒、充滿傳奇想象和民俗奇觀的畫卷,將文學語言的想象幅度與電影寬銀幕畫面質感的幻覺幅度結合起來,營造出一片現代社會文明之外、固守著數千年如一日傳統的、亟待拯救與關注的神奇土地。
看得出,第五代或多或少也受到了西部片的影響,不只是因為在中國西部同樣有類似美國西部“開闊但令人感到絕望的荒野、封閉沉悶的驛車/轎子、愚昧但生猛的人和黑暗的小鎮”這樣鮮明的西部片類型元素,更是鐘情于西部獨有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意境,這份高遠蒼涼令他們深深震撼,并以此作為直抒胸臆、涂抹潑墨的空白畫卷。然而,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背后,僅僅是因為他們其中的少部分人曾親身在那里下鄉這么簡單嗎?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20世紀我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所發現的“胡煥庸線”,即“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是中國人口地理上極具影響的一條分布線,一直為國內外人口學者和地理學者所承認與引用,并且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田心源教授稱為“胡煥庸線”。
這條貫穿我國東北地區至西南地區的“璦琿—騰沖一線”的發現(后被稱作“愛輝—騰沖一線”)在地理學(尤其是人口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以及人類學、社會學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性意義。
這條線從黑龍江省璦琿(1858年清政府和俄國簽訂《中俄璦琿條約》的所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1956年改稱愛輝,后改稱黑河市)到云南省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基本直線。線東南方的中國國境內43%國土上居住著我國95%以上的人口(計算結果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為依據),該片土地以平原、丘陵、水網、綠地和丹霞地貌為主要地理結構,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是沙漠、草原和雪域高原的世界,也是自古游牧民族馳騁的天下。一條看似稀松平常的直線,卻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劃分出兩個迥然不同、存在天壤之別的自然和人文地域。
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成為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分割線。處于這條線東南部分的各省市,城市化水平、現代化水平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是GDP的主要來源地;而這條線的西北各省區,除少部分擁有礦藏屬于資源依賴型和輸出型地區外,絕大多數經濟發展情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是中國扶貧攻堅的重點區域。
自古以來,中國東南植被豐富、人杰地靈,西北氣候嚴酷、地廣人稀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沒有人對這種未經證實的認識加以有力的論證與推斷。“愛輝—騰沖線”的發現則在理論與實踐范疇內廓清了這一分界,影響極為深遠,成為研究和決策我國各項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而它的得來,是胡煥庸對當時中國人口在不同地區的分布密度進行了點狀統計,發現全國96%的人口分布在該線東南,他將成果寫成論文《中國之人口分布》,于1935年發表在了《地理學報》。
一條“胡煥庸線”勾勒出自然、地理、文化差異懸殊的中國,亦是一幅影像中國的文化版圖——線以西是唐代邊塞詩描寫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景象,那里是馬背上的民族粗獷、豪邁、壯烈的風情,民風彪悍,驍勇善戰;而該線以東則是農耕文明、小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細膩俊美但人口稠密的人文景象。不可否認上億年的地貌、氣候變遷和影響,令人們不得不做出“逐水而居”的選擇,往更適宜人生存的環境遷徙,但這條分界線不僅區分了人口、經濟、氣候、水文等社會學、人類學的因素,有學者在著作中評價道:“它還是一條文明分界線:它的東部,是農耕的、宗法的、科舉的、儒教的……一句話,是大多數人理解的傳統中國;而它的西部,則是或游牧或狩獵,是部族的、血緣的、有著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國。”
當年為《黃土地》采景時,幾位主創很機緣巧合地來到了黃帝陵,他們虔誠而忘我地駐足參拜,那一刻,他們頓覺自己的渺小與卑弱,對于祖先的崇敬之情更激起了這些赤子的豪情與壯志。于是,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對農耕文明愛恨交加的民族感情,痛定思痛、渴望進步的民族反思,這種對個體命運和國家命運的思考深深地融合進了他們的作品之中。正如張藝謀在作為《一個和八個》攝影師時就已形成的個人美學風格——“構圖平面、單純、視點離奇和線條清晰,嗜好大片天地中極小的人影,偏愛靜止的畫面和時間的停滯。這一切,與其說是他攝影風格的流露,毋寧說是他生命意識的投射:天之蒼蒼,地之茫茫,人生渺小,滄海一葉。”
三、“文化鄉愁”視角下的開放中國
“傳統的厲害之處就在于它是歷史,而人又是歷史性的存在,傳統已經化為我們的行為模式、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對于傳統、傳統文化,一概否定、盲目否定都是有失公正客觀的,在剖析和批判之前,首先應該具有冷靜而清醒的自我意識,“先認識,然后再去考慮丟掉還是不丟掉的問題。認識,是第一位的”。如果在尚未有完整而客觀清晰的認識之前,就下結論做動作,這種冒進與激進,只能說明自身還是存在一種無法克服與解決的焦慮。
20世紀是中國社會接受外國文化(此處特指西方文化)最為直接與激烈的時代。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創造的東、西關系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被當成是“傳統”和“現代化”的關系,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中,東方常被當成是傳統的、古老的,西方才是現代的、新興的。這段話不無殘忍地直接揭示出近代世界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差距”與偏見,而電影恰好是一種可以超越偏見的藝術手段,它直觀的畫面與聲效,只要情節大致符合常理不至于非常晦澀難懂,一般都可以引發觀眾觀看的興趣,作為了解一方文化的窗口和捷徑。
第五代電影人中,有些人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之后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出國潮”前往歐美學習電影理論,一部分人選擇在國外定居;另一部分人于世紀之交前后回到國內,重新開始執導電影。與前文提到的“78班”多位駐守本土的電影人不一樣的是,“洄游”的第五代,又從一個新的“文化鄉愁”視角觀察、看待改革開放初具成效的中國,這其中,錄音專業的寧瀛和導演專業的彭小蓮分別拍攝了“北京三部曲”和“上海三部曲”。
“小人物”的個體記憶與時代變遷、國家記憶的交叉互文,是第五代“文化鄉愁”所縈繞的漂泊感尋求停泊和安全感的最突出特征;返璞歸真的“回憶”與“溫情”,以及面對變化時的“焦慮”,是其最顯著的情感底色,而對改革開放尚留有傳統痕跡的社會氛圍、家庭生活的依戀和憂慮,成為影片的立意所在。在她們的影片中,“家”在“國”之前,是凝縮的社會。
在學期間就受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影響的寧瀛,影片始終以一種真實還原的樸素質感進行著當代中國的想象。《找樂》以陳建功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與之后拍攝的《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并稱為“北京三部曲”。電影刻畫了“老韓頭”這一京劇院傳達室認真執拗又可愛的退休老人,與一眾退休的京劇票友,不甘心被社會遺忘,自發舉辦京劇社團過程中的酸甜苦辣。
影片開場即是展現了熙熙攘攘的百貨商店、菜市場等充滿著20世紀90年代氛圍感的北京街道,時髦青年的裝扮提示著西方文化對傳統社會的影響。但老韓頭出現的場景,有混亂嘈雜的京劇院后臺,有戲迷票友們自發組建的天壇京劇角,有水汽氤氳、現在已經難尋蹤跡的澡堂子,有擺滿了冬儲大白菜、生活氣息撲面而來的菜市場……
所有的畫面信息都在提示著這是一個剛剛跨入市場經濟不久的、充滿現代活力與傳統遺跡的新興中國。電影主角對原小說進行了藝術拔高,不再是一個處于社會底層、滿口俗話俚語的老北京,而是一個自認為有一定京劇修養和號召力的小人物,熱心、負責、較真,不甘寂寞與忽視。他召集組織的退休票友,也各具特點,組成了一幅處于新舊交替時期的生動群像,由此產生了紀實美學的動人之處。

圖1 寧瀛影片《找樂》
《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都以表現北京土生土長的普通職業者作為切入點,胡同、筒子樓生活是他們熟悉的場景,前者是千萬基層干警(片兒警)中的一員,兢兢業業完成本職工作,抓瘋狗、帶新人、審慣犯……非職業演員的本色演出,長鏡頭、同期聲、中景的拍攝手法,為整部影片帶來了“78班”鮮見的貼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實感。
而《夏日暖洋洋》,以出租車司機德子離婚后與幾位女性的交往,帶出了世紀之交的北京人心的慌亂與迷茫。高樓與平房、古建與新地標開始同時出現在鏡頭中,急速推進建設的城市、貧富開始分化給普通人,甚至是原先帶有優越感的北京原著民帶來的強烈沖擊,與紀實鏡頭冷靜的態度形成強烈反差。而這一切,預示著老北京保留的傳統痕跡,不可逆轉地在逐步消失,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拍攝了“上海三部曲”(《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上海倫巴》)的彭小蓮,將自己對于家鄉上海的深情,投射在海派文化背景下,同樣是以表現時代變遷下的個體命運,從而刻畫出人心的動蕩與皈依。無論是石庫門、被多戶人家“占領”的老洋房,鱗次櫛比的摩天樓,抑或是百年未變的車水馬龍、燈紅酒綠,彭小蓮恨不得“大拍特拍”自己深愛的熟悉的上海。
在平復了“文革”帶來的創痛后,對往日繁華與榮光的追憶、對家族聚散沉浮的嗟嘆,在影片中以一種平靜而克制的鏡頭語言緩緩呈現。而我們甚至可以相信,《美麗上海》里王祖賢飾演的“小妹”,或多或少帶有導演自己的痕跡——一種試圖理解家人、融入傳統家庭,卻又因為常年在國外而與兄弟姐妹存在觀念差異。整部影片因攝影的曝光處理而顯現出濃郁的懷舊色彩。

圖2 彭小蓮影片《美麗上海》
作為海外學成歸來的“78班”成員,有別于張藝謀、陳凱歌等同學看待中國的視角、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以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電影胸襟、更為貼近百姓生活的創作姿態,敏銳觀察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現代化”之迅猛。他們一方面對祖國已經不是自己搭機留洋離開時的面貌而感到驚訝感嘆;另一方面預感到中國社會在激變中即將失去獨具特色的“文化之根”而無奈惋惜。一切都處于暗流涌動的狀態中,面對消逝的傳統,她們試圖通過鏡頭記述、留存時代的余溫,更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文化鄉愁”,維系著“游子”對故人的珍視、對故鄉的眷戀、對故土的不舍。
結 語
第五代電影早期的另類、不拘一格,實際上就是一場醞釀已久的革命。與第四代影片中不具特定區域特點、雷同的農村、鄉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第五代電影首先選擇以文明相對滯后的、非儒教的西部中國作為影片的發軔地。發聲即是一種吶喊,是一篇戰斗檄文,喊話對象就是這一片無可撼動的、孕育了華夏文明如今卻閉塞貧困的黃色土地。他們用攝影機喚起觀眾的注視,試圖再次撼醒這片沉睡的土地。進入相對成熟的創作階段后,他們開始用更為冷靜客觀的態度審視觀察、“反思”“尋根”,他們對于“鄉土”“家國”的認識曲線,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成長與社會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