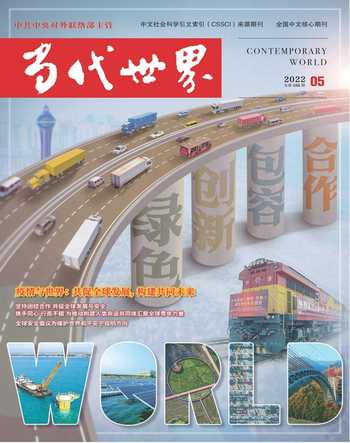超越西方傳統安全觀:全球安全倡議的時代價值
田文林

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在西方傳統安全觀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治主導下,世界局勢持續動蕩,戰亂沖突此起彼伏,經濟復蘇緩慢乏力,全球發展陷入停滯。俄烏沖突、大國博弈所引發的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議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不言而喻。
無論從歷史還是當下看,安全問題都是威脅人類社會的最大挑戰。在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疊加影響下,全球安全形勢加速惡化,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太平。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議的提出正當其時。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憑借其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先發優勢,日漸成為統治世界的主導力量。從安全角度看,西方主導下的世界歷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戰爭與沖突史。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戰爭與資本主義》中指出,14—15世紀期間,英國與法國爭斗了100年;在16世紀,歐洲只有25年的太平時光,而這一數字在17世紀縮短至21年。也就是說,在這兩百年里有154年處于戰亂。荷蘭從1568—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英國學者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指出,歐洲列強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策動戰爭,完全沒有戰爭的時間不超過25年。相比之下,東亞地區在1590—1894年間享有300年的和平,僅僅出現了幾次規模相對較小的兩國間戰爭。很顯然,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至少與東亞地區相比),西方列強主導下的世界充滿了戰爭與沖突。西方列強在對外征伐過程中更加窮兵黷武,熱衷于訴諸戰爭和暴力,并最終塑造出一個以“叢林法則”為底色的野蠻而血腥的等級性世界體系。
表面看,西方列強憑借軍事優勢和對外征伐,在世界政治中維系了長達數百年的優勢地位,但無處不在的零和博弈與戰亂沖突,使整個人類社會遭受了難以估量的災難和損失。據統計,1871—1914年間,英國進行了30場殖民戰爭。在此期間,英國、法國和荷蘭至少打了100場戰爭。這些殖民戰爭造成了28萬—30萬歐洲人死亡,而被殖民地區喪生的民眾則高達5000萬—6000萬人。
熱衷于用戰爭解決問題的西方列強最終也陷入自我毀滅的危險境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劃分勢力范圍進行的世界性戰爭。在這次戰爭中,僅索姆河戰役傷亡人數就超過了130萬。整個一戰期間,歐洲有數百萬青壯年死于戰場,大量人類文明成果毀于戰火。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親眼目睹了西方世界這種自我毀滅式的戰爭場景后,完成了《西方的沒落》一書,并悲觀地預言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某種程度上是一戰的延續。工業化水平日新月異,使各種戰爭武器的殺傷力和破壞性空前提升,由此導致二戰給人類社會造成的劫難遠大于一戰。1945年二戰結束時,德國國內生產總值跌至1890年時的水平,英國從一個債權國變成了負債國。1946—1947年,約有1億歐洲人只能靠每天領取1500千卡熱量的口糧來維持生活。事實告訴我們,指望訴諸戰爭實現霸權目標,最終只會適得其反。正如古羅馬學者西塞羅所說:“絕大多數人認為,從戰爭中獲得的東西要比在和平環境中獲得的東西有價值,其實這是錯誤的。”
二戰后,核武器的出現與隨之而來的“恐怖平衡”極大抑制了爆發世界性戰爭的可能。在長達50年的冷戰期間,盡管美蘇劍拔弩張,但雙方均較為克制,由此使世界出現了難得的戰爭間歇期。美蘇冷戰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冷和平”。
然而,蘇聯解體使美國因失去外部制衡而變得日益黷武好戰。冷戰后爆發的五場局部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均由美國發動或主導。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圍堵與遏制力度也在持續加劇。鄧小平在1989年曾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美國《國會記錄》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項目》等公開資料顯示,1890—2001年的111年間,美國共采取了133項軍事干預行動。
近年來,大國權力加速轉移,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對衰落趨勢明顯。經濟金融化、空心化使美國出現由盛轉衰的征兆。與此同時,“9·11”事件后美國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導致其軟硬實力加速衰落。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態勢明顯。歷史經驗表明,權力轉移期往往也是地緣矛盾多發期。意大利歷史學家喬萬尼·阿瑞吉認為,資本積累與戰爭具有正相關性。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最少經歷了三個積累周期,每次資本積累周期轉換(實際也是權力轉移),最終都是通過大規模戰爭解決。在美國等西方列強看來,權力就是強迫他國按照本國意志行事的能力,由此決定了霸權具有稀缺性和排他性。美國絕不允許任何國家與美國平起平坐,因此不斷加大對中、俄等新興大國的圍堵和遏制力度。
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沖突,表面看是俄羅斯主動發難,實則是美國推動北約東擴、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引發的結果。從根本上看,俄烏沖突具有霸權與反霸權性質,也是國際權力轉移大背景下的新舊體系之戰。沖突爆發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煽風點火,通過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策動“代理人戰爭”,其目的就是盡可能延長戰爭時間,借此從中漁利。
美國將發動戰爭視為有利可圖的“好生意”,但對整個世界卻是不折不扣的災難性事件。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至少要對37個受害國的2000萬人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對1000萬—1500萬人的死亡直接負責。不夸張地說,美國才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大威脅。
對世界各國來說,維護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穩定安寧的國際環境,有利于各國推動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并由此形成安全與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相反,安全形勢不佳會極大破壞當地營商環境;軍費開支居高不下直接擠占民生領域投入;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使交戰國兩敗俱傷,多年來取得的經濟成果毀于一旦。此外,發展滯后又會加劇政權不穩和地區動蕩,使各國陷入“越亂越窮——越窮越亂”的惡性循環,正所謂“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

2021年9月28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在美國華盛頓出席國會聽證會,表示阿富汗戰爭以“戰略性失敗”告終。(新華社圖片)

2003年6月18日,美軍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美英聯軍臨時總部門前持槍面對數百名示威的伊拉克人。(新華社圖片)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國際安全與國內安全相互影響。原本屬于傳統安全和國際安全領域的戰爭與沖突,其影響不僅限于國力消長和國際格局變動,還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應和次生災難,殃及整個世界。例如,此次俄烏沖突不僅造成烏克蘭大量人員傷亡、基礎設施被毀,還導致國際能源價格居高不下、多國糧食供應短缺危機頻發,使世界經濟復蘇再次放緩。
更令人擔憂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全球經濟日漸放緩以及俄烏沖突長期化等諸多因素相互疊加,使原本高度融合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加速分裂,潛在矛盾和不確定性因素不斷涌現,世界范圍內各領域失衡、失序、失范現象加劇。當前世界格局也出現了大國矛盾白熱化、政治陣營化、經濟碎片化、安全自助化、價值對立化等一系列危險趨勢。這些長期積蓄的矛盾一旦超過臨界點,便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大規模戰爭和沖突。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寧。”要想消除戰爭根源,構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必須尋找一種能夠體現新治理理念的新安全框架。
在世紀大流疫與俄烏沖突相互交織之際,西方傳統安全理念主導的世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動蕩與不確定性。全球發展不平衡與愈發顯現的國際矛盾催生出更多不穩定因素及國際安全問題。西方以恃強凌弱、舍他保己為內核的傳統安全觀引發世界更多國家和民眾的不滿與反對。在國際格局加速調整大背景下,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迫切呼吁在全球范圍內樹立以平等互信為基礎的新安全理念。基于此,旨在維護全球更廣泛人民安全利益的全球安全倡議應運而生。
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之所以頻頻出現戰爭和沖突,與西方國家信奉的實力政治直接相關。在西方國家歷史和思想中,強權政治的價值觀可謂根深蒂固。西方學術經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了一段雅典人與彌羅斯人的談判內容。處于優勢的雅典人說得非常露骨:“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這番話將西方國家恃強凌弱的霸權心態表達得淋漓盡致。對武力的推崇,使歐洲人在與非西方國家交往中,經常將軍事威力作為評價非西方民族優劣的主要參照標準。
現實主義是當代西方國家流行最廣、接受度最高的國際關系理論。該理論將國際社會視為無政府狀態,各國出于恐懼、利益或威望,強化安全自助意識并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在西方現實主義理論家看來,追求生存和強大是國家存在的終極目標。經典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漢斯·摩根索認為,國家間競爭的目標就是爭奪權力、保持權力和顯示權力。新現實主義知名學者肯尼思·華爾茲在《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一書中認為,武力的濫觴在于國際無政府狀態。戰爭的根源可概括為三種情形:壞的人性、壞的國家和壞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而近些年出現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在主張追求權力的同時,其政策主張也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更是如此。理論本身并非政治,但理論一旦體現為國家政策,便會對現實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各種似是而非的西方理論主張大行其道,才使國際安全困境持續加劇,使當今世界變成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損的“壞世界”。

2022年4月26日,德國國防部長蘭布雷希特宣布,德國將向烏克蘭提供“獵豹”防空坦克。(IC Photo圖片
西方國家基于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價值觀觀察和處理世界事務,很容易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維與冷戰思維,以及本國至上的狹隘民族主義,乃至恃強凌弱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問題在于,世界從來就是一個有機整體,各國只是這個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習近平主席指出:“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部復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器,拆掉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被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損。”從整體和系統的角度看,整體大于部分。作為組成部分的各個國家越是能夠協調合作,世界整體越能不斷優化,并由此形成“好世界”。
紓解當前全球日趨加劇的安全困境,必須首先從價值觀念上摒棄冷戰思維及零和博弈的習慣性做法。當今世界面臨兩種迥然不同的治理理念和路徑選擇:一種是抱守西方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觀念,以強權政治和窮兵黷武為行為準則,以集團對抗和犧牲他國安全換取自身所謂絕對安全的舊安全觀;另一種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天下主義為價值理念,強調公平合理、共建共享、政治談判和互相尊重的新安全觀。事實表明,西方國家長期踐行的舊安全觀使人類社會發展之路越走越窄,整個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在這種背景下,倡導和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變得日趨迫切。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就是這種新安全觀的集中體現。從具體內容和內在邏輯看,全球安全倡議強調的“六個堅持”是針對當今世界安全困境中的種種癥結,提出的切實可行的指導性方案。這些主張環環相扣、彼此呼應,為構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擘畫了藍圖。
從思想淵源看,全球安全倡議的基本內容既是對國際法基本準則和國際安全治理經驗教訓的凝練和揚棄,也彰顯了東方文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底蘊和底色。從哲學思維看,中華文明強調辯證思維,理解禍福相依、矛盾相互轉化,因而甚少走向極端,反對非此即彼、形而上學色彩濃厚的冷戰思維;在國家間交往中,不同于西方價值觀中動輒強加于人的霸道做法,中華文明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兼容并蓄;在安全理念上,中華文明有著強烈的“天下一家”意識,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這遠遠高于西方文明“贏者通吃”的價值觀站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是強調國際主義精神,主張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平等尊重、和平共處。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典型體現,全球安全倡議則是這一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縱向看,全球安全倡議與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及亞洲安全觀一脈相承,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三者分別從國內、地區和全球層面構建起體系完整的新安全觀。從橫向看,全球安全倡議與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相輔相成,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支柱,由此為創造不同于西方體系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理論和思想基礎。習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和發展議題中提出的重大創新性倡議,恰是中國在價值觀領域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的集中體現。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和平與安全是全球最重要、最寶貴的公共產品,也是最奢侈、最稀缺的全球公共產品。據統計,在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中,只有268年沒有發生戰爭。私有制是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總根源。資本就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實現資本增值是資本主義固有天性。馬克思曾指出:“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只要存在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資本積累為最終目標的帝國主義戰爭就不可避免。從世界歷史和當下現實看,西方國家的資本積累往往通過霸權主義方式完成,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是當前全球安全困境加劇的直接原因。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紓解全球安全困境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2021年9月25日,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郊區的“斯大林防線”博物館,人們重演二戰期間摩托化步兵參與抵抗德國法西斯的戰斗活動,紀念摩托化步兵日。(新華社圖片)

2022年4月,中國赴黎巴嫩維和部隊參加聯黎部隊“天使救援”演習。(新華社圖片)
世界和平與穩定僅僅靠善意和愿望是無法實現的,要想維護世界和平、落實全球安全倡議,歸根到底要反對霸權主義。鄧小平曾指出:“世界現在存在兩個最根本的問題。第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當今世界不安寧的根源來源于霸權主義的爭奪,它損害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問題。這是今后國際問題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一命題至今仍具有時代意義。
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現實中,好戰的美國日漸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自1776年美國獨立以來,美國沒有參與戰爭的時間不足20年。據不完全統計,自1945年二戰結束至2001年,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的248次武裝沖突中,由美發起的為201場,約占81%。美國在全球擁有800多個海外軍事基地,頻頻發動海外戰爭。2017年8月,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20個國家舉行的民調顯示,35%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權力和影響”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在此背景下,遏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行徑,已成為一項重大的時代課題。
從戰爭與和平角度看,世界大體存在兩種力量:一種是希望和平與發展的歷史進步力量,另一種是熱衷于發動戰爭并從中漁翁得利的反動力量。要想落實全球安全倡議,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必須聯合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形成反霸統一戰線。只有全世界熱愛和平的國家和民眾聯合起來且力量超過熱衷戰爭的力量,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