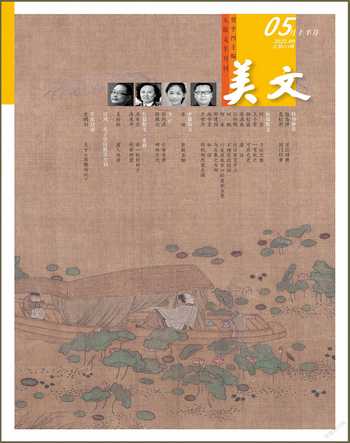關于《離婚訴訟》

史鵬釗
長篇小說《離婚訴訟》的原型是我聽來的一個故事,而現實發生的種種,或許遠比小說還曲折。
捷克籍猶太裔作家在《等待黑暗,等待光明》里說:“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團亂麻,一大堆抹布,瓶瓶罐罐,攪拌機,生了銹的管道,耗子在里面鉆進鉆出。還有線纜,燈具,鏡子,攝影機,帶子,剪刀和噴水車。”我讀完這本書后,感同身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不就是在黑暗和光明的時空交替中,走向精神深處的光明么。所以我們在旋繞的生活中,必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怎么去干,干成什么樣兒,這是我們的生活準則。
《離婚訴訟》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其實是個較短的長篇,字數只十五萬字,僅僅比嚴格意義上的中篇長了一些。我在寫作的過程中,往往隨心所欲,自己經常成了故事的敘述者。我構思這部小說時,信手拈來地選擇了自己比較熟悉的素材,可能從構想的意義上,我覺得能夠堅持下來。工作這么多年,長期又在基層,工作中有許多瑣碎的事情,林林總總的人,林林總總的事情,為我積累素材打下了堅實基礎。還有,我還算善于觀察和傾聽,在生活中發生的故事遠遠比小說更加精彩和離奇,而它確實已經發生,這就成了我小說中故事的一部分。
2020年春節,在新冠病毒剛剛在中國大地席卷期間,我在工作單位也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回家的次數較少。繁忙的工作,沉重的壓力讓自己合不上眼,每天利用空隙時間就一口氣寫了下來。在寫作過程中,我常常覺得這些值得被寫出來,因為這些故事就發生在每個人的身邊,親近且熟悉,人都是普通的人,但是他們在生活中又形形色色,這可能就是生活吧。所以,我寫這部小說,更多地是想以文字的形式,記錄這段故事,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影子,且產生共鳴。這是我寫這部小說的緣起和想法。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之前更多的是堅持非虛構寫作,寫了一些關于故鄉的文字,也堅持著一些自己散文的個性特點,如《光陰史記》《出村莊記》,還有即將出版的《大國小村》等,這些都是為生活了十八年的故鄉的真實畫像和記憶,這些書稿,也是我用非虛構的手法,給故鄉的獻禮,對自己的救贖。我的記憶永遠都在村莊里,放牛、賣西瓜、干農活,故鄉的溝溝坎坎,一樹一木,村莊里每個老人的笑臉和苦悶,都在我的記憶里深刻地儲存著,永遠抹不去,包括那些已經因病老去的人。他們的墳墓在哪里,我都記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利用自己的業余愛好,做了故鄉的記錄者和感懷者。非虛構和小說最大的區別就是是否真實。非虛構寫作我個人認為堅決不能有虛構的成分,而小說創作卻給了巨大的虛構空間。非虛構寫作更多的是我個人對歷史和現實的再現和見證,始終在真實的鐵律中,用情感去表達一個個細節,一個個場景,甚至是一句句對話。
在《離婚訴訟》這部小說的創作中,我始終堅持情節、人物和氣氛,以故事的情節去表達人物的特點,然后帶給讀者去評判。我在寫作過程中,心里始終想的是讓故事巧妙而不突兀,合理而不矛盾,讓小說有應有的質地。陳玲和路明,吳光明和程翠英,凌解放和符金英,還有莊澤亮和汪娟等等,這四個家庭的生活,構成了這個社會的悲歡離合,這是小說創作的需要。通過鮮明獨特的人物形象來表達這四組家庭的悲歡交織,讓他們的歡喜、焦慮、矛盾和憂愁更加個性化。我身邊遇到的那個人物原型,她堅強而獨立,執拗而敏感,是她的生活故事給了我這部小說創作的內容。尤其是我聽到她在焦慮時,絮絮叨叨地說起身邊的人和事時,在我內心的文學世界里,就已經有了寫下去的思路。當然,人常說,藝術來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我在寫陳玲這個女主人公時,盡可能把一個女人的完美和缺陷都表達出來,這個女主人公有血有肉,她可能是我們鄰居大姐,也有可能是匆匆而過的陌生人。她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是我小說人物塑造的典型,我個人認為只有這樣,小說的價值本質才能表達出來,讓讀者喜歡。
女主人公陳玲是這部小說的線索人物,也是核心人物,小說的故事始終圍繞著她的生活展開。她的婚姻家庭生活,和因為婚姻生活而引發的林林總總的事情,不僅僅是她的遭遇和命運,也是這個社會的現實寫照。陳玲自從被離婚后,她一直追求著生命和生存的尊嚴,正是因為這樣,她的生活有著很多疑問和矛盾,也充滿失敗和沮喪,她在構建和維護自己心理世界的過程中,與社會、親情、愛情,與親人、異性發生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她在不斷觸摸著自己內心最隱秘的疼痛時,卻讓自己的生活充盈了起來,讓自己變得甚至有些高尚,充滿溫度,這是這部小說想要表達的煙火氣。在日常生活中,許多女性在離婚后卻陷入思想的深淵,在人性的深處產生了情感的迷失。我寫這部小說,也可能是要探究當代社會生活的精神現象。
錢鐘書先生在《圍城》里說:婚姻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里的人想出來。我們都是這座圍城里的掌舵者,每一棟高樓里,有若干個單元,每個單元里都有諸多住戶。住戶就是在圍城內外的男人和女人構成的,他們構成了家庭,正是因為家庭是兩個不同的人組成,所以才有了喜怒哀樂。男女性別不同,成長環境不同,教育背景不同,面對生活的方式更是大不同。兩個大不同的人走在了一起,因為愛,但是愛有兩種結果。愛和不再愛,不再愛的有些人,就走上了離婚的道路,也有一些不再愛的人,因為種種原因,還在一張結婚證的契約下,將婚姻名存實亡地存續著,這就成了生活。《離婚訴訟》主要是展現近十年來的各種社會現實,反映當下社會人們價值觀的多元碰撞,刻畫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下,一幅幅真實的社會眾生相。在小說的創作中,我比較注重于都市生活的開掘,關注小人物的命運。這也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有句俗話說,丑媳婦總得見公婆。寫完后,我就找了一些朋友,讓他們有空了翻翻,提提意見。有人讀了,說你寫的這事兒,我知道的,那不是咱們原來見過的陳玲么。我笑了笑,說這就是聽來的故事。還有人,后來給我說,沒有時間讀啊。我也笑了笑,在這座城市里,大家都很忙。忙亂了這么多年,自己都不知道在忙亂些什么。我也忙亂,卻還是在去年疫情期間,把這個故事寫了下來。我的朋友Y發微信說,她現在有一種感受,對人對事越敏感的人,越能做成事兒。我又笑,我知道她是鼓勵我。因為她常常鼓勵我,鼓勵就像燃燒的火焰,有人拿著火棍子攪和助力下,本來還沒有火苗的柴草,就噼里啪啦地燃起來,毫無遮攔。因為我是個給點陽光,就燦爛的人。
說到生活,細細思量,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一團麻,每個人都有思想世界里解不開的疙瘩,或大或小。就和這部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寫這部小說,總是在夜晚,尤其是那段疫情期間,城市封閉,生活停擺,我和同事們每天都圍繞著疫情防控開展工作,除此之外,再無他事。每當后半夜,我總是想起陳玲的事兒來。我聽到這個故事時,故事還沒有結局。突然有一天,凌解放酒后去世了,我通過朋友見到了陳玲。一個很端莊的女人,和我的年齡相仿,但是眼角的魚尾紋掩飾不住這些年來日子的消磨。她說史老師,聽說你是個作家,我這一地雞毛的生活,是不是比你們寫的小說,還曲折呢。
陳玲是個性格中有些執拗的人,我從她的言語中能感受到。聊了會兒,我們都呵呵地笑了。她笑她過去的日子,那都是些啥呀,甚至自己現在都想不明白,自己咋有那么大的氣力,東奔西跑,總想要個說法。她說著端起桌上的咖啡,抿了口,說自己是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又說自己是劉震云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說完了,她又說自己誰也不是,是現在活成了的自己。過去的日子,都是好日子。說到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座城市,她又感恩了起來,這座城市給了自己生活。
我們在生活中,有許多故事的本身。《離婚訴訟》這部小說,以主人公陳玲和丈夫路明為買房而假離婚,路明假戲真做又組成新的家庭,陳玲執拗地要個說法,陰差陽錯走上了上訪路為故事的主線。一路上她遇到了逃避生活嗜酒如命的法官凌解放,外冷內熱的符金英,如父如母的吳光明、程翠英等等。這和我們每個人一樣,生活和工作的關系中,會遇到很多人,發生許多事兒;也消失了很多人,許多事情就戛然而止。來來往往,起起伏伏的日子,在生活的狀態中經見著成長和歲月的年輪,也經見了每個人的處事方式和對生活的態度。
文學是人學,小說是對普通人內心世界和感情變化的書寫。寫完了這部小說,我認真做了個深呼吸,我們都是平凡的人,我你他都是生活的主人公,小說中的人物,都是被陽光拉長了自己的影子。現實和虛構的交織,才是小說應有的質地。還有幾位朋友,后來給我說,你寫的不就是誰誰么。我笑了笑,說都是我們,我們。既然是小說,人物情節虛構,是文本的需要,請不必對號入座。就像我們每天在洗漱之后,要去照鏡子,照鏡子是為了讓自己更加滿意。如果你站在已經摔碎的鏡子面前,你看到的會是陌生的自己。每個有趣的靈魂,都屬于孤獨的個體。
書稿確定后,我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沖動,將書稿誠惶誠恐地發給了吳義勤、陳彥老師,他們作為文學界的大家,給了我諸多的鼓勵。陳彥老師在給我的微信留言說:生活看似平常,當我們換一雙眼睛凝視時,就發現了其中的荒誕不經與離奇巧合。但生活終歸是生活,我們永遠都腳踩在一地碎屑上漫步與疾行。繁華在兩旁,冷暖在心上。史鵬釗讓我們走讀了一次別樣的俗世百態和滿眼煙火。這句話我讀了十多遍,他的長篇小說《裝臺》《喜劇》我讀了好幾遍,給了我文學精神的食糧。吳義勤老師發來微信,給了諸多關心,還問了我是哪位編輯負責,他愿意作為推薦人,把這本書推薦給讀者。去年農歷十月一日那天晚,我和賈平凹老師在位于西安永松路的醬豆書屋見面,喝茶聊天,聊那時還正在蔓延的新一輪新冠疫情,聊我們基層單位疫情防控的做法,還聊起了生活的種種,尤其他聽我說完了剛完成不久的小說,勉勵的話兒如清茶般清香。聊完天,已經是夜里十點半,他還要給逝去的老人在十字路口燒寒衣,寄托一個兒子對老人的思念。我們倆從醬豆書屋出來,向南走,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和許許多多蹲在路邊燒寒衣的人一樣,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男人,是一個已經沒有了父母的兒子。我看著他和所有人一樣,從袋子里取出紙錢,蹲在那里,用打火機點燃,然后提起來,一沓沓紙錢在風中燃燒且彌漫開來,直到燒完了紙,才站起身來,返回自己家里去。
坐在出租車上,我的思緒還一直沉思在我們的聊天中,還在《離婚訴訟》這部小說中。對于我來說,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創作的過程就是撫養的過程。我在聽了賈平凹老師的一席話后,學會了重新了解和審視自己,和自己筆下的文字。作品甫一出版上市,就好像自己出嫁的女兒慢慢學會懂事,做人,要走向自己的生活,以后的路還很長。
最后要說的是,很感謝關注這部小說的人。尤其要感謝作家出版社及責編史佳麗老師。史老師不僅是資深的文學編輯,而且還是散文家、評論家。對于這部小說的書名,作者和編輯之間,一直有一個糾結點。對于編輯來說,不僅要照顧作者的文本,更多的是要照顧讀者的口味,甚至還有出版后作品的市場。僅僅是書名,我們就討論了多次,最終為《離婚訴訟》。
(責任編輯: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