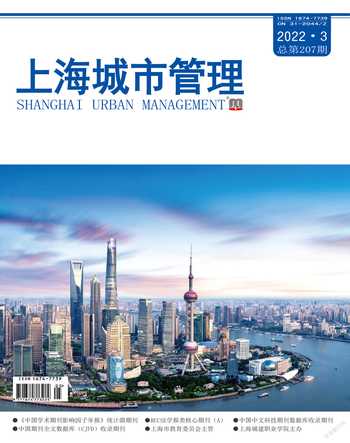空間理論視域下城市社區公共空間的治理
孫向謙 劉娜


摘要:現代城市社區公共空間的剝奪和隔離造成了社區公共性的缺失,是制約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題。基于空間生產理論,構建以“空間三元辯證法”為基礎的分析框架,探討了上海市X區“鄰里匯”公共空間在布局建設、治理架構、組織運營和服務發展方面的治理機制和邏輯。研究認為,鄰里匯作為集社會交往、公共服務和社區治理為一體的社區共享空間,是政府、市場和社會等一切參與主體行為的空間載體,空間治理應通過各治理主體的互動和協同來實現空間實踐、空間表征和表征空間的有機統一,形成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共治的公共空間治理范式。
關鍵詞:空間生產理論;空間三元辯證法;公共空間治理;鄰里匯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3.009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轉型和社會的變遷,我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單位制”的瓦解和城鄉二元體制的消解,過去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使得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加。這造成了人與社會、國家之間聯結的弱化、社區認同的缺失、社會的失范等,對城鄉社會管理體系產生了不利影響。[1]隨著城市化和住房商品化的影響,傳統社區“共同體”的價值觀逐漸被打破,在權力、資本等多方力量的參與下,社區公共空間的公共性讓位于城市發展的經濟性,出現了公共空間的剝奪、隔離等現象,進一步加劇了居民的孤獨感、疏離感和陌生感,使城市基層治理再次陷入困境。究其原因,關鍵就在于公共空間的均質性被打破,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和包容性不斷缺失。
城市公共空間的概念最早在1960年代初期由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雅各布斯(Jacobs Jane)等學者提出,成為了很多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家的研究對象。伯曼(Berman M)指出公共空間是城市居民可以親近的場所,是他們自由開展各種活動的場所。[2]朱坎茵(Zukin S)認為,城市公共空間可以滿足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公眾的價值觀和需求在不斷地碰撞和融合中賦予了公共空間新的意義。[3]阿倫特(Hanah Arendt)指出公共空間能夠讓人們聚集、閑聊、認識彼此的存在,對于民主政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4]可見,現代城市公共空間可以滿足多元的需求,是生活、社會交往、文化匯聚和民主參與的重要載體。
基層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指出要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資源向基層傾斜,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近年來,全國各個城市都致力于黨群服務中心、社區服務站點、公共會客廳、鄰里驛站等形式的社區公共空間和站點的建設,不斷加強公共空間和服務的有效供給,對于社區回歸公共性,創新基層社會治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鄰里匯”作為近年來上海市X區大力建設的一種新型鄰里空間,探索了一種公共服務供給和社區治理的新思路。本文以X區鄰里匯站點建設和管理為例,試圖分析城市社區公共空間的生產和治理機制及它背后的治理邏輯,為當前城市公共空間站點的治理提供借鑒和啟發。
二、理論基礎和研究現狀
社會科學理論的“空間轉向”是20世紀60年代后重要的發展之一,其最早可追溯到馬克思地理學和社會關系重組意義上的空間生產思想。20世紀20年代后,以齊美爾(Georg Simmel)等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將空間研究與社會學結合,開創了城市研究新范式。20世紀中期,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間權力理論和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是具有代表意義的研究成果。20世紀60年代之后,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哈維(David Harvey)等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重新思考城市化、空間生產、社會關系以及資本的關系,以空間理論為突破深刻揭示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方式,將空間理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其中,列斐伏爾在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空間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原創性地提出了“空間三元辯證法”,即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并以此來解釋各種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5]哈維進一步繼承和豐富了空間生產理論,他用資本的積累來解釋城市空間生產的機制、性質和后果,認為投資可以在不同的“資本循環”中轉換,來避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而這一切都取決于以擴張和重構來進行的空間生產。[6]
近年來,運用空間理論研究城市公共空間生產的議題廣泛,呈現出多學科且交叉研究的特點。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伴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加快和空間理論的引入,這一問題也得到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通過回顧,可梳理為城市公共空間功能和困境、公共空間生產邏輯和動力、公共空間構建的策略三個角度。
(一)城市公共空間功能和困境
現代城市公共空間是面對公眾開放的、供公眾使用的空間。它的功能多元且日益重要,是人們社會交往、學習發展、信息交換、政治參與和公共服務的重要場所。城市社區的空間設置對于鄰里關系具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7]在全球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空間的“公共性”正遭受著挑戰。Ljiljana Vasilevska通過對塞爾維亞尼斯市現有住宅類型在改造中的公共開放空間的研究,得出以市場為導向的后社會主義城市規劃框架可能導致住宅區的空間和功能碎片化,造成公共空間的退化或消失。[8]Rajjan等通過對加德滿都社區公共空間生產的實證研究,得出由于缺乏適當的城市規劃和控制措施,社區整體缺陷、組織能力差以及侵占公共土地等因素限制了當前社區公共空間的發展。[9]在我國,佘高紅、李志剛等學者們也從城市居住空間的貧富分化[10]、居住空間形態的隔離與分異[11]、公共空間的擠占以及公共服務的缺失[12]等空間社會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
(二)公共空間的生產邏輯和動力
城市公共空間是如何生產的,其背后的影響因素和動力機制也是近年來學者們關注的重點。Claudio de Magalhaes等提出了一種分析框架,將公共空間治理的角色分為政府、市場和使用者,提出了公共空間治理的四個維度:行動協調、規則秩序、管理維護和資源投入,分別分析公共空間對應治理模式的實踐及潛在結果。[13]我國學者也從制度變遷、資本、社會組織等維度探討了公共空間生產背后的邏輯。楊迪等探討了計劃型城市和經營性城市的空間生產,分析了制度變遷對城市公共空間生產的影響。[14]龐娟等認為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和經濟利益導向的政府治理容易形成利益一致,探討了空間生產背后的資本邏輯。[15]李雪萍認為社會組織在社區公共空間的生產中作用非常重要,政府應該通過讓渡權力實現向監督者的過渡。[16]陳水生指出我國空間生產遵循權力、資本和生活三重邏輯,城市空間生產要更加注重生活邏輯,以此來保持三者的動態平衡。[17]部分學者運用空間理論對某一具體空間的生產或某一行為現象進行解釋。魏萍、高紅、彭松林等圍繞某一具體空間探討了公共空間的治理,如選取了某鄉村[18]、社區花園營造[19]和圖書館轉型[20]的事例。孫小逸等將空間理論引入社區治理,指出社區治理規則的變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鄰里空間與業主追求權益與自治兩者角逐的后果。[21]陳進華認為“空間治理”通過政府、企業、社會、市民等不同主體在空間生產及其權益分配上達成“空間利益共同體”,可以有效化解城市化進程中的風險問題。[22]
(三)公共空間構建的策略
城市公共空間的構建應遵循什么樣的路徑,學者們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踐研究提出了對策和策略。卡爾(Stephen Carr)認為,公共空間首先要對所有使用者的需求保持敏感;其次要符合民主精神,適用于所有人群;再次要富有意義,在民眾的生活與世界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系。[23]曹現強等從空間正義的價值觀出發,指出城市發展要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以制度和治理機制為保障,以公共政策為支撐,同時要正確應對空間不公的社會抗爭行動。[24]鄭婷婷等認為我國公共空間的構建應該以公共性為價值范式,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控制資本對空間生產的侵蝕和空間資源分配上兩極分化的局面,謀求多元主體利益之間的重疊共識,倡導包容性和參與式城市空間理念。[25]陳水生等從服務型政府視角出發,指出公共空間生產應堅持人本導向的理念更新、包容共享的利益調節和多元適配的需求整合“三位一體”的再造策略。[26]
三、分析框架
在空間社會科學研究中,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理論,他提出了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的“空間三元辯證法”,用以解釋各種社會形態和生產關系,成為其理論的核心。其中,空間實踐是一種具有實體形態的社會空間,擔負著社會構成物的生產和再生產的職能,是一種可以感知的物理空間。空間的表征是社會上處于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所建構出來的空間秩序,是一個被統治階級所構想出來的空間。表征的空間是平民日常生活的空間,是被想象力改變和占有的空間,是對抽象空間的一種反抗和重構。三者在邏輯上存在著一種循環和遞進的關系,“空間實踐”和“空間表征”對應的類似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層面,“表征空間”是指在“空間實踐”基礎上對日常生產生活進行的抵制與回歸,“空間表征”是對“表征空間”在意識形態上的超越,列斐伏爾將這種循環遞進關系稱之為“回溯式進步”。[27]
通過空間三元辯證法來分析鄰里匯社區公共空間的生產和治理過程,可以厘清其背后相關主體的運行機制和治理邏輯。從空間三元辯證法出發,首先,鄰里匯占據一定的物理空間,是一切治理主體實現其空間權利的載體,是被感知的空間。其次,鄰里匯是區政府和街道辦為了實現“家門口的服務和更有序的治理”,通過品牌宣傳、統一標識、建立標準、規范管理等方式塑造話語和知識體系,并將其付諸實踐的場所,是被構想的空間。最后,鄰里匯也是居民在使用過程中用行動來實踐自己空間主張的過程,并在不斷地內化和抵制中形成的一種空間形態,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空間。
在這一框架下,三個“空間”之間相互作用、博弈達到一種不斷循環和遞進的均衡狀態。鄰里匯的建設、管理、運營和服務等治理過程呈現出政府、市場、社會等不同力量主導下的治理模式,三者通過其背后的不同治理邏輯實現協作、補充和發展,在不斷改進和動態平衡中實現鄰里匯多元共治的生產和治理機制,如圖1所示。
四、鄰里匯生產和治理的實證分析
近年來,社區公共服務資源稀缺一直是居民反映突出的問題和基層治理亟需破解的難題。2016年以來,上海市X區致力于構建“15分鐘社區生活圈”,以“鄰里匯,匯鄰里,美好生活共同體”為理念,通過鄰里匯共享空間站點的建設提供一站式服務和平臺。鄰里匯是一個由政府主辦,以街鎮為依托,多元主體參與的社區服務和治理的共享空間,通過對社區空間載體“外在”更新改造和對各類群眾需求“內在”系統集成,做到社會交往、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功能的有機融合。經過幾年的建設和發展,目前已經形成了“區-街鎮-居民區”三級鄰里匯體系和比較成熟的治理模式,完成了300余處鄰里匯和鄰里小匯的布局建設。
(一)鄰里匯布局建設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首先是一個容納社會關系的“容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鄰里匯作為一個實體的空間,承載著社交、服務和治理的功能。鄰里匯的選址以“15分鐘社區生活圈”和“5分鐘家門口服務圈”為半徑,原則上按照一個街鎮1~2個鄰里匯,一個居民區一個鄰里小匯布局,側重于對現有空間整合、活化和升級,同時通過新建、租賃和改建的方式挖掘新資源為補充。作為一項民生工程,鄰里匯的先期建設和設施配備,由區級財政一次性投入,并承擔全部建設責任。
為了讓居民能有一個好的空間體驗、心理認知和情感認同,政府對于鄰里匯的設計風格、建設標準、功能構成、名稱和標識標志等進行了規范和統一,既形成了品牌效應,也便于政府在空間的構建中,形成自己的“語言符號和知識體系”,成為一種隱性的空間權力。由政府權力意志主導的鄰里匯建設過程,充分發揮了宏觀引導、整體規劃和資金保障方面的優勢,但往往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受到追求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等非科學因素的影響,注重表面功夫而輕內在功能,使服務難以滿足居民的需求。因此,政府在鄰里匯建設中注重引入專家學者、社區規劃師、社會組織、居民代表等,組成了“智囊團”,有序參與到規劃設計、硬件配置、功能劃分和空間管理等方面,為鄰里匯建設提供民主決策和智力支持。可見,鄰里匯的建設一方面體現了政府作為權力主體基于其社會服務和治理的意志而推動的結果,另一方面,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發揮自身優勢特長,激發了共建共治的活力。
(二)鄰里匯治理架構
鄰里匯的管理以街鎮為主體,建立多層次管理機制。在街鎮層面建立了鄰里匯聯席會議制度,同時設立鄰里匯運營管理中心,定期研究鄰里匯建設和發展事宜。鄰里匯的具體管理由“鄰里匯理事會”負責,搭建起了民主決策議事平臺。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由區域單位黨組織負責人擔任,理事成員由群眾性團隊、社會組織、區域單位、志愿者等各方代表組成,負責鄰里匯重大事項的決策、服務質量的評議與監督等工作。經過實踐探索,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等議事協商制度和規范的自治章程、居規民約等議事協商規則,建立起了黨組織領導、政府負責和社會多元參與的鄰里匯治理格局,其本質是一種權力邏輯主導下的多元治理的空間秩序。
(三)鄰里匯組織運營
鄰里匯的運營根據其定位、功能和規模的不同,可采用自主管理、全權委托第三方運營、項目化合作運營不同的模式。其中,自主管理的鄰里匯是由居委會全權負責鄰里匯的運作,是一種行政主導的運營模式。這類鄰里匯大多數由居民區的活動室或居委辦公場所改建,基于“服務型政府”的理念,這些鄰里匯承擔著居委和社區共享空間的雙重功能。它們的面積自幾十至百平方米不等,服務的群體基本固定,可以利用的社區資源較為有限,居委和社區工作者承擔了較多的鄰里匯運營工作。
全權委托第三方運營是一種由市場主導的運營模式,其規模和運營模式有點類似于新加坡的鄰里中心,資源投入量較大,具有功能完善、服務專業、管理規范的特點,公共服務上仍以公益性為主,但是可以根據需求提供一些有償或低償的服務。
項目化合作運營是一種政社合作的運營模式,主要是以居委負責為主,同時部分公共空間分時段讓渡給社區的自組織團隊來運作,主要以街道示范型鄰里小匯為代表。這類鄰里匯公共空間面積相比“旗艦店”較小,輻射區域人群相較固定,依托社區的自組織團隊開展活動。以項目化合作運營的鄰里匯大多有穩定的志愿者隊伍,居委將部分公共空間交給居民運營,整體的管理和空間使用分配權依然由居委掌握,能讓居民真正產生一種“主人翁”和“我的空間我做主”的意識。這類示范型鄰里匯發展程度介于旗艦鄰里匯和普惠型鄰里匯之間,其建設的重點是如何提升社區自組織活動的規范化、常規化、專業化,逐步形成品牌效應,是當前最主要的一種運營模式(見表1)。
(四)鄰里匯服務發展
鄰里匯在服務管理上注重服務至上和需求導向,建立了社會化需求的遴選機制,鄰里匯理事會每年開展服務需求遴選活動,通過向使用者發放需求問卷或需求征詢等方式,形成需求清單,從而針對性地設計服務活動項目。這使得鄰里匯的服務能保持動態的更新和持續的優化,更好地滿足居民需求,發揮匯聚人氣的作用。
薩拉蒙(Lester M.Salamon)在其第三政府理論中指出,社會組織和政府在功能上互補,因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的不足,社會組織應該更多地承擔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28]鄰里匯要提供多樣化的服務、滿足多元化的需求,單靠政府的力量必然導致成本高且效率低的情況,依靠社會組織、志愿者、社會工作者是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必然選擇。鄰里匯在為民服務中注重居民自治和自我服務,通過“活動項目化”引入社會組織、志愿者團隊組織實施,通過“組織公益化”促進可持續化發展,發掘、培育社區能人達人,孵化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形成公共服務的長效化機制。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機制的治理邏輯發揮了主導的作用,社區社會組織成為了連接政府和居民的橋梁,提高了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政府在這一過程中“退居幕后”,一方面通過搭建平臺,孵化、培育社區社會組織發展,另一方面,對服務的過程和質量進行指導和監督。
五、結論
鄰里匯是由政府主辦,以街鎮為依托,多元主體參與的社區服務和治理的共享公共空間。在鄰里匯的規劃建設中,一方面體現了政府作為權力主體基于社會服務和治理的意志所推動的結果,另一方面,以專家學者、社區規劃師等為代表組成智囊團,共同參與其中,發揮各自優勢特長,激發了共建共治的活力。鄰里匯的管理主要由鄰里匯理事會負責,搭建起了一個黨組織領導下的民主決策議事平臺,形成了一種權力邏輯主導下的多元治理的空間秩序。為了保證服務和需求的匹配,鄰里匯建立了社會化需求遴選機制,同時大力培育社區自組織的發展,在服務提供上發揮主導作用,促進鄰里匯服務的長效化機制和可持續發展。這種由政府“搭臺”,社會力量“唱戲”的模式,已成為當前和今后鄰里匯服務提供的一個重要方向。
總之,鄰里匯公共空間是政府、市場和社會等一切主體行為的空間載體,空間治理也應該具有多重維度。通過各治理主體的互動和協同來實現空間實踐、空間表征和表征空間的有機統一,形成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共治的空間治理范式。
參考文獻:
[1]田毅鵬.轉型期中國城市社會管理之痛——以社會原子化為分析視角[J].探索與爭鳴,2012(12):65-69.
[2]Berman M.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M]. Toronto: Penguin Books, 1988.
[3]Zukin S. The Culture of Cities[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4]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5]張子凱.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述評[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10-14.
[6]李秀玲,秦龍.“空間生產”思想:從馬克思經列斐伏爾到哈維[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5):60-64.
[7]宋言奇.城市社區鄰里關系的空間效應[J].城市問題,2004(5):47-50.
[8]Ljiljana Vasilevska, Petar Vranic, Aleksandra Marinkovic. The effects of changes to the post-socialist urban planning framework on public open spaces in multi-story housing areas: A view from Nis, Serbia[J]. Cities, 2014(36):83-92.
[9]Rajjan Man Chitrakar, Douglas C. Baker, Mirko Guaralda. Urb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neighbourhood public space in Kathmandu Valley, Nepal[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53):30-38.
[10]佘高紅.城市貧困空間形成原因解析[J].城市問題,2010(6):60-64.
[11]李志剛,吳縛龍,盧漢龍.當代我國大都市的社會空間分異——對上海三個社區的實證研究[J].城市規劃,2004(6):60-67.
[12]韓志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空間政治學分析[J].探索,2009(2):65-70.
[13]Claudio de Magalhaes, Matthew Carmona. Dimensions and models of contemporary public space management in Englan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09,52(1):11-129.
[14]楊迪,楊志華.計劃型城市到經營型城市的公共空間生產研究[J].城市規劃,2017(10):39-45.
[15]龐娟,段艷平.我國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演變與治理[J].城市問題,2014(11):79-85.
[16]李雪萍,曹朝龍.社區社會組織與社區公共空間的生產[J].城市問題,2013(6):85-89.
[17]陳水生.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生產的三重邏輯及其平衡[J].學術月刊,2018(5):101-110.
[18]魏萍,藺寶鋼,張曉瑞.基于空間三元辯證法的城市周邊旅游型鄉村公共空間生產研究——以西安地區清水頭村為例[J].人文地理,2021(5):177-183.
[19]高紅,李一.城市社區公共空間的生產邏輯與治理策略——以青島市Q社區花園營造為例[J].行政與法,2021(10):46-55.
[20]彭松林.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對圖書館轉型發展的啟示[J].圖書館建設,2021(1):105-113.
[21]孫小逸,黃榮貴.再造可治理的鄰里空間——基于空間生產視角的分析[J].公共管理學報,2014(3):118-126+143-144.
[22]陳進華.中國城市風險化:空間與治理[J].中國社會科學,2017(8):43-60+204-205.
[23]Stephen Carr, Mark Francis, et al. Public Spa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曹現強,張福磊.我國城市空間正義缺失的邏輯及其矯治[J].城市發展研究,2012(3):129-133.
[25]鄭婷婷,徐磊青.空間正義理論視角下城市公共空間公共性的重構[J].建筑學報,2020(5):96-100.
[26]陳水生.中國城市公共空間治理模式創新研究[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8(5):99-107.
[27]潘可禮.亨利·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13-20.
[28]L. M. Salamom. 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 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M]. Public Policy,1981.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ory
Sun Xiangqian, Liu Na
(CPC Shanghai Xuhui District Party School,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deprivation and isol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modern urban community has resulted in the lack of publicity, which is a major problem restric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framework based on "Spatial Ternary Dialectics". It discusses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logic of "Lin-li-hui" public space in X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layout, governance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s a community public space integrating social interaction, public service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Lin-li-hui"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the behavior of all participan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Spatial governance should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governance subjects, so as to form a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paradigm of pluralistic co governance led by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spatial ternary dialectics;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Lin-li-hui
■責任編輯:王? 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