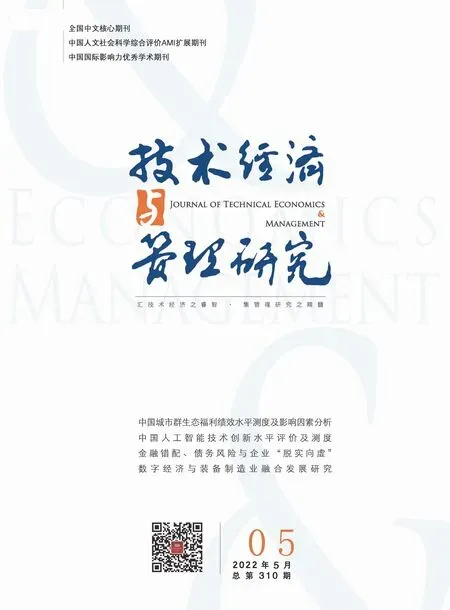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碳排放效應研究
楊 琴
(南昌理工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44)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工業革命以來碳排放大幅增加、碳濃度指數持續上升,造成了全球性氣候問題,為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災難,世界各國紛紛采取碳減排、碳中和的措施以積極應對。從國際上看,2016 年11 月生效的《巴黎協定》為2020 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行動安排,是繼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 年《京都議定書》之后,人類歷史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國際法律文本。為落實《巴黎協定》,世界主要碳排放大國都公布了碳減排、碳中和的方案規劃,美國和歐盟將在2050 年實現碳中和,中國將于2060 年實現碳中和。近年來碳排放上升速度加快,主要是由于:當前處于全球價值鏈加速發展的時期,全球工序分工的發展使得生產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國家完成。而且,發達國家把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規模加速上升,而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規模出現下降。從實踐看,2000 年以來,包括美國、日本、法國、德國等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量有所減少,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量增長顯著。
從中國的數據看,與加入WTO 時間同步,中國的碳排放規模也從2001 年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2019 年中國碳排放規模占全球的比重為28.8%,已經接近除中國外的世界前5 位國家的總和。這側面反映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下,國際資本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頻繁流動以期尋找到最佳的資源配置地,中國依賴于勞動力資源稟賦,成為跨國公司產業轉移的最佳場所,也成為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吸收地。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規模在下降。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碳排放規模的關系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
早期經濟學家主要關注碳排放和國內經濟增長的關系,大部分研究認為,碳排放和經濟增長之間呈倒“U”型關系,也就是所謂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1,2]。部分研究者分別從不同的國家或者區域實證檢驗“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存在性及轉折點[3-6],也有部分研究者否定了“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存在性[7,8],這些研究者發現碳排放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N”型、“U”型和倒“N”型等不同類型關系曲線。
顯然,上述有關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只是簡單證明了一國經濟增長與其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但缺乏國際資本流動與環境污染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隨著跨國公司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學者們開始從國際資本流動的視角深入分析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相互關系,形成了兩種對立的理論假說,即“污染天堂”假說和“污染光環”假說。對于“污染天堂”假說而言,主要是母國環境規制加大,跨國公司轉移產業到寬松的國家或地區,在實現產業轉移的同時,也導致污染和碳排放的轉移[9,10],環境管制較為寬松的國家具有生產污染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使得國際社會的污染密集型產業不斷轉移,導致全球范圍內的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 產業很容易繼續從具有較高環境管制標準的發達經濟體向低環境管制標準的發展中經濟體轉移。也有學者支持“污染天堂”假說(Jebli 等,2016;惠煒、趙國慶,2017)[11,12]。隨著對污染種類的不斷細分,開始有學者關注外商直接投資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13]。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認為不存在“污染避難所”[14,15]。這些研究認為“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取決于時期(短期內會存在,長期內不存在) 和資本流動模式等,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并不會引起污染產業在國際間轉移。外商直接投資母國嚴格的技術標準會提升跨國公司整體技術水平,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對中國的實證研究也部分支持了該觀點。
上述研究主要基于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碳排放之間的關系,至于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碳排放的影響,國內外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經濟增長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等方面(Cozza 等,2015;李雪松等,2017)[16,17],而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母國碳排放效應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然而,大多數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通常不會直接影響母國碳排放,而是通過其經濟增長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間接地對碳排放產生影響的[18]。關于國內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大多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碳排放沒有影響[19,20]。這或許是因為早期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以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為主。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規模加大,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等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這種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依賴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有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碳排放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并且存在相反的結論[21,22]。對于矛盾結論產生的原因,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解析。余官勝(2017)研究認為經濟發展水平低和制造業占比較大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加劇本國環境污染[23]。劉夏等(2019)認為對外直接投資通過作用于產業結構,顯著增加了對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24]。
整體來看,國內外學者們在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環境污染及碳排放影響方面的研究比較豐富,理論和實證都比較充分,但是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碳排放的影響,特別是隨著“走出去”規模的擴大,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如果存在這種影響的話,又是通過何種機制進行傳導的?中國應如何合理調整對外直接投資走向,降低國內碳排放?在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碳排放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文章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三種渠道深入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母國碳排放的傳導機制,為實現中國經濟更好更快地向低碳型增長方式轉變提供理論指導。
二、機理分析
1. 碳排放的一般均衡模型
參考盛斌和呂越(2012)模型[25],社會生產兩種產品:中間產品X和產成品Y,由于技術水平差異,兩種產品碳排放程度不同,假設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兩種產品的價格分別為PX和Py,投入兩種生產要素勞動(L)和資本(K),(KX/LX)>(KY/LY),假設X為污染密集型產品,Y為非污染密集型產品。生產函數為:

其中,C為碳排放,φ 表示Y產品中各要素所占的比重,0≤φ≤1,ω(φ)是遞減函數,受技術水平A的影響,一國碳減排強度函數為:

A為技術水平,技術水平越高,碳排放規模越小。

X產品部門在考慮碳排放規模下的最優決策為:

則X部門碳排放強度e為:

可以看出,碳排放強度和碳減排技術水平A以及碳排放成本δ 相關,也與產品價格相關。碳排放最佳要素投入比例為:

在均衡狀態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為:

要素市場均衡時資本(K)和勞動力(L)的需求和供給為:

產品X和Y實現均衡時的產出為:

2. 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母國碳排放的傳導機制
X部門的碳排放量表示為:

在H-O-S 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環境污染一般均衡模型中,對外直接投資也會通過經濟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對母國碳排放產生影響,其公式如下:

三、模型設定和指標選擇
1. 模型構建
基于Lin 等(2017)、Antweiler 等(2002)[26,27]拓展 的STIRPAT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構建以下面板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Cit為碳排放總規模,主要解釋變量ODI為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控制變量包括資本(K)、勞動力(L)、對外開放度(OPEN)、人均國民收入(GDP)、外商直接投資(FDI)、消費品零售總額(EXP)、研發投入(RD)、人力資本(H)等。φi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δit表示行業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
同時,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母國碳排放的傳導機制,構建和聯立方程分別為:

其中,Cit為碳排放總規模,Git表示經濟增長效應,根據C-D 函數,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資本要素投入、勞動力要素投入和對外開放度的影響。Sit為產業結構變量,主要引入了經濟增長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和需求規模的影響。Tit為技術升級效應,受對外直接投資、研發投入、人力資本以及研發投入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交叉項影響。
2. 變量和數據來源
(1)碳排放量
將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或其他管理人員數據的系統作為用戶數據的權威數據源,當人員信息出現新增或變更時,統一用戶身份管理系統獲取用戶創建或修改事件,定期掃描新變更的用戶記錄。統一用戶身份管理系統將這些事件同步給每個連接的應用系統中,各系統根據規則修改相應信息。要求各系統不能私自創建賬號或對用戶基礎信息做出任何修改,保持與權威數據源的數據一致。因此利用統一用戶身份管理能夠統一管理企業內用戶和組織機構的基本信息,并自動地為所有和統一用戶身份管理系統集成的應用系統進行用戶賬號創建、變更、注銷等工作。
根據2006 年IPCC 提供的CO2排放計算方法,碳排放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i為不同能源品種,共計8 類,E為能源消耗量,NCV是能源折算系數,CC是能源含碳量,COF是碳氧化因子,44/12是碳排放的轉化系數。

表1 各種能源標準煤折算系數
(2)對外直接投資(ODI)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初期對外投資規模都比較小,隨著資本規模的不斷擴大,發展中經濟體逐漸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對碳排放的影響才會逐漸顯現。對外直接投資有流量和存量之分,研究中都以流量代替。同時按照當年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單位為萬元。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3) 控制變量
資本投入(K):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公式為Kit=(1-δit)Kit+Iit,計算2000—2019 年的資本存量數據。預期對經濟規模效應影響為正。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
勞動力(L):雖然自動化和數字化的不斷提高,勞動力數量不斷減少,但是勞動力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就是人口紅利。因此,勞動力資本對于經濟規模效應為正。
人均國民收入(GDP):經濟規模和發展層次決定一個國家產業結構和碳排放規模,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碳排放規模也相應地降低。但是在工業化發展的早中期,收入水平越高,碳排放規模也可能越大。
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一般比東道國的產業層次稍高。隨著外資流入的增加,東道國產業結構會升級。但是也可能會產生產業固化現象,限制東道國的產業升級。
需求規模(EXP):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居民消費升級倒逼產業結構升級。背后的機理表現在恩格爾效應和鮑莫爾效應的影響。恩格爾效應反映的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會促使居民消費需求從低端產品向質量更高和更創新性的產品或者服務轉化,后者的需求收入彈性更大。鮑莫爾效應反映了生產率水平和居民消費需求的關系。因此,需求規模會影響產業結構升級。
研發投入(RD):研發投入對于技術升級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驗證。
人力資本(H):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代替,數值越高,技術創新水平也就越高,碳排放規模也會越低。
文章選擇的樣本區間為2000—2019 年,數據均取對數處理。
四、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研究模型,對跨國投資的母國碳排放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實證分為三步:第一步,利用面板固定效應估計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碳排放的影響,作為基準回歸結果;第二步,對不同類型行業做異質性檢驗;第三步,實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碳排放效應的傳導機制。
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對上述方程進行估計。表2的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對碳排放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升了中國的碳排放規模。這個結論否定了“污染光環假說”,與已有研究中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的結論相反。根據表2 中第(3)列的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1%,碳排放規模將增加0.1501%。從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來看,雖然2017 年稍有下降,但仍然呈現上升的趨勢,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碳排放規模仍然處于上升趨勢,按照中國的目標需要在2030 年實現碳達峰。從控制變量來看,資本投資、勞動力數量、人均國民收入、對外開放度、消費品零售總額等都顯著促進了碳排放的增加,在工業化早期和中期,經濟結構由輕工業向重工業轉變,包括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投入也逐漸轉移,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碳排放的增加。特別是中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而燃煤發電和供熱排放占能源活動碳排放的44%,煤炭終端燃燒排放占35%,所有涉及經濟增長的因素都在顯著增加,而碳排放也在同步增長。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顯著為正,符合“污染避難所假說”,中國吸引的外資以高碳排放的產業為主,由于發達國家較高的環境規制,跨國公司把部分高污染行業轉移到中國,使得中國碳排放的增加。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對碳排放的影響也為正,但是系數比較小,而且顯著性水平不高。一般認為,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的提升會降低碳排放,但本研究沒有證實這一點。

表2 對外直接投資碳排放效應的基準回歸結果
2.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碳排放影響的行業異質性檢驗
文章將所有制造業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碳排放特性。由于要與其他數據庫相對應,文章對行業進行了整合。估計結果見表3。

表3 分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碳排放效應
3. 對外直接投資的碳排放傳導機制實證分析
(1) 規模效應的估計結果
表4 中的估計結果從整體行業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效應為0.0836,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對外直接投資顯著促進了碳排放規模增加,但是增長的幅度不是很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2008 年以后才逐漸增加。因此,從2000—2019年的整體回歸結果看促進效應不是很大。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經濟規模增長主要依賴于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投入。資本和勞動力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3673 和0.234,并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些結論與已有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表4 經濟增長效應的估計結果
從分行業來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效應最大,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稍小,但整體各行業的影響程度都不高,資本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影響系數最大,勞動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影響系數最大。對外開放度對整體行業的影響系數為0.173,在分行業上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最大,對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影響稍低,這說明中國對外開放依賴于勞動力資源稟賦,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雖然中國近年來機電產品出口占比超過50%,但是以附加值計算的出口結果與傳統研究并不一致。在全球價值鏈下,中國進口大量國外高科技的中間產品,在中國加工組裝以后再出口,按照海關統計的貿易數據顯示,中國出口以高科技機電產品為主。但是以貿易附加值計算的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相對較高。因此,對外開放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影響最大。
(2)產業結構效應的估計結果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產業結構的變化受經濟發展水平、消費規模、外商直接投資等因素的影響。由表5 可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并不顯著,系數僅為-0.0236。從分行業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影響都不顯著。可以看出,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利用規模經濟優勢,復制在中國市場的經驗,擴大在國外投資,把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轉移到國外,特別是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貿易環境的惡化,大量產業轉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國家,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而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例較低,中國相關產業在國際上的優勢并不明顯,因此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并不突出。

表5 產業結構效應的估計結果
從其他因素看,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顯著提升了中國的產業結構。相對于國內企業來說,外資企業具有技術優勢、管理優勢和市場優勢,不僅在傳統產業上具有競爭優勢,而且在高端產業上可以復制母國的經驗,因此提升了中國的產業結構。另外,國民經濟規模、消費規模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為正,都顯著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
(3)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估計結果
從表6 可知,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顯著降低。按照全球價值鏈的觀點,國內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路徑包括三種:替代逆杠桿操作(以合資生產為起點,由最初的資金利用,到先進管理、技術、營銷方面資源積累,在此基礎上將對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轉換為自己的操作方法,逆向提升技術水平)、多點逆杠桿操作(以高起點配件生產為起點,學習國際先進的管理方式與制度,產品開發動向或者市場信息,提高自己的配件開發能力,與對方協同開發配件,甚至發展到超前開發)、縱深逆杠桿操作(以高起點配套生產為起點,取得成功后,進一步深度合作,生產更多的配件,直到能夠獨立生產)。從對外直接投資來看,中國制造企業通過跨國投資,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市場運行模式,提升國內生產技術水平。從分行業看,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最大,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相對較小。總體而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同時伴隨著顯著的行業差異。

表6 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估計結果
(4) 總體效應分析
前文分別從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據此研究獲得了對外直接投資碳排放的總體效應,結果見表7。

表7 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碳排放總體效應 (單位:%)
對外直接投資對整體碳排放的效應為0.1501%,說明對外直接投資每增長1%,國內碳排放總量將增長0.1501%,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并沒有減少碳排放,反而增加了碳排放,這顯然不符合“污染避難所”假說。分解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規模效應的影響最大,并且顯著為正。而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系數為負,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通過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降低了碳排放。但是由于規模結構效應的影響系數較大,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經濟增長效應拉動了碳排放,結合中國碳排放強度的下降趨勢,雖然碳排放強度有所下降,但經濟規模增長較大,仍然在較大程度上促進了碳排放的增加。
五、結論和建議
與工業革命前相比,目前全球變暖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將對全球生存環境造成嚴重沖擊,給經濟和社會造成危害,綠色發展與實現碳中和是國際社會共同矚目的熱點問題。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因此如何降低碳排放成為各國政府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對于中國來說,一方面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碳排放還沒有達到頂峰,另一方面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導致碳排放規模居于全球首位。如何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對于中國來說更具有現實意義。碳中和倒逼產能提效降耗,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對外直接投資是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途徑,其對于降低碳排放規模的作用尚需理論和實踐的檢驗。雖然已有很多研究證明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污染避難所效應”和“污染光環效應”,但這些研究針對的是環境污染,而不是針對碳排放。針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碳排放效應,特別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碳排放的影響,還需要進行檢驗。文章基于2000—2019 年的數據,分解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然后對這些效應進行匯總,研究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降低母國的碳排放規模,反而發揮了促進作用,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規模效應拉動母國碳排放,產業結構效應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可以降低碳排放。通過對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分類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勞動密集型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碳排放效應都為正,說明所有類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沒有降低國內的碳排放。這個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政策含義。
1. 繼續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隨著中國制造業在國內市場取得競爭優勢,也需要不斷走出國門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制造業加快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采取包括跨國并購和綠地投資等方式,不斷擴大走出去的規模,逐步形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雙向拓展的全球投資布局,投資結構由資源獲取型向技術引領型和構建全球價值鏈轉變,同時對外投資對于拉動外貿出口、促進產業轉型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還存在區域過于集中、行業比較單一的問題。有必要在財政金融支持、地區經濟政治風險保障和構建完善科學規范的政府服務制度體系方面,進一步加大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2. 加強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分類指導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不同類型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碳排放效應雖然都為正,都促進了母國碳排放,但是影響系數存在差異。勞動密集型行業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系數較小,因此應該進一步加大勞動密集型行業、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力度,把大量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組裝環節轉移到印度、越南等低成本的國家或者地區,將產業鏈中高環節留在國內,一方面可以降低國內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也實現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國內附加值高環節的出口。資本密集型行業是碳排放規模最高的行業,包括金屬和非金屬冶煉、金屬和非金屬制品、電力生產等都是高能耗碳排放最多的行業,這些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大,而且其本身的碳排放規模較大且處于上升過程之中,無論是規模效應還是產業結構效應、逆向技術溢出效應都還處于促進碳排放的過程。因此,更需要加大國內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力度,把相關產能轉移到資源豐富且交通便利的國家。
3. 加大獲取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力度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可以降低碳排放,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表現得都非常明顯。因此,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擴大技術需求性直接投資,學習國外更多的低碳清潔技術;政府把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視為政府扶持的重點,加大在發達國家技術研發型投資的補貼等支持力度,促使企業通過聯合研發、新建子公司或跨國并購等方式獲取技術。同時,在國外獲取的技術,需要在國內吸收消化,進而提升技術創新水平。特別是目前國外加大對中國技術性投資獲取技術限制的力度,需要政府協助營造良好的環境,讓企業能夠按照市場規則獲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