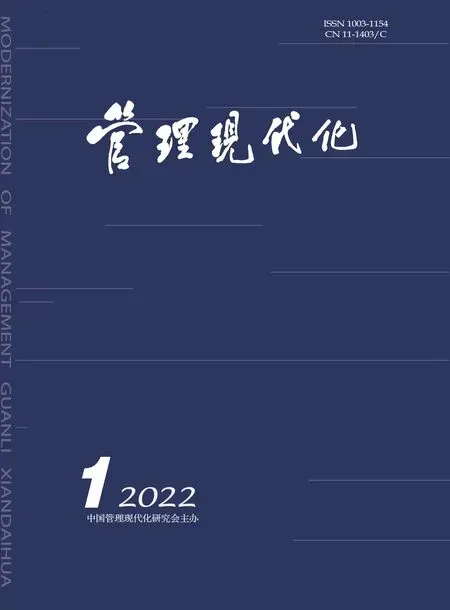中國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的統計測度
□ 王瑞梅
(1.江西財經大學, 江西 南昌 330013; 2.江西理工大學, 江西 贛州 341000)
一、引 言
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在促進農村經濟健康發展以及推動中國邁向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發揮關鍵作用。而農業保險可夯實農業發展的頂層支持,已經上升為國家重要農業政策,為“三農”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早于2018年中國銀保監會聯合四部門發布了《關于金融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意見》,強調保險行業參與農業農村領域,助力貧困地區打贏脫貧攻堅戰。在關聯政策推動下,農業保險市場規模顯著增長。據銀保監會統計,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迅速,從2007年的53.3億元增加至2020年的814.93億元。中國已成功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農業保險市場。特別是在鄉村振興戰略落實過程中,金融機構不斷強化農業保險的產品和服務供給,為防止脫貧農民“因病因災返貧”提供解決方案,助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隨著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深入實施,農業保險在農業農村領域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由于農業本身具有弱勢性與基礎性特征,農業保險在助力脫貧攻堅過程中仍存在針對性不足等問題。加之受國內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影響,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逐漸削弱。這不僅制約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還不利于全面脫貧成果的鞏固。在此基礎上,鞏固農業保險反貧困成果不僅利于全面脫貧攻堅成果的鞏固,還利于切實解決“三農”工作問題,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具有極強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現階段,學界對于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在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的理論研究方面,左停等(2019)[1]認為農業保險在反貧困進程中發揮極大作用,可通過主體、資源、能力與目標四項關鍵要素,防止居民陷入貧困現狀。張棟浩等(2021)[2]在研究農業保險內涵特征與發展條件基礎上,分別從內在驅動、外部因素兩個角度剖析其反貧困路徑。在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的研究方法方面,黃穎等(2021)[3]立足于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IV-Probit方法,對中國農業保險進行分區域調查,研究農業保險管理機制與反貧困路徑間的聯系。李嬋娟等(2021)[4]則運用空間計量方法,實證評價農業保險發展效率的空間收斂趨勢和影響因素。
綜上所述,學界對于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為進一步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寶貴經驗與可行參考。但就深入研究內容而言,學界既有關于農業保險反貧困研究的文獻多局限于典型區域亦或是特定省份[5],鮮有學者對全國范圍內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進行系統性分析。就研究方法而言,現有學術成果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模糊綜合評價法(FCE)有賴于主觀進行權重賦值,層次分析法(AHP)的分析質量會隨要素選取合理性與要素間關系正確性而波動,單階段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難以控制決策單元的非經營性因素。三階段DEA模型基于傳統DEA的多投入、多產出特征,無需考量權重量綱,有機結合SFA剝離外部因素,可使每個決策單元均處于相同外部條件與隨機因素,更契合農業保險反貧困研究需要[6]。本文以上述研究作為切入點,采用三階段DEA模型,借鑒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建構投入—產出—環境指標體系。在剝離外部因素與隨機誤差的影響后,對中國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進行研判,并提出相關建議與優化方向。本研究有利于促進農業保險反貧困理論實踐、加快國內農業保險反貧困進程,推動鄉村戰略走深向實、共同富裕目標逐步實現。
三、研究設計
(一)三階段DEA模型
三階段DEA模型能可剔除實證模型的環境因素和隨機干擾,具備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可確保研究準確性。參考郭軍華等(2010)[7]就相關實證模型的研究范式,建構三階段DEA模型如下:
1.第一階段,傳統DEA模型。對初始面板數據的投入與產出指標展開基礎效益測算,得出技術效率(TE)、規模效率(SE)以及純技術效率(PTE),TE=SE·PTE。選擇以投入作為導向的BC2模型(即規模回報可變),就樣本數據展開實證分析。具體模型建構為:
min[θ-ε(eTs-+eTs+)]
其中,i為決策單元(DMU),Xi為第i項DMU投入,Yi為第i項DMU產出,s-表示投入松弛變量,s+表示產出松弛變量,θ代表各項DMU的純技術效率數值,λi則表示第i項DMU系數。
2.第二階段,SFA模型。以第一階段DEA為基礎,估測外部因素對DMU所帶來的影響。這一過程需要對投入變量展開差額分析,剔除外部環境與隨機誤差,使投入值更貼合現實情況。第二階段模型回歸將第一階段回歸所得出的投入松弛變量視作解釋變量,將外部變量視作被解釋變量,然后進行模型回歸。該階段建構SFA模型如下:
Sni=f(Zi;βn)+vni+μni
i=1,2,…,I;n=1,2,…,N

開展SFA模型回歸是為使全部DMU置于同一外部條件下,剝離外部環境與隨機誤差對DMU帶來的干擾。是以,對公式展開如下調節:
[max(vni)-vni]i=1,2,…,I;n=1,2,…,N

參考黃桂琴(2021)[8]探究配置無效率的研究方法,建構配置無效率分離公式:

基于上述公式調整,得出隨機誤差項分離公式:
E[νni|νni+μni]=sni-f(Zi;βn)-E[μni|νni+μni]
3.第三階段,調節投入變量后的DEA模型。此處將其與初始產出變量數值代入第一階段DEA模型實證回歸,為提升此處實證分析信度與效度,選用基于投入導向的BCC模型展開效率測度,得出剝離外部環境與隨機誤差的實際效率數值。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選取的面板數據為跨年份型。因差異年份的生產前沿面存在異質性,經由分年份測度得出的效率數值不可直接進行比較。這也意味著對差異性年份DMU測算所得的效率數值不具備可比性,無法分析其時序演變態勢。為紓解跨年份面板數據為效率計算帶來的困厄,參考學界既有研究方法[9-10],采用面板三階段DEA模型,將跨年份面板數據轉為更具信度與效度的截面數據進行處理,然后展開實證檢驗。
(二)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說明
為保證數據可得性與連續性,選取中國除港澳臺外31個省級行政區2010—2019年的面板數據。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中國金融年鑒、知網數據庫、Wind數據庫,部分指標在原始數據基礎上采用平均值插補法計算得出。在借鑒既有相關研究基礎上[11-13],結合研究需要,構建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1.投入變量選取。投入變量可客觀展現省域農業保險反貧困內部投入。農業保險反貧困作為一項經濟活動,其現實運作可以從機構建設、覆蓋密度、建檔參保、財政補貼、自繳保費、出險理賠六方面考量。其中,基層保險服務機構是承接農業保險的一線主體,在農業保險反貧困進程中起基礎性作用,故以農村保險機構服務站數量(X1)對其進行表征。各個農戶對于自然災害損失保險、病蟲害損失保險、疾病死亡保險、意外事故損失保險等農業保險險種的微觀參與情況,可由農業保險投保覆蓋密度(X2)反映。隨著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貧困戶成為過去。著眼于農業保險的反貧困效能,曾在農村建檔立卡貧困戶的保險參與情況尤為值得關注,故以建檔貧困農戶參保比例(X3)對其進行度量。保費投入是農業保險投入的直觀反映,其大范圍開展有賴于政府專項財政補貼與農戶自籌保費資金。基于數據可得性,以農業保險保費財政補貼(X4)與農業保險自繳保費數額(X5)衡量農業保險資金投入。在現實環境中,農業保險效能主要經由兌付出險賠償金來發揮。農業保險理賠直接影響農戶經濟情況、參與農業再生產,以農業保險出險理賠數額(X6)表征。

表1 指標說明
2.產出變量選取。產出變量選取目的與標準為體現各省域農業保險效率,主要反映農業保險反貧困在農村與農戶兩個維度取得的進展。就農村層面來看,農業增加值即農林牧漁在一定時期內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形塑社會勞動量的貨幣表征,具有一定研究意義,故將其作為變量之一(Y1)。具體為農林牧漁業現價總產值扣除農林牧漁業現價中間投入后的余額。糧食穩產增產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核心要義,也是保障農村反貧困的關鍵所在,以農業糧食增產(Y2)進行度量。農村經濟發展對于中國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亦是反貧困的強大驅動,以農村人均GDP增長率(Y3)反映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就農戶層面來看,生產經營作為農戶主要經濟來源,直接影響農戶生產生活與農村反貧困進程,以農戶生產經營規模(Y4)表征。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經營性收入已成為農戶收入的新興增長點,以農村人口經營性收入(Y5)反映。消費支出作為農戶生活方式變革、可支配收入變化的直觀表現,值得在反貧困進程中引起關注,采用農村居民消費支出(Y6)表征。
3.環境變量選取。環境變量是影響農村反貧困工作開展效率的外部環境因素。財政投入是來源于社會經濟的財政對社會經濟進行反向干預,對農村反貧困意義深遠,以公共財政投入(Z1)度量。農村非農戶固定資產投資是農村各種登記注冊的企業、事業、行政單位進行計劃總投資500萬元以上的建設項目,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經濟基礎與現實依托,故將其作為研究變量,以農業固定資產投資(Z2)表示。農業機械化和農機裝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重要基礎,可大力促進農業提質增效,以農用機械使用率(Z3)反映。夯實農業經濟基礎、補齊農業發展短板,有利于促進宏觀經濟增長,增加農民和農民工收入,進而實現反貧困目標。2020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6.7億噸,為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提供有力支撐,故以農業GDP經濟增長(Z4)表征農業增長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為90 199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3.89%。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關鍵指征,對反貧困具有極大推動作用,因此以居住在大、中、小城鎮中的人口占城鄉總人口的比例反映城鎮化水平(Z5)。農村社會救濟是國家與社會對農村生活困難群眾提供物質幫助的一種社會救助,與農業保險并行對中國反貧困工作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以農村社會救濟(Z6)對其刻畫。
四、實證分析
(一)第一階段:傳統DEA效率測算
基于前述研究方法,采用DEAP2.1軟件,選取投入導向、規模回報可變的BC2模型,測算得出不同年份下各省域的技術效率(TE)、規模效率(SE)以及純技術效率(PTE)。由于樣本數量與面板數據較多,此處僅展示10年間各省域技術效率、規模效率、純技術效率的平均值(表2)。

表2 第一階段DEA效率測算結果
就技術效率(TE)而言,2010—2019年各省域TE的均值是0.472,效率損失高達53%。這表明從時間角度整體來看,農業保險既有技術效率水準較為低下。從不同年份技術效率數值排列來看,各年份技術效率普遍處于低位,除2011、2016、2017、2018、2019年,其余年份的技術效率數值均低于0.5,且全部年份的技術效率數值未超過0.6。但不難看出,近年來全國與各省域的技術效率值整體表現出波浪式攀升趨勢(如圖1)。這一趨勢自2016年起表現得尤為明顯。就純技術效率(PTE)而言,2010—2019年各省域的PTE均值是0.575。不足六成的數值水平說明國內農業保險反貧困的純技術效率仍處低位,農業保險經營運作水平有待提升。從不同年份純技術效率數值排列來看,除2010年外,其余絕大多數年份效率數值均高于0.5。同一時期,PTE整體數值隨時間推進展現出波動走高態勢。這意味著國內農業保險的經營模式與落地運作處于持續優化過程,為中國農村反貧困進程帶來一大利好。就規模效率(SE)而言,2010—2019年國內各省域規模效率均值為0.791,較之技術效率與純技術效率處于較高位,但整體而言仍存上升空間。從不同年份規模效率數值排列來看,除2011、2013、2016年出現過較大浮動,整體發展態勢平穩,且近3年來(2017—2019年)規模效率數值均超過0.8。從導致效率損耗的原因來看,TE損失的近53個百分點中有57.64%是由PTE無效造成,42.36%是由SE無效造成。

圖1 2010—2019年效率變動
由于各地區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存在區域異質性,依據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大陸區域劃為東、中、西、東北四部分,展開區域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測度(見表3)。
據表3可知,2010—2019年TE數值最低的省級行政區是甘,數值為0.056;最高的是京,數值為0.881。PTE數值最低的省級行政區為寧,數值為0.096;最高的是魯,數值為0.999。SE數值最低的省級行政區是藏,數值為0.211;最高的是渝,數值為0.928。國內各省域的TE、PTE以及SE均值各為0.487、0.587與0.716,均有不同范圍的提升空間。從地區分布來看,東部區域TE與PTE數值均為四大區域中最高。SE數值最高的區域為中部。這可能是因為中部區域為國內糧食產量較高、耕地分布密集的農業集中地域,規模化程度較優。東北區域的TE數值最低,西部區域的PTE與SE最低。各區域的效率數值都表現出SE數值最高、PTE數值居中、TE數值最低的現狀。這體現出綜合技術效率較低可能與純技術效率持續走低有關。

表3 2010—2019年各省域效率均值
(二)第二階段:SFA回歸
通過第一階段DEA效率測算,得出各項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見表4)。在第二階段,將六個環境變量——公共財政投入、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用機械使用率、農業GDP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農村社會救濟作為自變量。借鑒學界既有研究方法[14],將投入變量中反映農業保險覆蓋密度與出險理賠兩項關鍵指征的核心變量作為因變量,即農業保險投保覆蓋松弛和農業保險出險理賠松弛。經由Frontier4.1軟件,選擇面板SFA模型展開最大似然估計,以此調節投入變量。

表4 第二階段SFA回歸結果

由表4第二列可知:第一,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變量系數是-0.592,通過1%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與農業保險投保覆蓋松弛具備顯著負相關。隨著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增加,農業保險投保覆蓋松弛走低。農業技改項目、基礎設施建設、農林牧漁服務業經營等類別的投資擴大可推動農村反貧困效率攀升。第二,公共財政投入的變量系數為2.579,通過1%顯著性檢驗,說明公共財政投入與農業保險的投保覆蓋程度表現出顯著正相關。隨著公共財政投入擴大,農業保險投保覆蓋松弛持續走高,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則不斷降低。這可能是由于在全國財政公共預算用于農林水的支出中,部分項目必要性與可行性仍有待商榷,致使資金投入并未得到高效利用與效能發揮。是以,部分公共財政投入效率持續走低,難以切實推動農業保險反貧困落地、助力農業發展與農戶收入提升。第三,農用機械使用率、農業GDP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農村社會救濟四項變量的系數各為-0.368、-1.853、-1.174、-0.893,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征這四項指標與農業保險投保覆蓋松弛呈負相關。隨著資金投入的擴大,農業保險投保覆蓋松弛不斷降低,反貧困效率得到拉升。這可能是由于農用機械使用率提升、農業GDP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提高、農村社會救濟落實都會提升農戶的生產積極性。由此增加農業生產經營投入,使得農戶生產經營規模不斷擴大,進而推動農業產出增加與農戶收入提升。
由表4第三列可知:六項環境變量中僅有公共財政投入的變量系數具備顯著性,為0.042,通過1%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公共財政投入和農業保險出險理賠松弛具備顯著正相關。隨著公共財政投入的增加,農業保險出險理賠松弛不斷高漲,其反貧困效率愈加走低。如前所述,公共財政在農林水等項目可能存在粗放式投入的問題,財政資金并未得到合理配置,致使投入效率長期處于低位。因而其未能切實推動農業發展、改善農戶生活,也難以提升農業保險反貧困效能。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用機械使用率、農業GDP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與農村社會救濟五項指標的變量系數符號為負,但都不具備顯著性。這可能是由于前述變量的投入反映出農戶生產積極性增強,利于擴大生產經營規模,促使其對于農業生產風險的抵抗能力也有所提升,進而大幅拉升農業產出與自身收入。
(三)第三階段:DEA模型回歸
在第二階段SFA回歸剝離外部因素與隨機干擾的影響后,把經過調節的投入變量數值與初始產出變量代入一階段DEA模型回歸。通過DEAP2.1軟件,選擇基于投入導向且規模報酬可變的BC2模型,得出調節后的實際技術效率(TE)、規模效率(SE)以及純技術效率(PTE)數值。此處將其與第一階段效率數值進行比較(如表5),分析調節后2010—2019年各省級行政區的效率均值與變動態勢。

表5 第三階段調節后效率均值
就全國而言,經過投入變量調節后,2010—2019年國內大多數省域的三類效率數值均有攀升,僅有少部分省域有所降低。全國平均TE、PTE與SE分別為0.608、0.696與0.769,較第一階段的各項效率數值0.487、0.587、0.716而言,各上漲0.121、0.109與0.053。這表明環境因素對于TE、PTE與SE會產生顯著影響。就微觀角度而言,著眼于技術效率,津、閩、桂、瓊、渝、貴、藏、青8個省域的TE數值均有所回落,其余省域TE數值都有不同程度提升。著眼于純技術效率,津、浙、閩、桂、瓊、藏、青7個省域的PTE數值出現下降現象,魯的PTE數值與前持平,其余省域均有所上升。著眼于規模效率,津、晉、滬、皖、湘、渝、貴、藏、陜、甘10個省域的效率數值略有降低,其余省域SE數值均呈現攀升態勢。津是全部省域中唯一一個三項效率數值均有降低的省級行政區。魯在全部省域中各項效率數值最高,三項數值各為0.969、0.999、0.968,位于效率前沿面。
就區域維度而言,東、中、西、東北四大區域的TE、PTE與SE數值均有所提升。從綜合效率狀態來看,東部最優,而后依次是東北、中部與西部。從純技術效率來看,東北PTE數值最高,其次是東部,再次是中部與西部。從規模效率來看,中部SE數值高于其他三大地區,而后依次是西部、東部與東北。
整體來看,東北與東部的TE與PTE顯著高于西部與中部;SE則略低于西部與中部。究其原因,中、西部規模效率數值較高,可能是因為中西部區域是國內欠發達地區與相對貧困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農業保險反貧困項目率先在此類地區進行試點與推廣,促使該地區農業保險發端較東部與東北區域更早。同時,中西部區域地理總面積與耕地總面積在全國范圍內占比較高,豫、冀、鄂等中部省域與川、陜等西部省域均為農業大省,較早地形塑起規模效應,所以其SE數值較高。東北區域的純技術效率領先于中西部,可能是地區既有經濟基礎與農業發展水平的外在反映。東北地區不僅是中國的老工業基地,更是糧食主產區之一,且具有地廣人稀、農業條件優越、農業機械化程度高等特點,因而其純技術效率數值極高。東部區域的技術效率優于其他區域,這極有可能是因為這一區域經濟較為發達、技術程度較高,且管理水平較高,故擁有較高技術效率。
就時間維度而言,三項效率數值在調節變量后較之于第一階段,除2010與2011年規模效率數值有所回落、2019年未發生改變外,其余年份各項效率均值全部有所上升(如表6所示)。這證明了第二階段通過環境變量與隨機沖擊實施調節的可行性與必要性。2010—2019年,TE數值分布于[0.5,0.7],PTE數值分布于[0.65,0.8],SE數值分布于[0.78,0.9]。從總體態勢來說,TE、PTE與SE三項效率均處于波動變化的進程之中(圖2)。

表6 調節后2010—2019年各年份效率數值

圖2 變量調節后2010—2019年效率數值變動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中國除港澳臺外31個省級行政區2010—2019年面板數據,通過三階段DEA模型對國內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進行統計測度,得出結論如下:(1)中國農業保險反貧困總體收效良好,農保反貧困效率逐年攀升。在剝離外部因素與隨機干擾后,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得到進一步提升。農業保險技術效率的上升有賴于純技術效率的優化,說明近年來中國對于農業保險的投入取得顯著效率,農業保險管理運作水平不斷提高,農業保險規模效率持續企穩。(2)就區域維度而言,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數值均較第一階段明顯提高。然而,不同區域間三項效率狀況也具有一定異質性。從綜合技術效率來看,西部<中部<東北<東部;從純技術效率來看,西部<中部<東部<東北;從規模效率來看,東北<東部<西部<中部。東部與東北地區的綜合技術效率與純技術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區,但其規模效率較中西部略低。(3)就時間維度而言,變量調節后2010—2019年效率數值均較第一階段有所攀升(除2010與2011年規模效率數值有所回落、2019年未發生改變)。農業保險效率水平的整體時序變動呈現出波動式上升態勢。(4)在六個環境變量之中,公共財政投入擴張會導致農業保險反貧困效率降低;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用機械使用率、農業GDP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以及農村社會救濟投入則有利于推動農保反貧困效率的拉升,但這一影響路徑并未通過顯著性驗證。
上述結論為中國農業保險提升反貧困效能提供思路:(1)因地制宜落實農業保險關聯配套政策。從前述實證回歸結果看,不同省級行政區農業保險所取得的反貧困效能具有異質性。行政主體應將各地既有經濟基礎、農業發展水平納入考量,制定契合區域反貧困實際的農業保險發展規劃。同時,應在純技術效率較低的中西部區域加強技術扶持性農業保險投入,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機械化與智能化水平。在規模效率有待提升的東部與東北區域,應著力擴大農業保險經營規模與覆蓋范圍,提升保障密度與規模效能,由此推進綜合技術效率拉升。(2)科學合理優化公共財政投入資源配置。由實證結果可知,公共財政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農業保險反貧困進程起到負向影響,抑制其效能發揮。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用機械使用率、農村社會救濟等要素則對農保反貧困形成助力。因而,行政主體在實踐中應縝密籌劃公共財政在農林水等各項事務的投入支出,強化與其他生產要素的握指成拳、協調聯動,由此多元提升農業保險反貧困成效。(3)積極借鑒國際農業保險反貧困發展經驗。當前,國內農業保險尚處于藍海階段,險種有待豐富、結構有待優化。中國在持續推動本國農業保險穩健發展的同時,應以開放態度借鑒國外農保建設經驗,在保險產品供給、市場交易服務、精算技術支持等領域提升農業保險水平,助力反貧困工作走深向實。(4)探索實踐創新農業保險發展模式。既往農業保險在推動農業生產經營、增加農戶實際收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源于各地區、各機構展開多元農業保險反貧困模式的開發與探索。這符合農村發展、農業增產、農戶經營需求的農業保險會自發形成示范效應,在溢出效應的驅使下帶來更多利好。為適應中國反貧困進程的新形勢與新需要,行政主體應深入探索農業保險和農業生產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不斷推動農業保險發展路徑優化與發展理念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