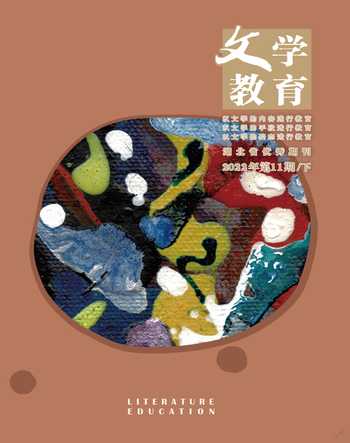電影《花木蘭》的跨文化維度解析
陳紅
內容摘要:近年來,全球化的發(fā)展極大地促進了文化領域的交流。作為中國經典文化瑰寶,花木蘭傳奇,逐漸成為跨文化領域熱議的話題。借鑒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從跨文化角度分析迪士尼電影《花木蘭》在中西文化融合中的呈現與意義。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涉及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權力距離、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不確定性規(guī)避等方面。對美國電影《花木蘭》中的中國傳說人物“花木蘭”的文化維度分析,有助于理解中西視域下花木蘭形象的演進,更好地闡釋“木蘭”這一文化符號的內涵。
關鍵詞:《花木蘭》 跨文化交流 文化維度理論 多元文
花木蘭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故事講述了主人公花木蘭如何從普通的鄰家少女成長為馳騁沙場、榮歸故里的女英雄,其中的女扮男裝、替父出征、沙場點兵、凱旋而歸等情節(jié)為人熟知,突出表現了木蘭的善良、果敢、勇于擔當的優(yōu)秀品質。從樂府民歌《木蘭詩》中的“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到豫劇電影《花木蘭》的“劉大哥講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享清閑”,木蘭傳奇一直被續(xù)寫、傳承,早已成為歌頌中國傳統女性光輝形象的經典敘事作品。
一.電影《花木蘭》在美國拍攝上映
二十世紀以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日益頻繁,中國經典文化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也被更多地挪用進西方文學、影視作品之中。作為美國流行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電影早已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通過影視手段,電影對敘事話題和人物進行了加工與重新呈現。迪士尼是一家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影視公司,其真人版影片《花木蘭》通過對中國家喻戶曉的巾幗英雄的影視塑造,參與到“花木蘭”敘事話語之中,“喚起人們對遙遠傳說的回憶”。[1]25這部影片以獨特的視角再現了花木蘭傳奇,與中國古代詩歌《木蘭辭》,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的小說《女勇士》等藝術作品共同豐富了“木蘭敘事”,是中西視域融合的產物。
借鑒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從跨文化角度分析迪士尼電影《花木蘭》能夠從中發(fā)現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式和意義。吉爾特·霍夫斯泰德認為文化分為不同的層次,而價值是文化的核心。“不僅國家之間的文化多樣性一直留存下來,國家內部的差異性似乎也在增加。種族群體對其身份有了新的認知,并且呼吁對這一事實的政治認可。當然,這些種族差異其實始終存在。改變的只是群體之間的接觸程度,而這一點又進一步強化了群體成員對自己的身份認同。”[2]384-385這種文化多樣性精彩地演繹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和交融,幫助讀者增進對于花木蘭形象的多元化理解,也有助于豐富其文化內涵。
二.花木蘭形象的文化維度解析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包括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權力距離、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不確定性規(guī)避等方面。“霍氏文化差異維度理論把文化分解成易于辨識的要素特質,為人們提供了觀察不同文化差異性的‘坐標系,是人們可以暗中不同那個的文化維度來認識不同國家文化差異,處理文化沖突。”[3]產生于中國古代父權社會下的花木蘭傳奇凸現了女英雄形象,它將女性的善良孝順與男性的果敢堅毅集于一體。在當今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下,花木蘭的故事走出了國門。它與西方思想理念相融合,展現出“高權力國家”背景下個體的獨特發(fā)展。對美國電影《花木蘭》中的中國傳說人物“花木蘭”的文化維度分析,有利于理解中西視域下花木蘭形象的演進,更好地闡釋“木蘭”這一文化符號的內涵。
(一)集體主義影響下獨特的女英雄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是霍夫斯泰德關注的重要文化維度,霍氏認為“個體主義指的是人與人之間松散聯系的社會:人們只照顧自己及其核心家庭。而集體主義指的是這樣的社會:人們從出生起就融入到強大而緊密的內群體當中,這個群體為人們提供終身的保護以換取人們對于該群體的絕對忠誠。”[3]80-81集體主義強調集團內部互相照顧,并保持忠誠;而個體主義則看重個人成就和競爭意識。[4]前者要求群里內部成員間要相互信任和保持忠誠,遵守秩序、統一思想、服從命令,因此社會等級感強;與社會等級分明的前者相比,后者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為了成就個體的獨特發(fā)展,成員間的關系常常既是伙伴又是競爭對手。
在迪士尼電影《花木蘭》中,木蘭的形象正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通過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得到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這部電影以中國花木蘭傳說為藍本,其中的替父出征、舍身救人等電影情節(jié)反映出的以“仁”、“義”為基礎的中華傳統美德,是集體主義的寫照。但是,與中國傳統的木蘭形象相比,影片中的花木蘭具有鮮明獨特的個性特征:影片從一開始就告訴觀眾這是一個“我的”的故事,不同于其它描寫木蘭的故事。當木蘭聽到父親關于“氣是為戰(zhàn)士的準備的”,“把你的天賦藏起來、并壓制它的聲音”等告誡后,她沒有無條件服從,而是對自身強大的氣和父親的訓誡深感困惑。不同于傳統木蘭敘事,影片將重點放在了木蘭隱瞞身份進入軍營后的經歷。在這里,木蘭面對著種種挑戰(zhàn):花軍的新身份使得她必須用智慧、勇氣和堅強等男性氣質特點為國效力;她常常在女性身份和男性偽裝之間掙扎不安;和敵方女巫的交鋒使得她尷尬的處境雪上加霜。面對女巫“你是誰?”的質問,她勇敢地選擇面對真實的自我,向戰(zhàn)友說明自己女性的身份。暴露身份被逐出軍營后,木蘭不得不學會處理自我價值和社會期望的沖突。終于,木蘭利用謀略和真誠說服了戰(zhàn)友,共同打敗敵軍,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這印證了個體主義。在故事的最后部分,木蘭的勇敢和堅韌感動了女巫,二人最終和解;木蘭也榮歸故鄉(xiāng)和家人團聚,同時改變了花父對于女性角色的偏見。這里體現了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互助精神和相互理解。
這部電影在展現花木蘭作為中國優(yōu)秀女性形象杰出代表的基礎上,賦予了人物鮮明的個體特征,使其形象更加立體化,成為儒家思想集體主義和西方個體主義結合的產物。首先,電影生動刻畫了在中華集體主義映照下,花木蘭既孝順懂事、善解人意,又肩負著保家衛(wèi)國、英勇殺敵的軍人使命,著重指出了女主人公的忠、孝、勇、毅的品質。其次,在集體群像襯托的鮮明對比下,花木蘭形象具有了新的內涵:不同于以往木蘭敘事中過分強調其作為傳統中國女性的形象,電影中的木蘭盡管痛苦和掙扎,主動承認女子身份,接受大家的猜疑和指責。她敢于直面命運,打破社會陳規(guī)挑戰(zhàn)傳統。最后她通過自身的努力幫助人們擺脫了偏見,贏得大家的尊重和認可。這恰好體現了中西文化價值觀的有機融合。
(二)權力距離與木蘭的無聲反抗
霍夫斯泰德提出權力距離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組織和機構中,弱勢群體對于權力分配不平等表現出的期待和接納程度”。[2]49它反映了社會等級關系和規(guī)則制度,人們根據身份和分工的不同,擁有各自的地位,行使不同的權利和責任。權力距離的高低正是說明了社會內部成員間地位的差異和社會關系的不同:在高權力距離國家中,等級制度嚴明,財富的分配根據人的地位而定,為了穩(wěn)固社會結構,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弱勢群體服從強勢群體,個體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而在低權力距離的國家中,人民追求平等、自由,社會環(huán)境較為寬松,個體期望得到認可和尊重。集體為個體發(fā)展提供基礎和保障,集體的發(fā)展又依賴于個人間的合作。不同于高權力距離文化中個人服從集體的上下級關系,協商和共贏是低權力距離文化所追求的目標,它強調個體和集體共生互補,彼此促進。
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強調君臣、父子、夫婦、長幼要守秩序,朋友間要講義氣。這種五倫的思想正是高權力距離的充分體現。電影《花木蘭》中多次出現沉默的場景反映了木蘭在高權力距離下做出的反應,或無奈服從、亦或積蓄力量。故事一開始,花父就告誡木蘭要隱藏其強大的氣來給家族帶來榮耀。少年木蘭聽后,雖然傷心不滿,但卻保持了無奈的沉默。成年后,木蘭沒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利,屈從于傳統的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那是服從的沉默。面對柔然敵軍猛烈的進攻,為了營救戰(zhàn)友,木蘭不得不暴露女性身份,被驅逐軍營時,她再一次選擇了沉默,但這次的沉默不代表著無奈和屈服,而是對于權力距離的無聲挑戰(zhàn)。在木蘭和女巫的交鋒的過程中,后者以一種以激進的反抗者的身份,迫使木蘭不得不正視自己的性別偽裝。經歷了內心矛盾和沖突,木蘭敢于直面女性身份,逐漸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也成功地營救了國王和戰(zhàn)友。木蘭的沉默表明在高權力距離因素的影響下,個人尋求發(fā)展遇到阻礙后內心的困惑和掙扎。這說明在等級制度森嚴的古代中國社會,個體想要自由、平等的發(fā)展,不僅需要外在的有利條件,更需要自身的勇氣和膽識。
沉默這一復雜現象,可以表示同意、默許甚至委屈;另一方面,“又代表著感受的深刻、立場的嚴肅和能量的積蓄”。[5]影片《花木蘭》中的沉默不僅表達對未來的無奈和自己的婚姻不自由,更探討了高權力距離對于女性身份和個性發(fā)展的阻礙作用,揭露當時社會權力分布嚴重的不均衡現象。在困境中,從無奈和屈從的不發(fā)聲,到為了堅守理想和信念的沉默,再到一飛沖天的勇氣和魄力,木蘭逐漸成長為兼具中國傳統婦女美德和西方人文思想的女英雄形象。電影對花木蘭故事的改編融入了西方文化元素,豐富了中國經典文化的內涵。此外,在與西方人文思想交流的過程中,花木蘭形象的演變標志著中西文化的結合,它也煥發(fā)新的生機,散發(fā)出獨特的藝術魅力。
(三)陰柔氣質和陽剛氣概糅合的產物
一般來說,陰柔氣質包括溫柔、感性和體貼等特點;陽剛氣質則包含理性、堅韌和務實等特征。霍夫斯泰德認為“一個個體可以同時具有陽剛氣質和陰柔氣質的特征”。[2]131作為女性的花木蘭,善良、孝順,聽從母親的安排,想通過相親來增加家族的榮耀。之后,出于對于父親身體狀況及安危的擔憂,冒險頂替父親入伍參軍;化身男性身份——花軍后,“他”甘于吃苦、英勇殺敵、援助戰(zhàn)友、營救皇帝。因此,在花木蘭的身上,女性的陰柔氣質和男性的陽剛氣概同時并存,并將二者完美結合。
中西方哲學都曾論及陽剛氣質和陰柔氣質的雜糅。中國古典書籍《山海經》中記載了天地初為一片混沌之氣,而后盤古生于其中,最后幻化成山川河流,鳥獸魚蟲等。道教思想家老子認為萬物之源為道,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陰陽相互作用的思想。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中氣為本元,陰陽相濟、互補融合的觀念。在古希臘,伊奧尼亞學派的哲學家阿那克西美尼認為萬物的始于氣,氣產生日月星辰,這和女性氣質陰柔的氣質相吻合。同時,氣質地似水,具有流動性,又代表著活力,因此又具有男性陽剛的氣質。影片中,氣作為男勇士的重要特征和專屬氣質,木蘭為代表的女性戰(zhàn)士對之向往。傳統的男女氣質觀受到了挑戰(zhàn)。但最終,新的社會身份的獲得—加入皇帝護衛(wèi)隊標志著木蘭獲得了社會認可,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可以在某一個體兼容。作品的創(chuàng)新意義不言而喻。
在電影《花木蘭》中,花木蘭形象完美結合了男性陽剛氣質與女性陰柔氣質。在影片中,氣是一個反復出現的意象符號,自然的豐沛之氣和木蘭的女性氣質交相呼應,幫助木蘭很好地利用這種和諧共處的關系,在危險或嚴酷的環(huán)境中,從容應對、化險為夷。隨著木蘭的成長,這股女性氣質散發(fā)出更強的活力。可是,在父權社會中,氣被賦予了男性主義的特征,具有了武力和強權的內涵。影片中,當花父發(fā)現木蘭體內蘊藏著源源不斷的氣,他告誡木蘭隱藏她的氣,并且學會壓制女性的聲音。這是傳統封建社會中存在的一種偏見,氣被貼上了男性主義的標簽,認為只有男勇士才能夠擁有并使用氣。反映著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和不認可,也使得木蘭困惑不已。但憑借超凡的決心和勇氣,木蘭在軍事訓練時脫穎而出;被誤解并放逐時毅然地面對質疑,同時理性平和面對,幫助軍隊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這一點充分地展現了男性陽剛氣質的一面。最終,花木蘭不但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而且依靠自身的“忠”、“勇”、“真”挑戰(zhàn)和戰(zhàn)勝了社會偏見。木蘭體現了男性陽剛氣質和女性陰柔氣質的完美結合,她的氣也轉變成了浩然之氣。
電影《花木蘭》彰顯了氣在中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意義:花木蘭通過獲得代表著勇敢、果斷的男性氣概,同戰(zhàn)友一起營救出皇帝,挽救了國家;同時,木蘭充分利用自身的堅韌、善良的女性氣質贏得了家人的理解和社會的尊重。因此,影片中的氣作為重要的文化象征,集中體現了中西方之間的思想碰撞與交流。
在古今中外的傳說、詩詞和中西方的影視作品中,花木蘭作為女英雄的生動形象被不斷賦予新的內容,得到新的闡釋。在那個戰(zhàn)亂紛飛的時代,花木蘭挺身而出,替父從軍,克服重重困難,在戰(zhàn)場上和男子一樣通過自身的本領和才智保家衛(wèi)國,為后世樹立了女性英雄典范。這些故事情節(jié)被詩人、作家、導演等藝術家們帶有創(chuàng)造性的重寫和改寫,也在一代代讀者和觀眾之間進行不斷地體驗和交流。它們不但豐富了對于花木蘭藝術形象的文化理解,也增添了說不盡的藝術魅力。
從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出發(fā),中西方的讀者和研究者不難發(fā)現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成功地融合了善良、包容的陰柔氣質和果敢、自信的陽剛氣質。盡管面對著種種社會阻礙和陳規(guī)偏見,木蘭仍然通過堅韌不懈的努力,從處于被動弱勢地位和受保護的傳統女性成長為敢于挑戰(zhàn)社會偏見、直面自我的女英雄。美國電影公司拍攝的《花木蘭》不僅僅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也著眼于傳遞著西方文化要素,主張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和融合,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巫漢詳:《文藝符號新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
[2][荷]霍夫斯泰德等:《文化與組織:心理軟件的力量(第二版)》,李原,孫健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3]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與跨文化研究,《社會科學》2009年第12期。
[4]翟石磊,李川:身份認知與文化維度——中美文化背景下的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對比研究,《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5]段李敏:機構話語中的沉默言語行為與身份建構,《跨語言文化研究》2020年第12期。
(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