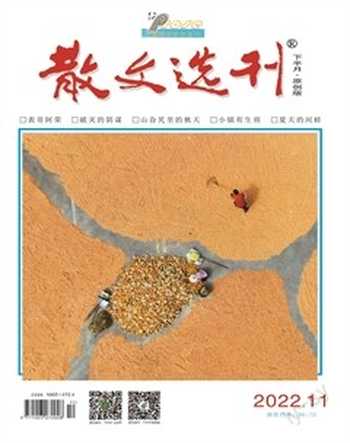表哥阿榮
馮瑤

一
去年五一小長假,我去了一趟深圳,行程之一是去探望住在寶安區的表哥。出發之前,我與他預約了到他家的時間。
他說:“好吧,你想來就來吧。”剛滿七十歲的表哥語氣平淡,有老年人那種看透世事的淡漠。
距離上次去表哥家約十年了。在這十年時間里,從親友們的口中斷斷續續聽到一些關于表哥的消息。其中有一則消息頗具顛覆性——正派誠實如他,竟是家外有家。據說那女的是說普通話的外省人,生得知性溫柔,還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現年已 25 歲了,比表哥表嫂唯一的兒子小 7 歲。二十多年來,表哥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掩蓋這個秘密,又是如何巧妙地周旋在兩個家庭之間的,令人困惑。畢竟,作為原配夫人的表嫂,可不是一只軟柿子。表嫂生得五大三粗,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男人喜歡娶作老婆的優秀勞動力。她精明、強勢、敏感,表哥能在她的眼皮底下藏著另一個家,且讓她二十多年都未生疑竇,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其實,熟悉表哥的人都知道,他作為一名丈夫的日常,可以說是無懈可擊:他基本生活在表嫂的視線范圍內,是廣東人對好老公戲稱的“二十四孝”丈夫,是孩子們心目中正派本分的父親。家里家外,表哥表嫂一直美滋滋地享受著“恩愛夫妻”的稱譽。那么,表哥究竟是什么時間去會情人的?據說,二十多年來,表哥有一個“好習慣”,那就是每天早上五點多,他就起床,穿上運動鞋、服,精神抖擻地出門跑步……誰會想到,一個男人一大早穿著運動服出去是一個秘密呢,真是別出心裁!那個小家,就安在與他家相鄰的南街小區里。
車很快在表哥家門前停下來了,現代化的導航效果精準得令人安心。表哥家是一幢小洋樓,坐落在一個較安靜的街區里。這個街區建于上世紀 80 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基本上由早期來深創業的外來人士在這里自建的樓房組成。這個街區統一規劃,120 平方米的占地面積,限高五層。表哥的房子還多建了一個小小的地下室,用來存放雜物。
我來表哥家,連本次共有四次。
第一次是1992年他這幢房子入伙的時候,表哥邀請我們全家來飲喜酒。那時,我參觀完表哥這幢豪華氣派、富麗堂皇的洋樓時,簡直驚為天堂!整幢洋樓的裝修和里面擺設的家私家電,可用“金碧輝煌”來形容!父親說,表哥家的超大金魚缸里所養的幾尾金龍魚、銀龍魚,都夠我們鄉下人建一座房子了。看來,表哥真是發大財了!那時是深秋,表哥西裝革履,意氣風發,曾經高瘦的身型此時顯得不胖不瘦,豪邁自信與躊躇滿志的氣質,讓我感受到他與我們遙遠的距離!我知道,他已徹底跳出農門,搖身變成了成功人士,變成了人上人。但他對我們這些來自鄉下的親戚還是客客氣氣的,不過,這客氣中,好像隱藏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疏離感。他稱呼我父親為二舅,聽起來彬彬有禮,但好像少了過往的親切和謙和……這些似是而非的感受,讓我覺得表哥變得有點陌生。
入伙酒擺在高檔酒店里,據說一共擺了五十席,鮑參翅肚、金豬龍蝦,非常豐盛,稱得上是豪宴。從來賓們的面部表情,我能讀出他們對表哥的敬意和仰慕。表哥在四星級酒店給我們訂房住宿,他還親自給我們規劃觀光景點,比如世界之窗、民族村、國貿大廈等,然后他派專車、專人帶我們逐一觀光。他風趣地提醒我們說:“現在國貿大廈是深圳的地標性建筑,不到國貿,不算來過深圳!”他對深圳的高速發展津津樂道,他說深圳這里藏著金山銀山,是創業賺錢的天堂,再給他十年時間,他一定會讓財富翻幾番。
我們回家時,表哥給每個人發紅包,回程的車票,也是他給我們準備好的。
表哥原是我們大山里窮得叮當響的農民,他出生于上世紀 50 年代初,父親早亡,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兒,下有四個妹妹。長兄如父,小小年紀的他,便帶領妹妹們開荒墾地,讀完高二,他不得不輟學回家當勞力。三十歲之前,為了溫飽,他當過農民,當過民辦小學教師,兼職做過電力工程安裝工作,還當過小販,與村人合伙販賣木材……上世紀 80 年代初,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以“遍地黃金”的傳說,吸引了不少年輕人。表哥也來到深圳打工,在兼職電力工程安裝工作時,掌握了相關的技術,就是靠這項技術,他在寶安站穩了腳跟,于 1988 年創立了電力安裝工程隊,專門承接路燈安裝、變壓器安裝等工程。經過小十年的奮斗,表哥終于從一貧如洗變成了有錢人。
成了有錢人的表哥,做事很講究效率,連走路都火燒火燎的,好像趕去救火似的。他說:“在深圳,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里到處有寶藏,但只有走得快的人才會得到更多……”
二
第三次去表哥家,是 2012 年暑假,83歲的大姑病危,父親帶上我到表哥家見大姑最后一面。這時我與表哥已闊別 12 年了。這次見到的表哥,他蒼老而消瘦,而且很憔悴疲累的樣子。
父親見到他這個模樣,十分驚訝。他憐惜地說:“阿榮,這次見到你瘦了好多啊,要注意身體呀,錢是賺不完的……”
表哥說:“二舅啊,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嫌錢多的,不是有句老話‘人為錢死,鳥為食亡嗎?”
表哥最小的妹妹嫁給深圳本地人,家里有公司、工廠,還有征地分的錢,很富裕。她偷偷地對我們說:“我哥這個人,對賺錢有一種病態的偏執,本來可以日進斗金,可他還是嫌賺錢的速度太慢,就因這一點,他被生意場上的幾個損友設局,誘他到澳門賭博,幾天幾夜后,他把家里所有的財產都輸光了,還欠下了一屁股債,幸得我老公為他擔保,才算保住了他最初創業時開的那家小公司和這幢房子,要不,他與家人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最近十年,他都在還賭債,現在債未還完,而他已年過六十了,想東山再起,難啊!您說他心里能不焦慮、不煎熬嗎?這樣的人,能長肉嗎?”
我們知道這些消息,心情很沉重,加上大姑病危,心情就更加糟糕。父親總是長吁短嘆的。表哥以為我們不知他近年的生活狀況,只因大姑的病危而傷心。他便小聲地勸我們說:“我媽已是 83 歲高齡了,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你們不必過于悲傷啊,各人過好自己的日子,就是對她老人家最大的告慰了……”
這次,表哥還像上兩次那樣,派車派人帶我們四處逛逛,還特意要安排我們去見識一下深圳新地標——“京基 100”。幾番推辭之后,我們也只好客隨主便,恭敬不如從命了。
聳入云霄的“京基100”,高441.8米,令人震撼!它的周邊,還有許多矗立起來的其他高樓大廈和先進的城市配套設施,以及精致美麗的城市園林景觀等。深圳這座城,確如表哥所稱道的那樣,正不斷向世人展示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速度和高度!在這些偉大的建筑面前,我恍若夢中。它們爭先恐后地出現,是否會讓這里的人們有一種恐為人后的緊迫感和焦慮感?
我們回家時,表哥還像上兩次一樣,給我們買車票,給每人一個大紅包。途中,父親拆開紅包,把里面的兩千元數了又數,然后小聲地對我說:“這次的紅包比上次的,還多了五百元。唉,這個阿榮,就是要面子,他現在背著一身債,卻還要行這些禮數,難為他嘍……”
父親接著說:“阿榮是我看著長大的,他品行好,吃得苦,人又勤,就是賭博害了他!唉,人無完人,優點太多,上天總會搭配些缺點給他的。”
父親在我大姑去世兩年后,也追隨她而去了。我表哥包養情婦一事,他完全不知情。
三
其實,表哥家外有家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相當嚴謹。可,還是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民諺。
五年前,表哥終于把賭債還清時,他已是六十五歲的老年人了。他決定把這個小公司交給兒子來接班。家族生意,沒費多少周折,兒子就順利接班了。也許是年紀大記性差,表哥百密一疏,有一筆三萬多元的租金開支在公司財會報表中有跡可循,他兒子順藤摸瓜,便知道了這件事。
這個天大的秘密揭曉時,無異于在家里引爆了一枚炸彈。一向強勢的表嫂異常震驚暴怒,兒女們也對這個欺騙他們長達二十多年的父親充滿怨恨,當面說他“為老不尊”。加上表哥十多年前那次到澳門豪賭輸掉的巨額財產,讓他們長期生活在債務的陰影下,家人們對表哥的不滿與怨恨早就積聚于心,現在因了這一事件,他們終于有了發泄的出口。為此,他們經常對表哥冷嘲熱諷,用最難聽的語言羞辱他、折磨他。家里因此雞飛狗跳,一個好端端的家,從此分崩離析。三年前,在妻子兒女的強烈要求下,表哥把家里唯一的一幢房產分割了,表嫂一層,表哥一層,兒子一層,兩個女兒各一層。首層放車和堆雜物。分割房產時,就是分家日。
兒子接管小公司后,由于經營不善,只維持了三年,便關門大吉了。自此,表哥創下的基業,終究未能守住。而相好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情人,也因表哥不再有經濟能力而與他各奔東西。眾叛親離的表哥,獨居在二樓的三房兩廳里。近年來,深圳房價不斷飆升,房租也看好。表哥為了賺取房租來補貼生活,他自己蝸居一室,把另兩個房間租出去,每月有五千元收入……
表哥的這些生活狀況,都是我從親戚處聽來的。
四
當我來到表哥家的大門口時,但見大門緊閉,敲門無人應答。我連忙給表哥打電話,卻是“暫時無法接通”的回話。
我繞到表哥家的側門,發現這個小門虛掩著,我推開小門,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步行梯,光線昏暗。這應是后來加建的樓梯。我走向樓梯,感應燈亮了,月白色的燈光,有一種涼颼颼的感覺,讓人仿佛滑進了一個夢境。我走到二樓輕輕敲了一下門。一會兒,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年輕女子,長頭發,戴口罩,有一雙美麗和善的大眼睛,青春而性感!她問我找誰。
我說:“找這房子的主人。”
她的眼睛彎成了笑意:“您是找我們的包租公吧?他不住這里,他住在地下室呢。”
住地下室?我很意外!
“地下室怎么走?”我問。
“你要退出小門,從大門進入才可以去到地下室。”
“可我敲不開大門啊?我打他手機又說無信號。”
“地下室信號很弱。要不,我幫你打他家的座機吧,你稍等。”
打完電話,女子出來對我說:“我通知林伯了,你去大門口等他吧。”
我匆匆返回大門口,只見一個滿頭銀發的高瘦老頭已站在大門口東張西望了。
我連忙扯下口罩,好讓他認出我來。
一看到我,他便說:“你瞧我這記性,我把你來找我這件事忘得一干二凈了。”
看到他,我竟不由淚目。十年不見,表哥已完全變了一個樣。他蒼老、孱弱,過去高瘦挺拔的個子,此時不但變得彎曲矮小,好像還小了一個碼。他的臉,溝壑縱橫,不過精神狀態還好,有一種淡泊通透的氣質。
我向他擠出一臉笑,興奮地說:“榮哥,好久不見,您好啊!”
他審視了我一下,笑著說:“胖了,胖了,比上次見到你時,起碼胖了 10 斤,氣色也好了。看來,你老公很會養老婆嘛!”
他聲音不大,有點中氣不足的感覺。
薄薄的嘴唇像蟬翼一樣抖動!
我笑了笑,夸張地說:“我現在吃水都會長胖。榮哥,您這個瀟灑身型幾十年不變,不過,現在好像更瀟灑了!”
表哥沒有接我的話,他說:“走吧,到我家坐坐。”
他引我進屋,并關好大門,帶我走向地下室。地下室的小樓梯從腳下的小燈泡取光,小燈泡裝在階梯兩邊,有玻璃覆蓋。三十年前,這算得上很時尚高檔的裝修了,而此時踩在腳下,只感覺這些小燈泡滄桑而寒磣。
未到地下室,先聞到地下室的味道,有一股霉味混合著風油精、煤氣、廚衛的氣味躥入鼻中,刺激著我的鼻腔,酸酸的,想打噴嚏,卻打不出來。
表哥對我的反應沒在意。他說:“地下室采光通風不算好,不過,我習慣了,你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說著,我們已來到地下室了。地下室裝有兩盞壁燈,橘黃色的燈光,讓整個空間顯露無遺。但見約四十平方米的空間里,收拾得很整潔。左邊有洗涮裝置和餐廚用品,比如小冰箱、氣爐、小飯桌和兩張小膠椅等,角落處還建有一個洗手間。右邊是休息區,靠墻放有一張約兩米寬的床,裝有一臺掛壁空調,空調下面是一個簡易布衣柜。布衣柜的側邊是一張布藝太妃椅,太妃椅靠背上搭著一件軍綠色的薄外套。太妃椅旁邊的茶幾上,疊放著幾本書,把這個小空間點綴出一點文氣來。
表哥從小飯桌旁挪出一張小椅子,讓我坐。
我把手上提著的禮品放在小飯桌上,說:“給您帶了豆豉、臘鴨腳包和炒米餅等陽江特產,家鄉的味道哦,我知道您喜歡吃。”
表哥歡喜地說:“有心啦,還記得我喜歡吃這些家鄉風味。”
“一直都記著呢,每次來深圳給你們帶的,都是這幾樣。”
“是啊,二舅在世時,每次來都是大袋小袋的,想起這些,特別懷念從前,有阿舅牽掛很暖心,有阿媽嘮叨很幸福,可惜他們都不在了。我也會很快去跟他們團聚的。”
“我呸!榮哥,您盡說這些不吉利的話,您身體好著呢,還可以吃到一百二十歲!”
“你這妹仔,還這么迷信,怎么不吉利啦,人終有一死,每個人都是向死而生。”
“榮哥,您現在講話文縐縐的,有點像哲學家。”
表哥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一笑,笑成了一個大核桃,他稍微得意地朝太妃椅旁邊放書的茶幾揚了揚下巴說:“呵呵,我近年來,確實購了一些哲學書籍在研讀呢。”
我低下頭稍微沉默了一會兒之后,便抬頭看著他:“您為什么住地下室呢?您原來不是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嗎?”
“是的,我那套房子在二樓,總共三室,我住一室,另兩室出租,前年月租還是五千元,去年底升到六千了,整套出租,可租到一萬元。所以,我住地下室,每個月就可多賺四千,四千啊,去哪里賺?”
“可這里畢竟是地下室,環境跟二樓差遠了,您又何苦?”
“安靜。我一個老頭子,將就一下多賺點錢,很合算。”
我很想問他,經濟上是不是遇到困難。可是說出來的卻是:“也是,也是,現在深圳的房價一路飆升,把房租也帶高了,您這樣做也是人之常情,可榮嫂和子女們都同意您住地下室嗎?”
“你榮嫂來勸說過幾次,她讓我跟她回去與家人一起住,就算不與他們住,也得住二樓。那四千元她承諾每月補給我。好歹夫妻一場,她見我現在如此‘折墮(凄慘),有點看不過眼。其實,最重要的是,她知道我與南街那個女人斷了,對我才恢復了一點好感。你還不知道吧?你榮嫂炒股賺了不少,她已另置豪宅與兒子一家居住。”
“我覺得您應聽她勸,與親人們住在一起,大家有個照應啊。”
表哥平靜地說:“情理上應該是這樣,可真正這樣做,大家都難堪,那又何苦?”
我明白,表哥說的難堪,是因他包養情人的事曝光后,妻子兒女與他斷絕關系。但是,我只能裝作不知道這些。
表哥不再說話,他默默地平視前方,好像前方有一個顯示屏,正把他過去的思想清晰地呈現。
這時,我腦際間不禁浮現出三十多年前,表哥這幢豪宅進伙時,他西裝革履,意氣風發,自信豪邁,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人生有兩出悲劇:一是萬念俱灰,另一是躊躇滿志。”我覺得,蕭伯納這句名言,用在我表哥的身上,或許是合適的。
我知道,深圳又有了新的地標建筑——平安國際金融中心,它的高度達 599.1米。可一直到我告辭時,表哥都沒有像往常那樣興奮地向我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