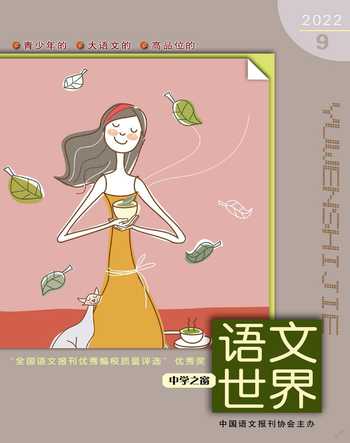茉莉花開(kāi) 光影流年
王躍波
七月,校園里的草茉莉開(kāi)了。紫的黃的白的、半黃半紫雙色的,抑或?qū)訉訒炄居腥鐬⒔鹂楀\的,各色花朵在柔嫩的綠葉間搖曳生姿,天真純?nèi)弧@w細(xì)的花蕊微微顫動(dòng),引得蝴蝶逗留。微風(fēng)里送來(lái)淡淡的香氣,和著蟬鳴,總有一種歲月安然的美好。
鄉(xiāng)下,這種草茉莉極常見(jiàn),房前屋后,撒下一把種子,不去侍弄,靠天將養(yǎng),時(shí)節(jié)到了,自有一片蔥蘢繁盛。然而每每見(jiàn)到,總覺(jué)心弦撥動(dòng),那些沉淀于心底的記憶一觸即發(fā),遠(yuǎn)去的學(xué)生時(shí)代在恬淡花香中漸次顯影,鋪陳開(kāi)來(lái)。
一
初見(jiàn)草茉莉是在村里小學(xué)的院子里。小小的花壇,各色的茉莉花熱熱鬧鬧地開(kāi)著。傍晚放學(xué)時(shí),似乎香氣更濃。上了一天課,最后一節(jié)課總是自由活動(dòng)。我們?nèi)鍌€(gè)小女孩就去采花,挑那些大的美的,扎在辮子上,別在耳朵后,插在衣襟扣眼里,或者用狗尾草穿成手串、項(xiàng)鏈戴在身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嘰嘰喳喳說(shuō)著,笑著。(大女孩們?cè)谂赃吿そ罨蛘咦プ觾海⒉粎⑴c這種幼稚的游戲。)老師從來(lái)不說(shuō)我們,只是看著我們笑,滿(mǎn)是寬容與慈愛(ài)。我們也是有分寸的,只是偶爾摘來(lái)玩,并不故意糟蹋,那花啊開(kāi)得太好了,看不夠呢!
我們這個(gè)小學(xué)校只有一間教室,一位老師。全村三十多個(gè)孩子,從育紅班到三年級(jí),小到五六歲,大到十三四歲(那時(shí)候可以留級(jí),家長(zhǎng)要是覺(jué)得孩子念得不好,就讓孩子留級(jí),留個(gè)兩三年也是常事),都在這里念書(shū)。老師姓劉,嫁在鄰村,不過(guò)二三里路,天天騎自行車(chē)來(lái)回,從不遲到早退,也從未請(qǐng)過(guò)假。當(dāng)時(shí)不覺(jué)得有什么,現(xiàn)在想起來(lái)殊為驚異,我也是做了二十多年的老師,不知當(dāng)時(shí)瘦瘦弱弱的劉老師是如何做到風(fēng)雨無(wú)阻從不缺課的。
一個(gè)人就是一所學(xué)校,是真的啊。
既然只有一個(gè)人,那所有的課也就只有劉老師一個(gè)人教。好在只有兩門(mén):語(yǔ)文和算術(shù)。四個(gè)不同年級(jí)的孩子在同一個(gè)教室上課。老師自有她的調(diào)度,給育紅班的孩子講故事,就叫另三個(gè)年級(jí)的孩子寫(xiě)作業(yè),如此循環(huán)。那時(shí)候作業(yè)很少,基本就在學(xué)校寫(xiě)完了。學(xué)的知識(shí)也簡(jiǎn)單,我作業(yè)寫(xiě)得快,老師給高年級(jí)孩子講課時(shí),我也常常支棱著耳朵聽(tīng),等輪到給我們講時(shí),好多知識(shí)已經(jīng)學(xué)會(huì)了。從那時(shí)起,我的成績(jī)就名列前茅。不過(guò)實(shí)在不值得驕傲,因?yàn)槲疫@個(gè)年級(jí)一共就四個(gè)人呀!我、我的雙胞胎妹妹,另外兩個(gè)是一對(duì)堂兄弟。
最高興的莫過(guò)于過(guò)“六一”。臨到“六一”,各村小要準(zhǔn)備節(jié)目,到中心校去演。每到這時(shí),劉老師就擔(dān)起音樂(lè)老師的職責(zé)。教室里有一架腳踏鋼琴,劉老師一邊彈琴,一邊教我們唱歌。《沒(méi)有共產(chǎn)黨就沒(méi)有新中國(guó)》《八月桂花遍地開(kāi)》《讓我們蕩起雙槳》……劉老師一句一句地教,我們一句一句地學(xué)。一板一眼的琴聲,荒腔走板的歌聲,某個(gè)孩子的輕笑聲,老師“再來(lái)一遍”的指令聲,充滿(mǎn)了整個(gè)教室。明明只是學(xué)一支歌曲,可是從老師到學(xué)生都是如此認(rèn)真莊重,仿佛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當(dāng)所有人都能跟上老師的琴聲,整齊的歌聲緩緩流出的時(shí)候,大家是多么高興啊,單純地發(fā)自?xún)?nèi)心的快樂(lè)!當(dāng)然,去中心校肯定不是表演大合唱,可就是借著“六一”這個(gè)時(shí)機(jī),我們學(xué)會(huì)了很多歌,獲得了最初的音樂(lè)啟蒙。
劉老師是代課老師,一直在我們村小教書(shū),教了很多年,后來(lái)趕上政策,轉(zhuǎn)正了,算起來(lái)應(yīng)是早已退休了。工作后,我常常想,如果給我這樣一群孩子,給我這樣一個(gè)教室,我能擔(dān)起這份重任嗎?那樣的年代,那樣的老師太多太多了,作為鄉(xiāng)村教育的中堅(jiān)力量、基礎(chǔ)教育的神經(jīng)末梢,他們付出了整個(gè)青春,默默無(wú)聞,但功德無(wú)量。
二
四年級(jí)起,我和妹妹就去外村讀書(shū)了。三年后,我如愿考上重點(diǎn)初中,妹妹則因幾分之差落榜,執(zhí)意去復(fù)讀。自此,上學(xué)路上便只有我一個(gè)人的身影。
進(jìn)入初中,我開(kāi)始住校。宿舍是一間大房子,兩條大通鋪,沒(méi)糊頂棚,抬頭就能看見(jiàn)檁柁。每個(gè)人只有一個(gè)枕頭寬的地方,枕頭碰枕頭,褥子是對(duì)折鋪的,不然鋪不下,一張通鋪擠十幾個(gè)人,根本翻不了身。沒(méi)有電扇,沒(méi)有暖氣,夏天悶熱,冬天寒冷。整個(gè)女生宿舍區(qū),只有一個(gè)旱廁,連燈都沒(méi)有。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家長(zhǎng)擠破腦袋也要把孩子送到這里來(lái),因?yàn)檫@是一所老牌重點(diǎn)中學(xué),師資好,管理嚴(yán),升學(xué)有保障。
每天雷打不動(dòng),學(xué)生五點(diǎn)半起床,六點(diǎn)進(jìn)教室,一天的課滿(mǎn)滿(mǎn)當(dāng)當(dāng),第八節(jié)課照例是體育活動(dòng),要么操場(chǎng)訓(xùn)練,要么越野跑,訓(xùn)練度滿(mǎn)格,直到晚上九點(diǎn)下自習(xí),一天結(jié)束。一年四季,天天如是。那時(shí),一周上六天課,周六下午放假,周日下午返校,不能耽誤上晚自習(xí)。到了初三,一個(gè)月便只休一天。我家離學(xué)校二十多里路,一般下午四點(diǎn)鐘就要騎自行車(chē)從家出發(fā),冬天則要更早,不然天就黑了。回學(xué)校要收拾東西,交作業(yè),換飯票,稍一磨蹭就趕不上趟兒。
趙天增老師是我初二時(sh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數(shù)學(xué)老師。他那時(shí)不過(guò)四十多歲,只是天生頭發(fā)少,頭頂锃亮,僅其余三面有些頭發(fā),拱衛(wèi)中央,保持著最后的倔強(qiáng),屬實(shí)是“聰明絕頂”。他個(gè)子很高,瘦,長(zhǎng)臉,小眼睛,眉毛很淡。不笑時(shí),一臉嚴(yán)肅,讓人摸不著頭腦;笑起來(lái)和藹可親,嘴角上揚(yáng),眼睛里都蓄滿(mǎn)笑意。
他“御下”極嚴(yán),做事極有條理,也頗有分寸。總之,我們大家都挺喜歡他,背地里叫他“趙老頭”,雖然他并不老。他大概也知道,但不以為忤,他看我們真像看自己孩子一樣。他數(shù)學(xué)講得極好,總是三言?xún)烧Z(yǔ)點(diǎn)出要害,又常常語(yǔ)出幽默,讓人印象深刻。比如數(shù)軸,他說(shuō):“數(shù)軸就是孫悟空手里的金箍棒,想要有多長(zhǎng)就有多長(zhǎng),可以向兩端無(wú)限延伸,需要時(shí)能一下子捅到天宮,不需要時(shí)變成一根火柴棍藏到耳朵眼兒里。它還是它。”比如合并同類(lèi)項(xiàng),他問(wèn)我們:“仨貓加倆狗等于多少啊?”我們笑著說(shuō):“老師,這沒(méi)法加啊,不是一個(gè)東西。”他說(shuō):“對(duì)——嘍,貓加狗不能加,x加y也不能加,加到這就到頭了。”“哦——”我們中有人恍然大悟。至于徒手畫(huà)圓,秒算得數(shù)更是不在話(huà)下。我至今仍記得他背著一只手,面朝我們反手畫(huà)圓的神氣,一個(gè),又一個(gè),都是標(biāo)準(zhǔn)圓。看著我們一個(gè)個(gè)大眼瞪小眼、不可置信的神情,他笑得很灑脫,說(shuō)著:“這有什么啊,瞧——”反手又是一個(gè)圓。服了!
在他的影響下,我第一次對(duì)數(shù)學(xué)如此著迷,第一次覺(jué)得數(shù)學(xué)是那么神奇那么美。更重要的是,他讓我知道,女生也可以學(xué)好數(shù)學(xué),不遜于男生。因?yàn)樗麖膩?lái)不會(huì)說(shuō)“到了初高中,女生學(xué)數(shù)學(xué)就后勁不足”那樣叫人泄氣的話(huà),他說(shuō)只要好好學(xué),每個(gè)人都能掌握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的密碼。一個(gè)班60多人,期末考試數(shù)學(xué)平均分108,是不是無(wú)敵了?這就是無(wú)敵啊!
很多年以后,我還是會(huì)常常想起他。想起他明明相貌平平,一站到講臺(tái)上就神采奕奕,整個(gè)人仿佛會(huì)發(fā)光的樣子;想起他把我們這支“隊(duì)伍”拉到操場(chǎng)上,舞動(dòng)著雙手做指揮,指導(dǎo)我們分雙聲部唱《打靶歸來(lái)》的樣子;想起他拿著小木棍,迎著北風(fēng),帶著我們一絲不茍?zhí)哒健⒕氷?duì)列的樣子;想起他在拔河比賽上,站在我們身邊,用力揮動(dòng)雙臂大聲呼喊給我們加油助威的樣子……他把整顆心都給了我們啊。有他在,我們是那么踏實(shí),那么有依靠。
三
1997年初中畢業(yè),我以?xún)?yōu)異的成績(jī)考上了中師——廊坊師范學(xué)校(即現(xiàn)在的廊坊師范學(xué)院),一扇嶄新的大門(mén)朝我慢慢打開(kāi)。我第一次從家鄉(xiāng)三河的一個(gè)小鎮(zhèn)走進(jìn)一個(gè)繁華的城市,也第一次面對(duì)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
說(shuō)來(lái)慚愧,我真正讀書(shū)其實(shí)是從這個(gè)時(shí)候開(kāi)始的。家里世代務(wù)農(nóng),一個(gè)讀書(shū)人也沒(méi)有,小學(xué)階段我?guī)缀鯖](méi)讀過(guò)課外書(shū)。中學(xué)幾乎是全封閉學(xué)習(xí),假期倒是有時(shí)間,可是依然沒(méi)書(shū)讀。買(mǎi),當(dāng)時(shí)沒(méi)那個(gè)意識(shí),也沒(méi)那個(gè)條件。借,無(wú)從可借。中師的學(xué)習(xí)沒(méi)那么緊張,課余時(shí)間很多。干什么,讀書(shū)吧。學(xué)校寬闊明亮的圖書(shū)館,于我而言,就是一座寶庫(kù),我第一次有了當(dāng)家做主的感覺(jué)。
我跟著基督山伯爵層層布局快意恩仇,酣暢淋漓;我目睹茶花女淪落風(fēng)塵命運(yùn)多舛,黯然落淚;我看到歷經(jīng)磨難的冉·阿讓依然仁慈善良,照護(hù)他人,生出對(duì)抗苦難的勇氣 ;我感嘆出身貧苦的簡(jiǎn)·愛(ài)敢于蔑視權(quán)貴,自尊自強(qiáng),悟到精神強(qiáng)大的可貴。
我讀到余光中,“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gè)盛唐”,立覺(jué)余音裊裊,繞梁三日;我讀到席慕蓉,“陽(yáng)光下慎重地開(kāi)滿(mǎn)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瞬間淪陷于那佛前女子的深情,千回百轉(zhuǎn),柔腸百結(jié);我讀到舒婷,“我如果愛(ài)你——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sh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頓悟這樣堅(jiān)強(qiáng)柔韌的女子,才是吾輩典范。
就這樣一路讀下去,讀林語(yǔ)堂,讀余秋雨,讀汪曾祺,讀史鐵生……囫圇吞棗,生吞活剝。那時(shí),我常常在圖書(shū)館二樓臨窗而坐,初夏溫柔的陽(yáng)光照進(jìn)來(lái),高大的法桐枝葉茂盛,清風(fēng)吹過(guò),窸窣作響。
毛筆字也是從那時(shí)練起。這得益于學(xué)校開(kāi)的書(shū)法課。書(shū)法老師叫李健,四十來(lái)歲,中等身材,微微發(fā)福,濃眉大眼,眼角略下垂,有一股慈眉善目的味道,說(shuō)話(huà)不疾不徐,四平八穩(wěn),常常一副老干部打扮。上課時(shí),他總是拿一個(gè)暖壺蓋,里面裝半下清水,一支大毛筆,一布袋子書(shū)。
李老師教的柳體。柳體瘦硬,結(jié)體嚴(yán)緊。我常常想,若論“字如其人”,他教顏體定然也是極好的。最喜歡看他寫(xiě)字。他拿毛筆蘸了水,從橫豎撇捺、鉤折挑點(diǎn)開(kāi)始,在黑板上給大家一一示范。他一面運(yùn)筆,一面講解:“看,長(zhǎng)橫,逆鋒向左,輕起筆,起;折筆向下輕頓,頓;折向右中鋒行筆,行,手要穩(wěn)住;到末端微向上提筆,提;折向右下頓筆,頓;回鋒收筆,收。好,我們?cè)賮?lái)一遍……”一節(jié)課下來(lái),我們就在他的“起頓行提頓收”的延長(zhǎng)音中度過(guò)。
臨完點(diǎn)畫(huà),臨部首,再臨字,循序漸進(jìn)。我雖學(xué)得認(rèn)真,但初入門(mén)不免把字寫(xiě)得東倒西歪,向老師求教,老師說(shuō):“嗯,這個(gè)字寫(xiě)得不錯(cuò),練多了就好了。你練得多?你這才練幾天?人家寫(xiě)一輩子了。不能心急。”老師說(shuō)話(huà)一貫是慢悠悠的,你問(wèn)一句,他答一句,串起來(lái)才是一篇話(huà)。我暗想,不愧是學(xué)書(shū)法的,養(yǎng)氣的功夫的確一流。
學(xué)了大半年,早也寫(xiě),晚也寫(xiě),到考試那天更是連午休都棄了,一心一意臨帖,寫(xiě)到手酸。考試當(dāng)場(chǎng)寫(xiě),當(dāng)場(chǎng)出成績(jī)。老師站在講臺(tái)上,被我們團(tuán)團(tuán)圍住。拿回我的字,擠出人群,看著老師在宣紙上用朱筆畫(huà)的紅圈,我心里不知有多高興。同學(xué)們也是,大家紛紛數(shù)自己得了幾個(gè)紅圈,紅圈倒比分?jǐn)?shù)更讓人在意。那是真的好,才給畫(huà)圈的。自然,如果是方框,那就要注意了,說(shuō)明這個(gè)字筆法或者結(jié)構(gòu)肯定有問(wèn)題。
記得一次課上,我正在寫(xiě)字,老師踱到我這里,指著那個(gè)“慕”字,徐徐地說(shuō):“這個(gè)字寫(xiě)得真好,比我寫(xiě)得都好,你看這一捺,筆意到了。”我都傻了,真的那么好嗎,盯著那個(gè)“慕”字,看了又看。老師一臉真誠(chéng),不似作偽。說(shuō)完,轉(zhuǎn)身又去指點(diǎn)別人了。無(wú)論如何,這句“比我都好”著實(shí)鼓舞了我,每每想要偷懶之時(shí),記起這句話(huà),便又提起勁頭再寫(xiě)下去。二十多年過(guò)去,那溫和醇厚的聲音似乎猶在耳畔。
茉莉花開(kāi),光影流年。那些遙遠(yuǎn)的青春歲月去而不返,那些上過(guò)的課,經(jīng)過(guò)的事,看過(guò)的書(shū),寫(xiě)過(guò)的字卻都一點(diǎn)一滴融入骨血,長(zhǎng)成性情,鑄就品格。春風(fēng)化雨,潤(rùn)物無(wú)聲。就讓我和我的老師們一樣,好好教書(shū),默默耕耘吧。總有一天,我的花兒也會(huì)開(kāi)滿(mǎn)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