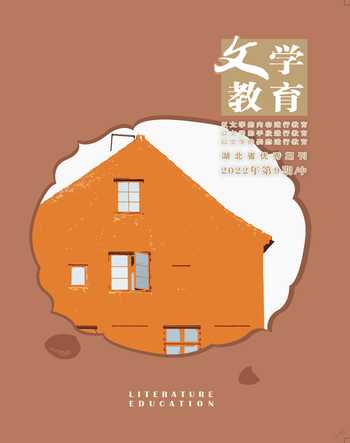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南荒記》:詩意與苦難共存的湘西記憶

近現代以來,作家們紛紛“返回鄉土”,或以文為媒,詩意勾勒描繪地方“風景”,展現鄉土世界豐富的文化表情;或化筆為戟,以映射底層生存狀態與生命意識為己任,深入探討鄉村歷史境遇下的苦難生存現實。作家劉鴻伏于2019年出版的作品《南荒記》,小說故事背景設置在湘西大山深處一個隱匿的村子之中,依據村中的“細伢子”(小孩子)劉務的視角展開,將此兩種主題兼容并包,并以數十年積累的湘西經驗與老道的文筆,創作出一種詩意與苦難兼具的故事風格,帶給讀者新穎的審美體驗。
山水如墨畫,似詩亦似歌。劉鴻伏依照始終留存在心中的湘西記憶,精心描摹《南荒記》的自然風光,將那股沁人心脾的美感氤氳在字句之中。“溪水從石壁上濺落,日光下幻出五彩光暈,騰起的水霧消融于木葉草石間”,這類詞句在書中比比皆是。而且,除山清水秀以外,還有數不勝數的生靈在讀者眼中躍動——小說開篇即“知了的叫聲像一陣雨從樹上落下來”,隨后又有彩色鵝卵石上的魚群和螃蟹,露水上的蝴蝶、蜻蜓和甲蟲,爭食的喜鵲與八哥,還有劉務家養的那條小黑狗……它們作為大山的一部分,使湘西世界呈現生機勃勃的景象。
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生活在這山明水凈的村莊里的人們,具備著勤勞、善良和淳樸的美德。于己或是于人,每個人都遵循著規矩,守護著屬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縷溫情與溫暖。落雪天里,劉嬸娘踩著積雪,送給高燒的劉務一個珍藏了大半年的橘子,而這樣的橘子卻是救命的吃食。三麻子的爹綽號利猴子,為了救劉務的命,選擇破了祖師爺傳下來的禁忌,用了一生只能用三次的強盜水。在名為“鷂子飛過山梁”的一章里,曾經是救星的新化瓦匠以為自己已經被遺忘,但劉務爹卻告訴劉務“他救活過我們一村子的人”,知恩的品質又在此處隱現。此外,如劉務爹經常說的,“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陽世上每個人都有一兜露水草養著,只要勤勞,就不會餓死”,大山里的人們奉行的便是這樣一種生存法則,他們堅忍、耐苦,有著無與倫比的生存能力,以最少的資源養活自己和家人。他們并不信奉“人定勝天”或“天定勝人”,而是與天地和鳴,與山水和諧,融為一體,順應自然規律,在對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樂觀而努力地生活。
除了詩意的山水與人物,《南荒記》還特別聚焦了湘西地域神秘浪漫的“巫文化”。小說中村民的世界觀往往帶有超驗色彩,認為萬物皆有靈性。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念中,村中的祖祖輩輩對客觀世界里的一草一木充滿了敬畏,譬如劉務拜了一塊大石頭做干娘,并獲得了個新名字叫“巖保”。并且,在這種“萬物有靈”的世界觀中,最為常見的是“預兆”觀念。大樟樹上鸮的叫聲,白鷺在巢里發出的不安聲響,劉務弟弟的夢……都傳遞著不可解讀的預兆。
《南荒記》飄口處的文字寫道:“故事人物首尾相連,渾然一體,又相互獨立,你可能感覺在讀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還能感覺在讀《水滸傳》。”除了詩畫般的自然與人情美,劉鴻伏并沒有拘泥于對作品的詩性雕琢,小說中,魔幻現實主義的筆法流淌其間,具有神秘色彩的環境、超現實的荒誕情節,都指向了一個主題,那就是呈現出那個年代湘西人苦難的生存狀態,凸顯無處不在的悲劇,喚起讀者的共鳴。
《南荒記》共十六章,在那些唯美動人的秀麗風光的背后,讀者往往體會到一種濃重的悲涼氣氛綿延其間。那是一個動蕩的年代,國家尚未安定,物質仍舊匱乏,因此小說中最突出的苦難,就是物質的稀缺給人帶來的痛楚。饑荒年代沒有糧食,很多人患上水腫,拖不了三個月就會埋入黃土。村中最流行的食物是紅薯,一年四季都是主食,過年時才有機會吃到白米,平時的紅螃蟹、鳥蛋或者苦鳊屎都是難得的牙祭。當堂伯娘那頭摔死的老黃牛被做成全牛宴后,男女老少一哄而上,像一群野獸一般瘋搶。此外,蝗災過后,人們毫不顧忌,撿拾死掉的蝗蟲為食,光棍毛五和屠夫打賭,生吃十斤豬板油,回去哇的一聲吐出來,用大火來煎,這些情節難以想象,有時甚至令人反胃,但這都是長期挨餓缺乏營養的現實,在小說整體構架中并不顯得突兀。更為重要的是,《南荒記》在對苦難的書寫上,有諸多含有魔幻色彩的情節建構,這種情節突破對一般現實的直接復刻,而是將現實與虛幻交織,呈現出夢幻的特征。例如夜里,村里大部分人開始夢游,光棍毛五啃床腳,滿嘴是血,劉務爹去河里倒毒藥,三麻子爹趕牛去偷吃禾苗,動物們也開始反常起來,幾十只蛇相交,鳥群亂叫,全村的植物開始以千萬倍的速度生長、腐爛,乾坤顛倒,時序錯亂。個中緣由,書中并沒有詳細解釋,只有劉務奶奶解釋是“靈魂出竅”的緣故。身體好、精力好的人的靈魂不會出竅,而白天想得多、夜里夢得多的人才會夢游,再聯想每個人夢游的表現,大致可以推斷出,這場事件背后的原因正是人們對于食物的渴求。魔幻色彩的情節,以夸張的手法將非現實的因素和現實的人物和環境巧妙融合,有一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模糊感,但讀起來更觸目驚心,帶來心靈上的震撼。
比貧窮更抓人肺腑的,是死亡的苦難。小說中涉及死亡的情節很多,但又都不相一致,各有其特點。主人公劉務自己就有過好幾次的死亡經歷,起麻疹、被斧頭劈中、頭倒插到紅薯地里……但每次都是“從閻王殿里打了一個轉回來”,這些死亡經歷,都成為了劉務成長的助推。但對其他人來說,則沒那么幸運,劉王氏早年喪夫,與鐵匠兒子私通被發現,物質生活和情感生活全部崩潰,選擇喝農藥自殺。泥鰍嬸娘褲子被偷,加上不被人理解,在豬樓屋吊死。自殺之外,還有小女孩薇薇被積雪壓死,三麻子爹和穩叔病死,堂伯娘掉下山崖摔死。魔幻情節在這里仍有體現,如劉務奶奶臨終時,爺爺生前栽的梨樹史無前例地結了果,刀生的弟弟薯生前世是刀生父親殺的一個人,可以認出自己前世的家……有的死者知道死法,有點不知道死法,死的方式又互不相同,這些在書中均有展現。死亡越是如此正常,如此普遍,越是隱喻這篇土地的無常性,正如在劉務爹大難不死后的一段文字:由生忽死,死而忽生,死生禍福,旦夕逆轉,命運波詭云譎,全不由人。
小說的封底處有三句評語,其中一句是“一部向生命和自然致敬之書”,除此以外還應說,這是“一部記錄苦難與命運的血淚之書”,則更符合對《南荒記》特色的中肯概括。可以說,劉鴻伏深刻地理解了鄉土小說作家的使命,以靈動的文學運思和鞭辟入里的生命思考將表達詩意和反映苦難都做到了極致,又為湘西文學增添了一抹亮色。
姚樂旗,河南信陽人,湖南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