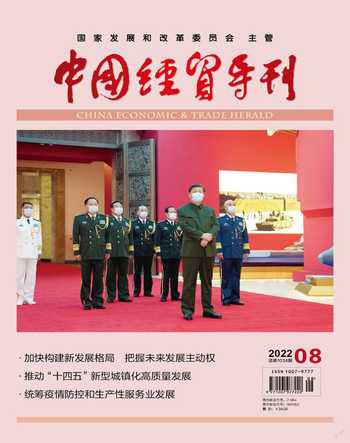越南出口激增對我國挑戰應分行業、人群、區域差別應對
夏成 潘彪 胡月 王繼源
2022年1—4月,越南出口貿易額達到1224.8億美元,同比增長16.5%,而同期我國出口增長10.3%,特別是4月份出口增速下降至3.9%。這一鮮明對比,引發國內對貿易訂單轉移和產業鏈外遷的雙重擔憂,甚至產生越南是否會取代我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討論。從貿易和生產數據來看,近期越南出口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短期利好因素,但更多是源于長期比較優勢動態調整帶來的分工變化。這種轉移對我國貿易總體影響不大,但應重點關注對勞動密集型行業、勞動力就業、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等帶來的挑戰,采取針對性應對措施。
一、“兩長兩短”因素疊加,助推越南出口激增
越南出口上漲并非近期現象,2000—2021年,越南出口額年均增長率達到16%。2010年,越南出口額還不足蘇州的五成、深圳的四成,但在2016年和2019年先后趕超蘇州和深圳,2022年一季度分別達到二者的1.4倍和1.5倍,這源于長期趨勢和短期因素疊加帶來的復合增長效應。
(一)長期因素一:低勞動成本吸引大量國際投資,外資企業構成出口主力
從2007年開始,越南進入人口紅利期。2020年,越南總人口達到9734萬人,規模介于我國河南、江蘇兩省之間,結構優勢明顯,年齡中位數31.9歲,比我國年輕6.8歲;15—34歲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1.2%,比我國高3.7個百分點;制造業勞動力成本每小時2.99美元,約為我國的46%。低勞動成本為越南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資,2022年前4個月,越南吸引FDI逾10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88.3%。外資企業成為越南出口貿易的主力,2010年至2022年前4個月,FDI企業出口額占比從54.2%上升至73.2%。
(二)長期因素二:廣泛參與經貿合作組織,有效增強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優勢
越南作為經濟和貿易小國,加入經貿合作組織的外部阻力小,目前已成為全球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最多的國家之一。2007年加入WTO,2010年作為東盟成員與我國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近年來又先后加入CPTPP,與歐盟、英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22年RCEP生效后,越南被認為是獲益最多的國家。越南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一步提高了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增強對外貿易優勢,對其出口推動作用將越來越突出。
(三)短期因素一:中美經貿摩擦下部分企業從中國遷移至越南,貿易替代效應逐漸顯現
2018年3月以來,中美經貿摩擦總體不斷升級,一部分跨國公司為規避貿易壁壘被迫遷出我國;同時,美國、日本、韓國等一些發達國家推出優惠政策及扶持項目,鼓勵本國企業回流或轉移到第三國家,其中很大一部分產能轉移到了越南。越南對我國出口形成明顯短期替代,如2019年,越南對美出口額同比增長29.1%,我國對美出口額則同比下降12.5%。2018—2021年,越南在美進口來源占比從1.9%上升至3.4%,我國占比從21.2%降至17.8%。
(四)短期因素二:“帶疫解封”加快復工復產進度,獲得大量外貿訂單
2021年10月,越南開始放松國內疫情管控;2022年1月起壓縮疫苗接種者入境隔離期,4月27日起暫停邊境口岸入境人員健康申報,5月15日進一步暫停入境人員核酸檢測要求。率先“帶疫解封”加速了越南制造業復蘇,國際訂單快速反彈。特別是趁我國疫情反復造成供應鏈短期運行不暢,越南承接了大量來自珠三角和長三角外貿轉單,直接推動今年3、4月份出口額同比上漲17.0%和25.2%。
二、“三大三小”挑戰并存,對我國不同行業、人群、區域存在差異影響
從生產和貿易數據來看,越南出口增長集中在少數產品和個別領域,對我國的沖擊并非是全方位的,無論是經濟體量還是生產能力,越南都難以撼動我國“世界工廠”地位,但需要重點關注受影響較大的部分行業、人群和區域。
(一)對勞動密集型行業挑戰大,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挑戰小
目前越南制造業以勞動密集型行業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裝配環節為主,其出口增加對我國的貿易替代作用也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2022年1—4月,越南通信設備及配件、紡織服裝等前5類商品合計占總出口的58.1%,進口結構則與之高度相似(見表1)。這意味著越南制造主要是將原材料、零部件經過加工或組裝后再出口,整體處于全球產業鏈下游,對我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沖擊較小。對美貿易數據也顯示,今年3月份與去年9月份相比,我國在美國紡織服裝、鞋帽、機電產品進口份額中下降10個、6.3個和4.1個百分點,而越南所占份額則上升了3.1個、5.0個和0.8個百分點。
(二)對勞動者挑戰大,對資本所有者挑戰小
訂單轉移和產業鏈遷移并不意味著我國企業被剔除全球產業鏈,只是部分產品組裝環節轉移到了越南,國內企業開始向上游原材料和下游訂單管理擴展,供應鏈網絡規模擴大。越南出口增加對我國組織生產的資本所有者沖擊有限,但對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者挑戰較大。作為越南最大的進口來源國,2022年前4個月,越南自我國進口額達380.8億美元(占比31.7%),其中紡織面料、通訊設備及配件、計算機電子產品配件自我國進口分別占63.2%、42.4%和28.1%。同時,我國紡織服裝、鞋類、木材加工、電子等行業部分企業,為降低成本、規避貿易壁壘跟隨國際巨頭轉移至越南。2011—2021年,我國對越南投資流量從1.9億美元增至10.7億美元,中美經貿摩擦后投資增速明顯上升,2021年,我國已成為越南第四大FDI來源國(占比9.9%),按比例估算去年中資企業為其新創造就業崗位約46萬個。
(三)對中西部地區挑戰大,對東部沿海地區挑戰小
2021年,越南人均GDP約為3700美元,略低于我國西部地區的甘肅、廣西、貴州等省份,在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存在競爭關系。相較而言,中西部成渝、關中平原、北部灣、黔中、滇中等城市群,擁有龐大的生產和消費群體、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成熟的配套市場體系,投資綜合吸引力高于越南。如果部分產業從東部沿海直接轉移到越南等東盟國家的短期現象長期化,將打破國內從東到西梯度轉移部署,對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發展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對于東部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其本身有向外轉移低端制造實現“騰籠換鳥”的需求,將轉移至國外的產業鏈和外貿訂單保持在一定規模和進度,保障重點行業有序轉型升級,則負面影響可控。
三、“三穩三提”多措并舉,主動化解外部沖擊帶來的挑戰
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國外轉移,是符合經濟規律的正常現象,無需過度擔憂。針對當前受影響較大的行業、人群和區域,需打好“三穩三提”政策組合拳,全面化解挑戰。
(一)穩定勞動密集行業和生產環節外遷節奏,提升向“微笑曲線”兩端擴展能力
穩定國內制造業核心環節的關鍵在于破解生產成本高企問題。要用好政府性融資擔保,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基金,降低企業融資難度和成本;加快落實降低企業用水用電用網等成本措施,鼓勵企業采取精益生產、精益管理等理念,重塑生產流程和管理方式,降低綜合成本。擴大市場采購貿易試點范圍,支持通關一體化模式發展。引導各地推廣口岸收費“一站式陽光價格”,提升出口退稅便利化水平,增強出口信用保險政策對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服務力度,對沖經貿摩擦帶來的成本和風險。加強與外資企業溝通,穩定企業預期和信心,為關乎產業鏈穩定性的重點外資企業對華派駐員工提供出入境便利。對研發設計投入達到一定規模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探索按高新技術企業予以稅收優惠。支持各地搭建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型共性技術服務平臺,推出銷售和服務管理系統解決方案,提升企業向研發設計和產品服務管理核心競爭力。
(二)穩定重點群體就業和收入,提升對低技能勞動力教育培訓水平
化解對重點群體就業和收入的影響需要把短期救濟幫扶與長期就業能力提升相結合。要指導各地提高援企穩崗措施的精準性和支持力度,通過保市場主體來保就業和收入。對受短期疫情影響和中長期產業鏈外遷壓力較大的行業,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緩繳企業社會保險費政策覆蓋范圍擴大到受外遷影響較大的行業,提高對吸納勞動力較多企業的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比例和留工補助規模。督促地方盡快將中央下撥的困難群眾救助補助資金發放到位,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追加補助,結合家庭收入情況和資產狀況,允許一定比例的失業群體延期償還貸款。用足用好一次性留工培訓補助、拓寬技能提升補貼、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專賬資金等政策,借助互聯網平臺推動線上線下培訓結合,支持職業院校按規定備案成立職業技能等級評價機構,提高教育培訓覆蓋面,幫助低技能勞動者適應產業轉型和生產技術復雜度提高要求,增強再就業能力。
(三)穩定國內產業轉移梯隊,提升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能力
推動制造業從沿海向內地有序轉移是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增強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關鍵之舉。要加快國內制造業產業轉移梯隊建設,支持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開展制造業企業轉移意向調查,形成潛在轉移企業名錄,建立產業轉出地和承接地信息匹配機制。鼓勵各地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搭建產業轉移承接輔助系統,嵌入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對接園區合作共建,幫助轉移企業落地。落實國家鼓勵產業目錄相關支持政策,加大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企業稅收減免和信貸投放力度,打造重要產業鏈備份基地。加強對中西部地區城市基礎設施補短板強弱項支持力度,依托各類開發區、產業集聚區打造產業轉移承接平臺,推動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鼓勵產業轉出地和承接地結對建立營商環境優化幫扶機制,破解體制機制制約。支持中西部地區城市爭取內外貿一體化試點,以龐大市場需求增強內地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力。
(夏成、潘彪、王繼源,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地所。胡月,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