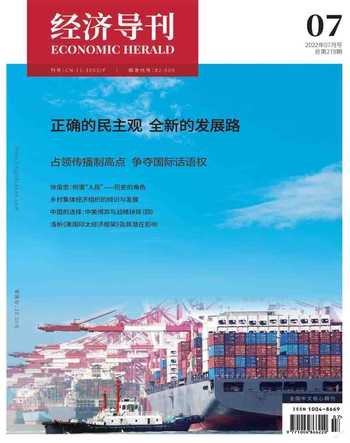新聞傳播學如何回應時代之問
張濤甫

新聞學的時代之問,是在當今世界秩序面臨失控和失衡之時產生的,它是世界之問、中國之問、人民之問。在這個時代當中,究竟有沒有一個整體性的解釋,來概括我們面臨的問題與困惑?而尋找這種整體性的解釋,就是“時代之路”。
重構“時代之路”
在“時代之路”中,盡管現代的傳播技術、數據整合和資訊連接的能力要強于以往,但思考路徑亟需調整,學術理論面臨危機。答案就是我們要“告別學徒期,成為中國”。
何謂“告別學徒期”?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當中,曾經學習西方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然而,在學習西方知識秩序的同時,中國并沒有完備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要找到整體性的解釋,統籌中國的知識和精神兩種秩序。在中國革命時期的探索是“立足中國土,構建整體性”的范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革命斗爭中發揮了救治中國的作用。這給我們以“走出西方,回歸中國”的啟示。
中國新聞傳播學之困
人類社會是語境化的,各種文明的演進方式是“并聯”而非“串聯”,現代化的解釋路徑因存在先驗的文明優劣之分而令人難辨,我們應當回到具體的文明本身。
聚焦于中國語境,我們亟需回答兩個問題:新聞傳播學從何而來?新聞傳播學之困是什么?
作為一種知識體系,新聞傳播學是知識脈絡中晚生的子集,雖然有諸多成熟學科提供知識儲備和資源,但其所擁有的學術權力和知識權力較為低下。不可否認,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借鑒了西方的結構化知識,但缺乏以中國本土的知識傳統為本。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科的“工具箱”因為散裝理論和弱范式變成了知識的“八寶箱”,甚至因為“既有鑰匙又有鎖”而陷入認知失調、知識不分涇渭的焦慮和混沌之中。
從知識的追求角度來說, 新聞傳播學科需要整理出一個自洽的秩序,這是業界學者需要努力的方向。雖然當下尚無法用統一的秩序和邏輯串聯起所有關于新聞傳播學的知識,但是可以通過分類的方式去偽存真。雖然新聞傳播學無法成為羅素所言不存在水分的“邏輯的木乃伊”,但也不能再繼續作為“一堆知識的亂碼”存在。
新聞傳播學的三個維度
在知識維度上, 新聞傳播學要以“ 求真” 作為知識生產的宗旨,以科學研究作為樣板,追求命題與事實的一致,具有準確性、一致性、簡明性和預見性。在價值維度上,新聞傳播學要追求正當、合理、邏輯這三個標準, 關注于“ 人” 的存在。在規則維度上,新聞傳播學要確立知識典范,建立學術共同體共識性的理念和共同遵循的典范。
在上述三個維度之下,新聞傳播學科還存在如下三個問題:一是我們的學科知識是邊緣性、專業性、地方性的“弱知識”,二是我們的學科價值是弱正當、低認同、小邏輯的“ 弱價值”, 三是我們學科的規則是缺乏共同體普遍認同和足夠硬度的“前范式”。
新聞傳播學創新要善做加減法
今天,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科面臨著作為“西方理論搬運工”的外部張力,以及作為“學科洼地”“知識洼地”和“話語權力洼地”的內部壓力。
展望未來, 新聞傳播學科的創新路徑, 應形成問題導向,進行整個學科的話語體系創造, 形成知識、價值和規則上自成邏輯的結構化秩序。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者要做的,一要跳出“繭房”,避免“內卷”,關注學科大樹的“枝干”而非“落葉”; 二要善做“ 加法”, 面對涌現的新問題,基于在場進行內生原創的理論創新;三要勇做“減法”,去掉學科中的中低端產能,做創新意義上真正的理論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