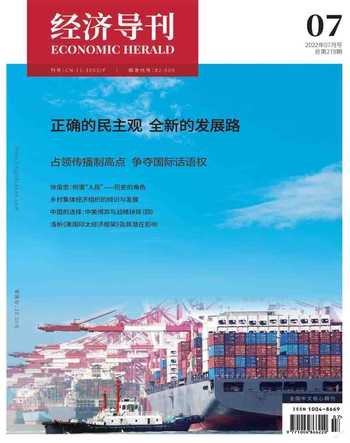大力促進(jìn)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
范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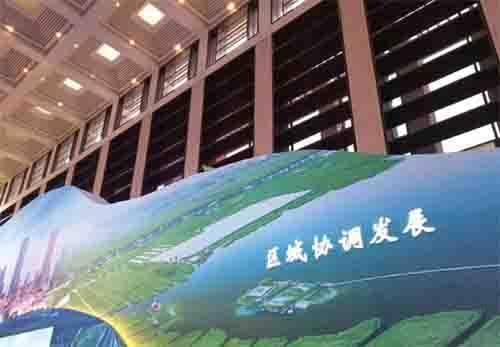
區(qū)域問題是影響全局、關(guān)乎社會(huì)前途的重大問題。我國幅員遼闊,但地區(qū)發(fā)展很不平衡,運(yùn)用國家戰(zhàn)略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進(jìn)而推動(dòng)整個(gè)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是中國的一個(gè)創(chuàng)舉,其效果已為過去幾十年區(qū)域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日益協(xié)調(diào)的實(shí)踐所展示和證明。可以說,區(qū)域戰(zhàn)略在國家發(fā)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國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shí)施與實(shí)踐效果
嚴(yán)格地說,我國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戰(zhàn)略的制定和實(shí)施始于上世紀(jì)90 年代的中期。針對日益拉大且比較顯著的地區(qū)差距,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huì)提出,“應(yīng)當(dāng)把縮小地區(qū)差距作為一條長期堅(jiān)持的重要方針”,并強(qiáng)調(diào)“從‘九五開始,要更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逐步加大解決地區(qū)差距繼續(xù)擴(kuò)大趨勢的力度,積極朝著縮小差距的方向努力”。①自此開始,縮小不合理地區(qū)差距、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就提到了黨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之上。
遵循這個(gè)指導(dǎo)思想,國家陸續(xù)出臺了一系列重大區(qū)域戰(zhàn)略。到2006 年,形成了以東、中、西和東北四大區(qū)域板塊分類指導(dǎo)為特點(diǎn)的國家區(qū)域發(fā)展總體戰(zhàn)略。針對“四大板塊”戰(zhàn)略覆蓋的空間尺度仍然比較寬、“一刀切”狀況依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實(shí),從2006 年起,政府著手縮小區(qū)域政策的空間單元,通過為一些典型地區(qū)量身制訂規(guī)劃和方案,進(jìn)一步將“四大板塊”戰(zhàn)略的實(shí)施加以深化、細(xì)化和實(shí)化。
國家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戰(zhàn)略即“四大板塊”戰(zhàn)略的實(shí)施,特別是對之深化、細(xì)化和實(shí)化帶來了十分明顯的效果,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是推動(dòng)區(qū)域增長格局發(fā)生了革命性變化。所謂“革命性變化”,指的是前所未有的變化或根本性的變化。這個(gè)變化是,區(qū)域戰(zhàn)略的實(shí)施扭轉(zhuǎn)了長期以來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增長一馬當(dāng)先、中西部與東部發(fā)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狀況。2007 年,西部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超過東部;而從2008 年起,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全面超過東部。今天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相對困難的東北地區(qū),實(shí)際上從實(shí)施振興東北戰(zhàn)略的2003 年起,一直到2012 年,都曾實(shí)現(xiàn)了超高速的經(jīng)濟(jì)增長。實(shí)踐表明,無論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年代還是在市場經(jīng)濟(jì)時(shí)代,東北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都有過輝煌的表現(xiàn)。有人對東北經(jīng)濟(jì)運(yùn)行有些擔(dān)心甚至灰心,認(rèn)為其發(fā)展難以出現(xiàn)新的轉(zhuǎn)機(jī),這種擔(dān)憂是缺乏科學(xué)依據(jù)的,東北經(jīng)濟(jì)是可以搞好的,關(guān)鍵取決于我們怎樣去做。
二是培育打造了一批重要的經(jīng)濟(jì)增長極。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引擎能量得到進(jìn)一步激發(fā)的同時(shí),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成渝經(jīng)濟(jì)圈等一批中西部地區(qū)的增長極迅速崛起,顯示出蓬勃旺盛的增長活力。
三是有力促進(jìn)了困難地區(qū)的轉(zhuǎn)型跨越。一批革命老區(qū)、集中連片貧困地區(qū)和資源枯竭型地區(qū)擺脫貧困,駛?cè)虢?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快車道,這得益于中央出臺的一大批直接服務(wù)于它們的政策文件與發(fā)展規(guī)劃。例如國務(wù)院《關(guān)于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qū)振興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從實(shí)地調(diào)研到制定出臺只用了90 天時(shí)間。且這一文件措施實(shí)在,具有很高的含金量。經(jīng)過這些年有針對性的扎實(shí)貫徹實(shí)施,贛南的發(fā)展面貌煥然一新,完全可以用“今非昔比”“翻天覆地”來形容。國家對烏蒙山、秦巴山等11 個(gè)貧困連片地區(qū)和新疆南疆地區(qū)等三個(gè)深度貧困地區(qū)制定了區(qū)域發(fā)展與扶貧攻堅(jiān)規(guī)劃,這些扶持政策為貧困地區(qū)加快脫貧發(fā)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實(shí)踐證明,基于適宜的空間板塊運(yùn)用戰(zhàn)略規(guī)劃和政策文件實(shí)施分類指導(dǎo),對加快縮小地區(qū)差別、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是十分有效的。這個(gè)過程不僅帶來了顯著的實(shí)踐效果,而且實(shí)現(xiàn)了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理論和思想觀點(diǎn),完全可以構(gòu)成一部中國獨(dú)創(chuàng)性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學(xué)。
黨的十八大以后,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得到進(jìn)一步的重視,戰(zhàn)略謀劃實(shí)施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黨的最高層直接謀劃與推動(dòng),一批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陸續(xù)出臺。與此同時(shí),在政策指導(dǎo)上體現(xiàn)出一些新的特點(diǎn),較為突出的有兩個(gè):一是更加注重跨區(qū)域、跨流域的經(jīng)濟(jì)區(qū)建設(shè)和一體聯(lián)動(dòng)。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長江經(jīng)濟(jì)帶發(fā)展、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sh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成渝雙城經(jīng)濟(jì)圈建設(shè)等戰(zhàn)略,所涉空間范圍都是跨省域或跨區(qū)域、跨大流域的。二是更加注重聚力解決區(qū)域發(fā)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最具標(biāo)志性的就是實(shí)施扶貧攻堅(jiān)戰(zhàn)。絕對貧困是導(dǎo)致地區(qū)差距懸殊、影響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首要問題。經(jīng)過艱苦努力,運(yùn)用中國獨(dú)創(chuàng)的方式,這場攻堅(jiān)戰(zhàn)成功實(shí)現(xiàn)了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下農(nóng)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在中華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消除了絕對貧困,建立了全面小康社會(huì)。
今天,謀劃、制定與實(shí)施區(qū)域戰(zhàn)略和政策已列入各級黨委、政府的核心議事日程,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一把手工程”,也成為各地方各部門的自覺行動(dòng)。地區(qū)的新領(lǐng)導(dǎo)、新班子到位后無一例外都把謀劃區(qū)域發(fā)展格局作為優(yōu)先開展的重點(diǎn)工作,區(qū)域戰(zhàn)略與政策擁有的地位之高可謂前所未有。區(qū)域戰(zhàn)略具有很強(qiáng)的感召力、集聚度和時(shí)代性,集高品位、強(qiáng)影響和大實(shí)惠于一體,作用舉足輕重,成為推動(dòng)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全面建設(shè)現(xiàn)代化國家的根本支撐與關(guān)鍵抓手。中央要求深入實(shí)施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和區(qū)域協(xié)調(diào)戰(zhàn)略,促進(jìn)東、中、西和東北地區(qū)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在今天,無論是短期謀劃還是長期部署,區(qū)域戰(zhàn)略與政策都成為當(dāng)之無愧的主角。
實(shí)現(xiàn)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的重要意義
我國地域廣闊、情況復(fù)雜,尤其是區(qū)域發(fā)展嚴(yán)重不平衡。在實(shí)行“全國一盤棋”部署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不同區(qū)域板塊的實(shí)際狀況進(jìn)行分類指導(dǎo)是十分必要的,能夠大大提升區(qū)域戰(zhàn)略指導(dǎo)的精準(zhǔn)性、匹配度和有效性。雖然從空間上看,十八大以來所推出的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是以跨省域或跨區(qū)域、跨大流域的,但從全國范圍看,這仍然是一種區(qū)別了四大板塊的另一種形式的分類指導(dǎo)。由于是一種基于較大地理空間的分類指導(dǎo),換個(gè)角度看,它又是一種以自然地理為基礎(chǔ)的相關(guān)省份間的一體聯(lián)動(dòng),或者說是跨區(qū)域的一體聯(lián)動(dòng)。這樣的一體聯(lián)動(dòng)有利于促進(jìn)資源要素在更大范圍流動(dòng)和配置,從而能夠提高區(qū)域整體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協(xié)調(diào)性和效率性。如果有科學(xué)理性的區(qū)域規(guī)劃引領(lǐng)、堅(jiān)強(qiáng)有力的組織機(jī)制推動(dòng)、持之以恒的聯(lián)動(dòng)舉措支撐等相配套,這種一體聯(lián)動(dòng)無疑有利于縮小戰(zhàn)略覆蓋區(qū)域各省份之間的發(fā)展差距,加快推動(dòng)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我國國情區(qū)情復(fù)雜性的表現(xiàn)之一是,即使以單個(gè)省份而論,其內(nèi)部各地區(qū)間的發(fā)展差距也是很大的。從這個(gè)角度看,任何基于較大地理空間的分類指導(dǎo)同時(shí)也是一種縮小版的“一刀切”。此外,一般的邏輯是,戰(zhàn)略覆蓋的空間范圍越寬,務(wù)實(shí)操作的難度就越大,不僅會(huì)因責(zé)任主體不清而影響工作力度,也容易導(dǎo)致實(shí)際操作淺嘗輒止、大而化之。這構(gòu)成了區(qū)域經(jīng)濟(jì)理論中一對有趣的“矛盾”:從合作聯(lián)動(dòng)角度看,空間范圍似乎越大越好;從分類指導(dǎo)角度看,空間范圍似乎越小越好,而它們又都是有利于促進(jìn)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
不少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近些年在地區(qū)分化加劇的同時(shí),地區(qū)間的發(fā)展差距又有所擴(kuò)大,其產(chǎn)生的具體原因是什么,需要做進(jìn)一步的研究。總結(jié)“十一五”及以后一個(gè)時(shí)期通過縮小政策指導(dǎo)空間單元帶來的區(qū)域差距逐步縮小的成功經(jīng)驗(yàn),可以認(rèn)定,秉持這樣一種操作策略也是極為必要的,即在實(shí)施跨省域或跨區(qū)域、跨大流域的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的同時(shí),應(yīng)著眼于一些空間尺度較小的特殊地帶,量身打造具有針對性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和政策舉措。這種基于區(qū)域板塊細(xì)分的分類指導(dǎo),能夠彌補(bǔ)縮小版的“一刀切”或操作中“大而化之”帶來的缺陷,從而有力地推動(dòng)一些特殊地帶擺脫困境、實(shí)現(xiàn)跨越發(fā)展。當(dāng)然,這類基于較小空間板塊的分類指導(dǎo)并非都需要由中央政府直接開展,其大部分應(yīng)該是在國家指導(dǎo)下由省級行政區(qū)進(jìn)行決策和實(shí)施。為了遏制區(qū)域差距擴(kuò)大的勢頭,這項(xiàng)工作應(yīng)與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的謀劃實(shí)施共同持續(xù)推進(jìn)。
鑒于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的獨(dú)特功效和作用,必須促進(jìn)各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間的有機(jī)銜接和一體協(xié)同。這個(gè)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也會(huì)直接影響到對抑制不合理地區(qū)分化和縮小地區(qū)間發(fā)展差距所做出的各種努力。
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是依特定區(qū)域的自然環(huán)境、當(dāng)前基礎(chǔ)、主要矛盾、基本需求等基本因素而制定的,其所體現(xiàn)的基本目標(biāo)、戰(zhàn)略定位、主要任務(wù)、基本政策安排等各不相同。這種不同是“因區(qū)制宜”的必然選擇,也是體現(xiàn)其實(shí)施效果的必由之路。但有著明確區(qū)域指向的區(qū)域戰(zhàn)略,也為各戰(zhàn)略間的相互隔斷提供了潛在條件,如果對其進(jìn)行封閉性實(shí)施就有可能形成兩種情形:一是各自為戰(zhàn)。各自獨(dú)立貫徹所涉區(qū)域的發(fā)展戰(zhàn)略成了一件十分自然也非常正確的事情,但這也使一些地區(qū)囿于圈中而跌入自我循環(huán)境地。從宏觀層面審視,這就是一種地區(qū)間的戰(zhàn)略分割,準(zhǔn)確地說,是在相互獨(dú)立運(yùn)作中使戰(zhàn)略差別演變成為戰(zhàn)略分割。二是各司其政。實(shí)施不同的政策成為相關(guān)地區(qū)的當(dāng)然職責(zé),也相應(yīng)阻礙了相關(guān)政策在地區(qū)間的融通和靈活運(yùn)用,形成了地區(qū)間的政策極差。
“戰(zhàn)略分割”將導(dǎo)致要素自由流動(dòng)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試所形成的經(jīng)驗(yàn)與做法得不到及時(shí)擴(kuò)展,而規(guī)則、規(guī)制、管理標(biāo)準(zhǔn)等制度性要素開放也面臨障礙等后果;而“政策極差”必然帶來地區(qū)發(fā)展環(huán)境的差異、所得紅利的懸殊,造成各地區(qū)發(fā)展機(jī)會(huì)的不均等和發(fā)展權(quán)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說,戰(zhàn)略分割和政策極差都可能給區(qū)域發(fā)展帶來新的不平衡,也可能會(huì)帶來不合理的地區(qū)分化。這個(gè)問題往往被人們所忽視,包括被區(qū)域經(jīng)濟(jì)研究者所忽視。大家更多關(guān)注的是區(qū)域戰(zhàn)略本身對促進(jìn)區(qū)域發(fā)展和國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正面作用,而區(qū)域戰(zhàn)略本身的顯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區(qū)域戰(zhàn)略本身并不存在問題,但如何避免封閉性實(shí)施則是一個(gè)值得重視的問題。解決這個(gè)問題正確的思路是,大力推動(dòng)并實(shí)現(xiàn)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間的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
推動(dòng)并實(shí)現(xiàn)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的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要關(guān)注開發(fā)性和平衡性:一是最大限度保持區(qū)域戰(zhàn)略間措施實(shí)施的開放性。除了存在較大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的先行先試項(xiàng)目、地域特性很強(qiáng)的發(fā)展改革舉措、需要中央特殊授權(quán)或特別審批的事項(xiàng)這三種類型,各區(qū)域戰(zhàn)略中所涉及的改革發(fā)展安排原則上都應(yīng)對所有地區(qū)開放。一些體現(xiàn)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本質(zhì)要求的制度規(guī)則,尤其應(yīng)允許各地相互借鑒和自主移植。二是最大限度保持區(qū)域戰(zhàn)略間直接政策紅利的平衡性。除了對特殊困難地區(qū)明確給予的政策優(yōu)惠,原則上不應(yīng)通過戰(zhàn)略規(guī)劃等直接給予特定地區(qū)優(yōu)惠性財(cái)政金融政策支持,對處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高位的發(fā)達(dá)地區(qū)尤其如此。對這些地區(qū)的直接支持主要應(yīng)集中在賦予其深化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權(quán)利上,而這種賦權(quán)又主要應(yīng)集中于風(fēng)險(xiǎn)很大、成本較高、前景不明的試驗(yàn)項(xiàng)目上。一旦試驗(yàn)成功,應(yīng)該及時(shí)向全國其他地區(qū)開放,防止因固化政策差別而形成或強(qiáng)化“馬太效應(yīng)”。
強(qiáng)化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的探索空間
任何實(shí)踐活動(dòng)的推進(jìn)都需要理論的引領(lǐng)和支持,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的研究、制定、實(shí)施是如此,促進(jìn)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的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也是如此。作為理論工作者,我們要有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擔(dān)當(dāng)和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精神,在研究探索中應(yīng)當(dāng)把握住這樣的導(dǎo)向或原則,即不僅要敢于批判,更要善于建設(shè);不僅要講否定什么,更要講提倡什么;不僅要告訴不能做什么,而且要告訴應(yīng)當(dāng)怎么做;不僅要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還要闡述只能做什么。總之,最為關(guān)鍵的是,既要提出問題,更要結(jié)合實(shí)際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案。
應(yīng)當(dāng)把推進(jìn)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間的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作為一項(xiàng)重要使命,為之提供深刻的、源源不斷的理論成果和政策建議。例如,各區(qū)域戰(zhàn)略間的融合對接應(yīng)秉持怎樣的原則,可融合對接的主要內(nèi)容有哪些,如何在實(shí)行戰(zhàn)略開放中保障其直接覆蓋地區(qū)必要的排他性探索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間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需要構(gòu)建怎樣的體制機(jī)制,如何實(shí)現(xiàn)區(qū)域戰(zhàn)略探索獨(dú)特性和政策公平性的有機(jī)統(tǒng)一。與此相關(guān)值得研究的課題還有:不同層級區(qū)域戰(zhàn)略實(shí)施對地區(qū)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影響、戰(zhàn)略覆蓋區(qū)域與非覆蓋區(qū)域發(fā)展效應(yīng)的差異、重大探索成果復(fù)制推廣的原則與路徑、區(qū)域戰(zhàn)略協(xié)同聯(lián)動(dòng)的平臺建設(shè)與運(yùn)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