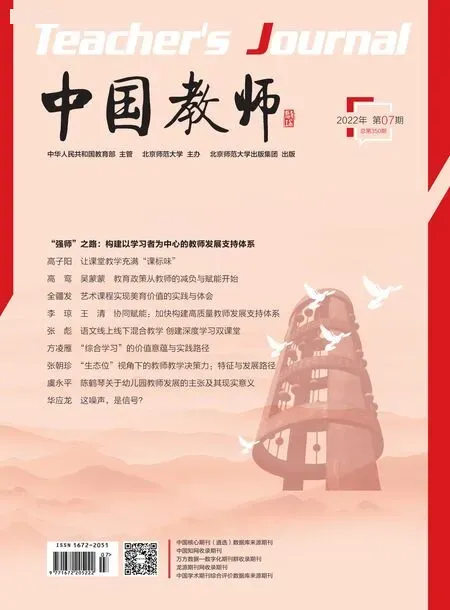二十六小時:一部手機引發的風波
李玉偉
閱讀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與成長:存在心理學探索》一書時,曾看到這樣一段話:
盡管人類可能是自私、貪婪、好斗的,但這些并非最根本的天性。透過表層,從心理學和生理學角度來看人類的天性,我們會發現最基本的善良和尊嚴。當人們表現得不那么善良和正派時,那只是因為他們正在對壓力和痛苦做出反應,或者因為安全、愛和尊嚴等基本的人類需要沒有得到滿足。
2020年的一段經歷讓我這個只有一年教齡的班主任記憶猶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對這段話的理解。一部手機,一個愚人節,當信息和事件一股腦地涌來時,一時間我手足無措。在班主任共同體的幫助下,我最終用愛和接納化解了一場風波。到現在我依然相信,兒童最基本的天性是善良和尊嚴,而這也正是我開展工作的出發點。
一切,都要從一部丟失的手機講起。
不翼而飛?
“老師,我的手機不見了……”剛回到辦公室,只見小嘉同學手足無措地對我說。
由于做核酸檢測,我要求全班學生上交手機,統一保管。原本一切順利,誰能想到竟在中午放學時出了問題!我詢問手機的具體品牌、型號、樣式特征。旁邊的郭老師聽到了,感嘆道:“這款手機起步價就要8000塊呀。”
大家的目光一齊落在了手機保管箱上。手機保管箱放在我辦公桌后面的沙發上,絕大多數手機已被拿走,只剩幾個落單戶,孤零零地躺在其中。
“可能是被同學‘錯拿了。”我寬慰小嘉。
隨后,我在班級群發了信息:“請‘拿錯手機的同學下午放學前把手機放到我的辦公室,否則失主將讓有關部門處理。”我格外注意措辭,并未用“偷”,而是用“拿”。
與辦公室其他老師簡單商議后,我們決定中午都不在辦公室,給“錯拿”手機的學生一個機會。
忐忑焦灼 15:40-17:45
時值早春,空氣中卻早已有了熱潮。
參加完歷史教研活動,回到辦公室,除了一摞摞的書和幾支筆,我的辦公桌上空無一物,手機依舊沒有歸還。我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于是迅速聯系年級組、安保處、學生處,調取監控,尋求幫助。
辦公桌對面的翟老師推測道:“好像沒有學生進過辦公室。”小嘉的媽媽發來語音:“如果晚上還找不到手機就報警。”安保處的胡老師也打來電話:“辦公室門口是監控死角,看不到上午放學時進出的學生。”
幾則消息一齊襲來,空氣一時凝固,讓人汗流浹背!作為班主任,我只能強壓住陣腳。故作鎮定之下,借用了即將要上的數學課,打算給學生上一堂臨時班會。
一進教室,我便開門見山:“今天發生了一件意外,班里一位同學的手機被‘錯拿了。我希望‘錯拿手機的同學盡快將手機歸還失主,否則就要報警。如果公安部門介入,事情的性質就變為‘偷拿,而不是‘錯拿,如此結果必將對這位同學帶來嚴重影響。大家千萬不要誤入歧途,一失足成千古恨!”
教室里一時沸騰起來,學生們有的表情嚴肅,有的竊竊私語,還有的則繼續低頭寫作業。
我采納辦公室陳老師給出的建議,拿出提前準備好的紙條,讓每位同學寫下自己知道的手機丟失的細節,并輪流進入一間拉著窗簾的空教室,把紙條和手機放入指定的箱子中。學生魚貫而入,依次而出。
結果讓人更加焦急,紙條中沒有線索,手機也沒有出現。
只能擴大查找范圍。
懸而未決 18:50-20:30
在年級組王老師和安保處的幫助下,我們將上午放學時進過辦公室的學生集中到一間空教室里,先給他們講清利害關系。
一通電話打斷了進程。“請問是李老師嗎?我是昆侖路派出所的民警,希望學校協助幫助尋找手機。如果20:30之前沒有線索,您要帶著小嘉同學來昆侖路派出所做一下筆錄。”小嘉的父母已經聯系了警察。高中生都還是未成年人,警察也不希望大動干戈,利用法律手段制裁學生。法律好比懸在頭頂的一把劍,一旦起用,必要……
靈機一動,我順勢請民警給學生普法宣傳,偷拿別人財物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公安機關會利用高科技手段迅速破案。“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昆侖路派出所的民警……”一席話果然起了作用,個別學生神情不太自然,顯得手足無措。我們再次安排學生陸續進入另一間空教室,要求如果有錯拿的,在紙條上留下線索,并寫明歸還時間。
學生依次而入……
“李老師,有情況!”譚老師邊說邊拿出了紙條。只見一張被折了多次的紙片左下角寫著五個字:“明天下午交。”因害怕被認出,每個字都被描了兩遍以上。
一通電話,一張字條,一顆懸著的心放下了。
塵埃落定! 翌日15:35-15:40
為了給“錯拿”手機的學生一個機會,安保處胡老師在沒有監控的門口設置了一個手機投放箱。
到了中午放學,箱中依舊空無一物。
距午讀還有五分鐘,兩個學生突然沖進辦公室,喊道:“老師,開水房有一部手機!”我沖過去一看,果真是那部有透明外殼的手機。
從2020年4月1日 13:35到2020年4月2日 15:35,整整26小時,終于塵埃落定。
下午第四節班會上,我巧用幽默來化解這一人心惶惶的事件:“昨天是愚人節,權當這位同學給大家開了一個玩笑。為這位同學感到高興,他迷途知返,沒有一失足成千古恨!還要感謝失主及家長的寬容大度,讓學校幫忙處理和教育……任何事情,在學校處理成本會小很多,因為學校允許大家犯錯;而一旦走入社會,事情錯綜復雜,代價往往是慘重的。”
我事后反思,生活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必須與犯錯者斗爭,強烈譴責一切違法行為。但作為班主任,有時我們還要從“情理”出發,給未成年的學生以改正的機會,以此避免學校教育中的“成功式失敗”。
26小時,挽救了一個“一念之差”的少年,找回了一部“價格不菲”的手機,安撫了一顆“躁動不安”的心靈。雖然“錯拿”手機者并未找到,到目前為止這依然是一樁懸案,但它帶給事件親歷者的教育意義卻是無窮的。我愿意相信,學生性本善,當他們表現得不那么善良或正派時,只是因為他們正在對壓力和痛苦做出反應,或者因為安全、愛和尊嚴等基本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我愿意相信,那個學生只是因為一時的貪念而犯錯。作為班主任,有時我們需要一些耐心。在教育中,愛和接納是最好的解藥。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克拉瑪依附屬學校)
責任編輯:胡玉敏